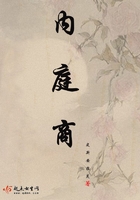陈郁记得自己去找母亲。母亲把他揽在怀里,低声说:“对弟弟好一点儿。”陈郁不说话,摇头。母亲就叹气,说,“你爸的话不可信。但是,你要对你弟弟好一点儿。”
陈郁不明白母亲的话。今天的我也不明白。
我觉得,在武汉车站站台上的陈郁,一定是心神不宁的。而他,在心神不宁之后,会做什么呢?
陈郑的牺牲始终是个谜。假如按照我的突发奇想,那么陈郁也许就在离开车站后向上司告发了弟弟。他会编造一些理由,说明自己当时来不及抓住共产党人陈郑,说明陈郑狡猾地脱逃了,而陈郑这个人,绝对是个值得大动干戈的重要人物。他提供了陈郑的相貌特征,提供了他可能的去向,也提供了陈郑其人的性格特点。他是哥哥,他了解陈郑。于是,铁路沿线的特务都动了起来,而陈郑就在返回途中中了圈套。
陈郑宁死不屈,壮烈牺牲。而陈郁的手,从此染上弟弟的鲜血。
他会这样做吗?
他会。因为他是……我打了个冷战,我不敢往下想了。我又想,不,不会的。不管怎么说,那是他的弟弟,他们有着同一个父亲。那么,也许是陈郁和陈郑的接触落在别人的眼里,引起了怀疑。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像陈郁这样的身份,不可能一个人在站台上执行任务。也许另有一个很阴险的家伙,逼陈郁交代出了陈郑。他告诉陈郁,你的行动是可疑的,你不说出那个人是谁,那么我将把情况报告上级。他还说,你不用编瞎话,我看得出你和那个人关系密切,而那个人必定不是好人。我知道,陈郁这家伙在性格上是憨直的,他肯定不会装出镇静,他的慌乱一定会摆到脸上。而如果真有那个阴险家伙的话,陈郁的心虚也一定会坚定他的信心,他的讹诈也会很快转变成有把握的逼问。如果是这样,结果虽然相同,但于陈郁来说,主动与被逼无奈,性质上大不一样。
我愿意相信事实是后者。
但那样陈郁就没有责任吗?当然不是。想到这里,我积攒许久的愤怒在胸中爆发起来了,它顶着我的喉咙,想要喷发出来。陈郁无疑是个出卖者,他为了自己的恩怨,而不惜出卖了自己的兄弟。即使是有人威逼利诱,他也绝对是半推半就的一头蠢驴。
我喃喃地咒骂着,付了钱下车。宾馆的霓虹灯在眼前闪烁,处在静音状态的手机在衣兜里振动着。我办好入住手续,在电梯里才掏出手机看了一眼,竟然是父亲。
我突然想:郑谦同志肯定是知道些什么的,他给我的感觉永远是深藏不露。
9
我洗过了澡,才给父亲回电话,嬉皮笑脸地说:“副市长生气了吧?原谅我哦,你知道我就是个不争气的丫头。”
郑谦同志叹了口气,说:“你呀,总不让人省心。”
我的心热了一下,我知道其实老爸是爱我的。
我恢复了欢快的语调:“老爸您就放宽心吧,我就是出来玩玩,没准儿还会给您带个女婿回去。”
“得了吧,”老爸的语气仍然平静,“你哪是休假,你人在武汉,你还是去调查那些破事的。”
我大吃一惊:“您怎么知道?”
老爸的话里竟有几分得意:“别忘了我曾经也是警察。你要想瞒我,就该把桌上的记事本收好。”
我想起来了,我在查找火车车次的时候,顺手在本子上记了一下。我无语。沉默了片刻,我把我刚才的想法大致和父亲说了一下。我承认我是被武汉吸引来的,我承认更吸引我的是我的前辈在武汉这块土地上的足迹。在叙述的过程中,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越来越相信自己的推断了。好像我在诉说中不断地加强和补充了自己。我说着,却听不到父亲的回应。这是他的习惯。他从来不会打断别人的诉说,他只是不动声色地听。我仿佛看见他举着电话时那张毫无表情的胖脸。在过去,他的这种冷静常让我恼火。
听完我的唠叨,他仍然沉默。
我说:“您说话嘛,骂我也好呀,我就怕您不吭声。”
老爸咳嗽了一声,然后说:“你呀,不撞南墙不回头。好吧,我告诉你,你的推测纯属无中生有。对于咱们家那些事,我早了解过的。陈郁,是长期潜伏在敌人内部的我们的人。看过电视剧《潜伏》吧?就是那样的。他活到了现在,已经是百岁老人,一直单身,深居简出,不见任何外人。”
我愣住了。在我的愣怔中,老爸又说:“历史不是推测,更不是凭空想象。历史是血染成的,我们不能不严肃对待。懂不懂?”
他挂了电话。他一定很得意,因为他教训了他这个愣头愣脑的女儿。想到这儿,我怒火万丈。
可是我不得不冷静下来思考。父亲的话在我面前打开了另一道门,这道门里的历史更惊心动魄,更充满戏剧性。陈郁和陈郑最后竟然殊途同归了,那么让陈郁最终选择和弟弟一样道路的契机在哪儿呢?我知道,在警校,陈郁是优等生,他是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做了国民党警察的,而且,从父亲的话里我知道,他后来确实进了“军统”。在武汉和弟弟陈郑相遇时,他……啊,难道那时他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了吗?那么放走陈郑就是他的故意了?甚至,他就是党组织派来保护陈郑的?
我在胡思乱想中睡去。我做了好多的梦。在梦里,我坐在了陈家端午节的餐桌旁。我的对面是陈庭生,他亲切地看着我。他的左右是两位太太。大太太埋头吃饭,不看我。我知道,她知道我是陈郑一支的后人,所以对我有一种仇视。她虽然低着头,但每一个肢体动作都流露着冰冷。二太太好奇地看我,好像说原来我的后代就是这样啊。她有一双美丽的眼睛,那眼睛里说出的话很亲热。有人踩我的脚,当然是陈郑这个坏小子,目不斜视的陈郁是不会干这种事的。当然陈郑也是目不斜视的,但他嘴角的坏笑暴露了他的行为。我好像还端着一只碗,碗里的肉好像是陈庭生夹给我的。我正准备吃这块肉,大门突然被猛烈地撞开了,暴民涌了进来,冲在最前面的,是一个举着步枪的孩子……
我一下子醒了。
拉开窗帘,城市还在沉睡,稀稀落落的灯火远远近近地亮着。只有江水,像一条暗白色的带子,铺陈在浓重的夜雾里,吸引着失眠者的眼睛。这就是武汉。这就是我的前辈们战斗过也缠绵过的地方。他们在这里生,也有人在这里死。他们的命运和这块土地紧密相连。
陈郑不是死在这里的,他的悲剧发生在从香港到武汉之间的任何一个地方。他的牺牲至今仍是个谜,而他的遗骨今天也不知道在哪里。他牺牲的时候还很年轻,刚刚二十三岁,他的孩子还在母亲的怀里嗷嗷待哺,他们父子就此永远地阴阳相隔。
我为此感觉很悲痛。
陈郑从香港归来时一定是快乐而轻松的。任务完成了,归途就像是旅游。但他仍然会是机警的,机警对于他来说已经是一种常态。所以,当他在某一个小车站发现站台上增加了特务时,他一定是警觉的。他会立即去判断这是为什么,但我想他大概不会想到这是冲他来的,他会想是不是当地地下党组织出了什么问题。
不,不对。我这样的想法仍然是以陈郁出卖了他的弟弟为前提,而我的老父亲明明告诉我,陈郁是我们的潜伏人员。
但我还是觉得不对。因为在路途中的陈郑不大容易因其他原因而暴露。他不属于他路过的任何地方的党组织,没有人认识他,知道他是谁。他已经完成了任务,身上没有武器,没有文件材料,在特务眼里,他应该和任何一个路人没什么两样。
他唯一的软肋,就是在武汉曾经碰到了陈郁。
当然这样的分析也有漏洞。如果是陈郁出卖了陈郑,那么陈郑失事应该在他的去程中,应该是没到香港就被捕了。难道是陈郁之流要放长线钓大鱼吗?这倒是可以说得通的。特务们从武汉开始跟踪陈郑到香港,发现他没有什么油水就在他的归途中下了手……不,也不对,陈郑在香港是向有关方面报告过工作的,而这些联系点事后并没有被破坏。
远远地,黄鹤楼在天际露出了雄伟的剪影。我仿佛看到,陈郁站在楼顶,他趴在栏杆上,痛苦地看着江水从脚下流过,心里纠结着他和弟弟的恩恩怨怨。
其实在我的想象里,陈郁才应该是倾向于共产党的人。他的母亲来自乡村,自幼家境贫寒,和陈庭生又是包办婚姻,没有感情,更忍受着小老婆的欺凌。在陈郁心里,母亲应该是痛苦的,这种痛苦就是共产党人所说的阶级仇恨。
陈郁在黄鹤楼上站着。他孤独的目光在江面上留下迷茫和阴冷。他现在是孑然一身,因为他的母亲已经去世,而他和二娘永远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父亲死后,是二娘拿出自己的首饰,供他们兄弟上了学。他感谢这个女人,可他和这个女人永远有距离感。这让他苦恼,也让二娘对自己有一种陌生的疏离。他拼命地工作,希望工作驱赶心中的痛苦。他是一个冷酷的警察,一个可以称作鹰犬的东西。但在黄鹤楼上,他拷问了自己的心。
10
我的爷爷郑天明从朝鲜回来的时候,英姿勃勃,年轻气盛。他一直在部队当到营长、团长。几年后,领导征求他的意见,是转业,还是继续在部队干下去。说实话,我认为郑天明在面临重大选择时是有私心的,他为了和已经从部队文工团复员到地方的漂亮未婚妻过幸福生活,一口答应转业。
从此郑天明来到了一个他陌生的城市。也就是说,我出生并长大的地方其实是我奶奶的故乡。为了爱情,郑天明同志把家族的履历改写了,我们由此和武汉这个城市再无瓜葛,以至于今天我在武汉的街巷中迷失了方向。
我换了好几辆出租车才找到老校长指定的饭馆。老校长的大板牙在阴暗的房间里显得更白了。他已经叫好了一大桌子菜,为忘记接站而道歉,态度很诚恳。我对武汉农家菜有一种好奇的亲切。特别是那道爆炒藕根,让我吃得胃口大开。他看着我吃,高兴地笑,说我的吃相和当年在学校食堂一样贪婪。我瞪他一眼,反击说他的门牙上也和当年一样沾着无数根韭菜。
那天我们喝了不少酒。我的酒量当然比他大。当我镇静地给自己倒上第五杯白云边酒时,老校长的舌头已经变得又大又短。他在反反复复地给我讲鄂北大山里的故事。他说,那个归隐山林的老家伙其实一生都不甘心他的贫苦和寂寞。他活着的时候,他的藤椅就永远摆在村口,他就永远地凝视着出山的那条路。他死了,他的坟也就依照他的遗嘱修在了这个地方,尽管村里人强烈反对,但他仍然固执而顽强地眺望着山外的世界。
我说,这是因为他当过警察。当过警察的人都这样,对自己的职业拿不起放不下。他那不是望山外的花花世界呢,他是望他曾经的岗位,望他的警服和肩章,望他那吆三喝四的曾经岁月。我的话当然是酒后的醉话,可老校长听得摇头晃脑,说我长大了,成熟了,说我不再是当年动不动就调皮捣蛋的毛丫头。我于是嘻嘻笑着,再敬他酒,把老家伙灌得酩酊大醉。在他最后醉倒之前,他说:“好多好多的事你还要问你爸爸,他其实……应该知道好多事的。”
他的话像一道闪电,在我的心上劈开一条深深的缝隙。我何尝没有这种感觉呢,可是我和父亲隔阂已久,我竟然不知道应该如何和他说话。回想起来,我们好像是一对冤家。
我摇晃着走到柜台,说了半天才让胖老板娘明白我的意思。她一边给我的母校打电话一边埋怨我说:“你说你一个小丫头干什么喝那么多酒。”我不吭声,扶着柜台站着,直到深夜母校来人把烂醉如泥的老校长接走,我才硬挺着走出饭馆叫出租车。回到宾馆,再清醒时已经是第二天早晨,我发现我没脱衣服躺在床上。模模糊糊记起,母校来的人我好像认识,最后一个记忆是我拍着那人的肩膀大笑,而那个人说我和当年一样,一点儿没变。
我痛苦地知道,其实我变了。
我忍着强烈的头疼,在床上呆呆地坐到中午,然后给父亲拨通了电话。电话响了很久,等待的时间长得令我几次产生了要把话筒扔了的冲动。最后,当父亲平静的声音终于响起的时候,我突然想,大概他和我一样,接这个电话也需要勇气。
“爸,我昨天喝多了。”不知为什么,我第一句话竟然这样说,而且语气是令我自己吃惊的娇嗔。
“和你的老校长吧?而且,他一定比你醉得厉害。”父亲的声音也是和蔼可亲的。他一定也在接电话前调整了自己。
“我头疼……我觉得我要死了……”
“傻丫头,你死不了,你还没气够我呢。”
“爸,我想知道,您这一辈子,到底喜欢不喜欢当警察?”
说完这句话,我知道我面临的一定是沉默。副市长知道我的话里有着太复杂太丰富的内涵,也感受得到我的话是在他平静如水的心湖里扔下的一块大石头,他只能沉默。职业对于人来说本身就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掺杂了太多情感太多痛苦太多付出的话题,这个话题纠缠着每个人的一生而且永远没有答案。而警察,则是所有职业中最具挑战性的一种,也是我的老父亲最不适合的一种。
但是,他生命中最鲜活的一部分,却做了警察。
终于,父亲说话了,声音有些沙哑:“你这个问题太重大了吧。”
“对于我们家来说,确实重大,重大到我不能不问。我们家好像命中注定与警察职业有关,不管我们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不管我们的心在哪里。”
郑谦副市长又沉默了。我想象得到,他此刻一定是站在窗前,眼睛盯着窗外的树叶。
“最开始我是不愿意的。”他终于又说话了,语气仍然平静,“也许……更准确地说,我一直都……”
“可是您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可是您一直关心公安局的事。可是您……早就调查了我们家的一切!但,您不告诉我。”
“有什么可告诉你的?说那个陈庭生是你的祖宗?有意思吗?”他激动了起来,“我不认为我们家有什么光荣。相反,我的梦里总是有你爷爷血肉模糊的脸!”
轮到我没话说了。爷爷的事在我们家就是一场集体的噩梦。我记得奶奶说过,爷爷因为不肯低头认罪被戴了背铐,戴了足足三个月。那三个月,爷爷只能双手背在背后,趴在凳子上,把脸埋在饭盆里去咬他的窝头,而大小便只能拉在裤裆里。后来,是总要给他打扫粪便的看守不耐烦了,才不得不给他打开了背铐。据说打开背铐时,爷爷的双臂已经不能正常弯曲,而他,只是怒目而视,嘿嘿冷笑,他的笑声让所有人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有人说,正是因为他的冷笑总在人们耳边萦绕不去,人们才索性把他殴打致死。
他的惨死,无疑在郑谦同志的心灵上留下了极大的创伤。在我的父亲那可怜的平静背后,竟然是不能让人正视的鲜血淋淋。我问不下去了,也不能再问。可是,当我准备挂断电话时,他却又开口了:“我第一天到公安局报到时,进了大门就想退出去,因为我满脑子都是你爷爷……我觉得我不能进这个门,我进不去。”
我听着。我仿佛看到了郑谦同志在公安局门前徘徊。那是极其沉重的徘徊,像是对自己的一种拷问。年轻的郑谦是很英俊的,据我奶奶说他像他的父亲,但我以为,其实他的性格一点儿也不像爷爷,他过于温和,甚至懦弱。他看着穿着上白下蓝警服的人们从他身边走过,看着同样上白下蓝的吉普警车轰轰隆隆地驶来驶去,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是陌生的隔阂。当然,他最终战胜了自己,不然今天就不会有副市长郑谦。命运就是这样的,不经意的一个拐弯,一生的轨迹就完全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