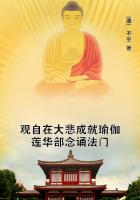银匠说:“我喜欢坐在陌生人中间。”
银匠说话时,他已在岩西村住了四个场期。十多天时间里,他打制完接到手的器物,到了和逐渐熟悉的村庄告别的时候。
银匠的出现很突然。十多天前,岩西村收完梯田上的稻子,湿润的稻草还没来得及码到零星的梨树干上,几个在晒谷坝上翻晒谷物的女人,不经意地往空旷下来的梯田上看去,她们看见早上出门赶场的村长从对面垭口上下来,腋下夹着两个纸卷,身后跟着一个背背夹的陌生男人。
“村长,赶场回来了?”一个长龅牙的中年女人远远地问,“你的胳肢窝里夹的是啥子东西啊?”
“我看你想男人想疯了,大老远地问村长夹的啥东西,村长能夹啥东西?还不是男人的东西。”另一个肥硕的中年女人故意装出呵斥的样子,眼睛却投向村长身后的陌生男人。龅牙女人的男人去重庆打工,有一年多没回来过了。自从岩西村的道路敞开以后,村里再也留不住那些长脚的男人,他们把老婆和孩子留在家里,像影子一样飘进城市,从此很少回来。要不是乡长将村长堵在家里,他也会走掉。村长是唯一留在村里的中年男人。
“你才想男人想疯了,真会乱嚼舌根,我说的是村长夹的纸卷是个啥东西。”龅牙女人说完,丢下肥硕的中年女人,回过身子拍了拍一个长相年轻且丰满漂亮的女人说:“陈慧琴,我眼睛花,你看看,村长后面那个人是不是他家亲戚啊?”
陈慧琴眯起眼睛去看越来越近的银匠。阳光洒在她圆润、白净的脸上,几颗晶莹的汗珠缓缓淌过她挺直的鼻梁和轮廓分明的唇线,泛起一片不易觉察的银白色光斑。陈慧琴将黑睫毛下的大眼睛努力聚焦,看见村长后面的男人精壮、瘦长,扬起一张白净且陌生的面孔。她说:“没见过,可能是村长家的亲戚吧。”
几个女人议论的当口,村长和银匠已经到了晒谷坝。她们围上来,嘴里和村长说着话,眼睛却看着陌生男人。
这真是一个白净的人。他的面孔白净细嫩,领口下露出一块呈三角形的洁白肌肤。长期下田的男人会在颈子下面留下一块深重的栗色,上面布满太阳烤晒出来的亮晶晶的油汗,而眼前这个男人的皮肤像女人,看上去很不自然,多少有些病态。女人们知道,他不是一个干农活的人。
村长说:“别看了,你们没见过男人还是没见过银匠?这是我从场上请来的银匠,他有一身好手艺。走遍山上的村寨,都能听见他的好名声。”
“哎!”女人们发出一声惊叹,像风吹过麦田,发出一阵细碎的共鸣。她们好久没听说过银匠了,上一次见到银匠,还是她们出嫁时的事情,仔细想一想,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村长,你夹个纸卷干啥子啊?”龅牙女人问。
村长从腋下取出纸卷,在阳光下展开说:“乡长给我的东西。一份是县法院枪毙犯人的布告;一份是县政府建设新农村的公开信。回头我把它们贴在我家板壁上,你们空了自己来看,反正你们也不识字。”
“这和银匠有什么关系?”陈慧琴问。她的声音清脆响亮,像鸟鸣。银匠好奇地看了看她,发现这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没有关系。”村长说,“银匠是我自己请的,不是乡长给的。陈翠不是在广州打工吗?她说那里的城里人喜欢我们这里的银首饰,她把自己带出去的银子当成工艺品卖了,很值钱,她让我把家里的旧银子打好带给她,她再去卖给有闲钱的城里人。”陈翠是村长的女儿,她和她男人一块到广州打工,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回来过了。
村长说完,丢下好奇的女人们,带着银匠往家里走去。
回到家,村长把枪毙犯人的布告和建设新农村的公开信一齐贴到虚楼的木板壁上。下午,西斜的阳光从白纸上折射下来一束银白的反光,把布告下的银匠照亮。银匠被村长安置在布告下,从此以后,村长家便传出银匠敲打银子的清脆鸣响,不停地在秋后空旷的土地上盈盈响彻。
闲下来的女人们借口看布告和公开信,拿着针线活来到村长家,眼睛却盯住那个女人一样白净的银匠。
开始,女人们只看看银匠的脸和他的手艺;一天之后,慢慢过渡到和他说话;最后,她们拿来坏掉的早已不用的银饰,让银匠修补。在银匠看来,这都是一些零碎杂活,焊接一只围腰链上的断口,为一块布满银锈的胸佩抛光,或者给一只被岁月磨旧的手镯錾上花纹,对这些零碎活计,银匠一概不要工钱。每当有女人拿来陈旧的银饰,他会像过去人们见过的银匠一样,用一杆小秤称好银子的重量,等做好后再称还给她们,重量分毫不差。他用一杆小秤守住了银匠的传统,也守住了自己的清白。
女人们说:“秤砣不会撒谎,这是一个好银匠。”
村里的女人们越来越爱到村长家,看银匠展示手艺,听他敲打银子的好听的声音。人们发现,银匠很少说到自己家,过了很多天,人们也不知道他家在哪里,更不知道他前面几十年在什么地方度过。在好奇的女人们的眼里,这个行踪不定的远方银匠像一片烟波浩渺的大海,露给她们的只有三五块礁石,其余则不为人所知。
银匠发现,围观女人中,陈慧琴是一个漂亮而安静的女人。她有时带一点针线活,有时带上她两岁的小儿子,她每次都坐在离银匠很远的阳光下,静静地看银匠把手中的银子打制成漂亮的头饰、胸佩和其他首饰。她和叽叽喳喳的女人不同,那些女人喜欢用嘴巴说话,她却喜欢用眼睛说话,偶尔露出一点声音,也像银子的声音一样好听。
“银匠师傅,你手艺真好,你为什么不进城打工呢?”陈慧琴问。
“我的手艺跟了我二十几年,害得我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银匠快乐地说,“城里要的是力气,不要我的手艺。”
银匠知道,陈慧琴的男人也在城里打工,他可能找到了一个好活路,所以今年秋收没有回来。银匠想,我要有这样一个安静漂亮的女人,一定不会进城打工,也不会走村串寨,我一定要守着这个女人过一辈子。银匠接着想,如果再住些日子,这个女人肯定能让自己发疯,肯定能。
好在银匠不用再住下去了,他把村长家的事做完,明天就可以告别这个逐渐熟悉的村庄,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银匠自言自语地说:“我喜欢坐在陌生人中间。当我坐在陌生人中间,说明我的手艺又要开始。”
银匠说话的时候,是中秋节下午,他坐在虚楼的楼檐下,为最后几件银器抛光。银匠的话音刚落,几个女人走过栅栏的缺口,陆续来到银匠身边。接着村长走出房门,走过贴在板壁上的布告,给银匠支付工钱。
“村长,银子还没过秤。”银匠说。
“大家都看到了,你是一个好银匠,你的心比秤还准。”村长说。
“我明天才走。”银匠说。
“今天是中秋节。”村长说,“到了中秋节,欠账要还钱,讨债要上门,付清匠人的工钱,晚上才能出去摸秋。”
银匠知道,中秋节付清匠人的工钱,是这一带的习俗。他接过工钱揣进怀里,说:“我听说过中秋节还账,没听说过摸秋,什么是摸秋啊?”
村长说:“中秋节晚上,人们可以到别人的地里讨要一点东西,即使主人发现了,不能骂,也不能喊,任由别人把地里的东西拿走,叫做摸秋。不过这个季节,地里除了几个老南瓜和老黄瓜,也没什么好东西可摸。”
“不对,村长,我家还有棵梨树才黄熟。”一个女人说。
“你是不是想村长摸到你床上啊?”另一个女人大声喊。
女人们围着摸秋的话题,叽叽喳喳地追打着离去。女人们离开之后,银匠看见西斜的阳光穿过虚楼边敞开的栅栏,栅栏把阳光分割成金色条纹,像若干道放射形光柱,冷艳峻洁地铺洒在虚楼前晒满谷物的院坝上。
人群散后,一片寂静,偶尔有一声银子的撞击声响起,又很快消失。
一群斑鸠掠过洒满阳光的竹林,空荡荡的土地上传来它们悠远的鸣叫。
吃过晚饭,银匠收拾好背夹走出虚楼,他看见一轮银子般皎洁的满月爬上前面的山峦。四溢的月光下,空中薄白透亮,幽蓝的空气水一般动荡,村中的大树展开它们丰茂的轮廓,衬托得辽远的田野寂静而幽冷。
银匠想到了摸秋。他决定去地里看看,说不定能摸到几只水分充盈、味道甘甜的梨子。
银匠踩着一地洁净的月光离开村长家,穿过虚楼外栅栏上的缺口,走上通往洼地的大路。银匠记得洼地上的玉米地边,有一棵结果的梨树。八月,梨子已经黄熟。在岩西村,自从有人举家迁到城里打工之后,人口密度降下来,不再像过去那么拥挤。到了梨子黄熟时节,除了偶尔有小孩攀上树去摘掉几个,多数梨子都会在树上烂掉,烂掉的梨子掉入秋天松弛的土地,发出沉闷的声响,空中浮满陈年蜂蜜的甜蜜味道。
银匠踩着月色到达洼地,穿过玉米地的浓厚阴影,结果的梨树像一大蓬阴影从土地上隆起。站在树边,银匠看见月亮重新浮出一小片薄云,把树上的梨子照亮。银匠身后,不断传出玉米秆被风拂动的声音。秋收之后,人们还没来得及砍掉枯萎的玉米秆,发黄、易折碎的玉米秆像影子立在空荡荡的地头,微凉的风拂过来,漾起细密的沙沙声。
正当银匠越过树下的稻草准备爬上梨树,身后的玉米地里传出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银匠想,又来了一个摸秋的人。他回过身往玉米地深处看去,他看见一个女人丰满的身影划开玉米秆的羁绊,像一个模糊的幻影突然呈现在梨树浓厚的阴影之中。
由于月光被梨树挡住,银匠看不清女人的面孔。他透过土地上的反光,努力分辨那个身形应该有一副怎样的面孔。在岩西村居住的十多天时间里,银匠差不多能认出所有的女人。
难道是陈慧琴吗?银匠想。
这个念头一下子击蒙了银匠,他感觉到一股暖流从脚底升起,穿过肠胃和胸腔,直冲脑门。当那个丰满漂亮女人的影像从他意识里浮升出来,银匠迅速离开梨树,将暗影中的女人搂在怀里。
女人没有反抗,任由银匠抽掉她松弛的裤带,解开她的衣裳,把她推倒在梨树下的稻草堆上。稻草刚从田里收回来不久,还有几分潮湿,一股植物素馨的芬芳在阴影下弥漫。
银匠那双细嫩的长手探过女人温暖而丰厚的小腹,像游蛇一样弯弯曲曲地往下滑,一直滑到他梦想已久的地方才停住。扑面而来的热气里,银匠感觉到身下的女人像肥沃的土地一样波动。纠缠中,他相信得到的就是那个能让他发疯的女人,他觉得自己的命太好了,一下子就得到了这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一块薄云飘过来,遮住了原本透亮的月色。
趁着黑暗袭满大地,女人迅速提起裤子,从稻草上站起身,准备像兔子一样逃开。心有不甘的银匠拉住她的衣裳,说:“你是慧琴吧?你肯定是慧琴。你看看,我很想你,不知道你会出来,我什么也没带。”说着银匠腾出一只手摸遍了身上的所有口袋,终于从裤包里摸出半块磁铁,说:“慧琴,我身上什么也没有,只有村长送给我的从坏喇叭上取下来的半块磁铁,我送给你,如果你晚上把针掉到地上,只要拿磁铁比划一下,丢掉的针就会跑到磁铁上来,这样,你晚上再也不怕掉针了。”
一直沉默着挣扎的女人终于开口。她的声音听上去很清脆,像陈慧琴,同时又很尖锐,又不像陈慧琴,银匠不知道这个女人到底是不是陈慧琴。正当他困惑不解,黑暗中的女人说:“我不要你的磁铁,如果你真心想送我东西,你就送我七个银座佛吧,我儿子过冬的棉帽子上正缺七个银座佛。”说完,她一下子从银匠的手里挣脱出来,像一道一闪而过的幻影,迅速逃进玉米地,很快消失了踪影。
一只夜鸟滑过梨树上方,月亮重又露出它银子一般干净的圆脸。
梨树依然站在玉米地的尽头,飘动的叶影拂出一地月光的碎屑。
银匠一夜未眠。躺在床上,银匠想,一定是那个能让自己发疯的女人,她什么也没得到,却把一切都给了我,她不是要七个银座佛吗?这是多么小的要求啊,我一定要拿出最好的手艺,给她打制七个银座佛。
吃过早饭,告别村长,银匠背上背夹,借故去了陈慧琴家。
走过一段土路,透过早晨初升的阳光,银匠看见陈慧琴家的大门上悬着一把铁锁,瓦脊上没有炊烟,也没有雀鸟的欢鸣。银匠像影子站在阳光下,看着铁锁百思不得其解,未必昨晚上真的做了一个梦?但自己一夜未眠啊!正当银匠看着铁锁出神,一声狗叫从牛圈楼下传来,很快又被一个女人喝住。
那是陈慧琴的邻居,她说:“银匠师傅,你找慧琴吗?她一早就走了。”
银匠说:“嗯。我要走了,过来看看。”
邻居说:“你真是一个好心情的匠人。”说完唤开狗,从屋角消失了身影。
银匠不得不离开岩西村。连陈慧琴也没有把他留下来的意思,他相信再也没有人挽留他。湛蓝的天空晴朗无云,温暖的阳光下,银匠把一颗心留下,带着一个空荡荡的身子,往东边独自上路。
起风了,秋天的风从北边的山冈上吹下来,带着一丝阳光的淡淡温暖。阳光灿烂金黄,没有多少热力的光线垂落下来,土路上的尘土像鸟羽般起伏。银匠走过一个小山冈,穿过一道深谷,当他到达一条湿气蒸腾的河流,身上已泛起阵阵热气。他从背夹上取出一顶破旧草帽戴上,以此遮挡炫目的阳光。银匠的前面,从河流延伸到山坡的乔木林上方,有一片银白色的河水反光,像大块银子的光泽,笼罩在呈锥形拔地而起的山峰上。他想,爬过这道陡峭山峰,就可以到达岩东村,在那里,应该能看见借宿的人家。
“银匠,如果命运称心如意,你又何必匆匆忙忙?”
银匠离开一地水气充盈的卵石,迈上一条河边的大路。透过河水流动的轻柔喧嚣,他听见一个说话的声音,循声望去,一蓬茂密的水麻树后面,一个老汉正用一双笑眯眯的眼睛看着他。河水的反光照亮了水麻树浓重的阴影,银匠看见老汉的脸上坑坑洼洼,仿佛一支火药枪曾经迎面给了他一下,他的脸才留下一堆密密麻麻的弹坑。
银匠说:“这年头许多人生活得称心如意,银匠的命运却不好。”
老汉说:“既然命运难以让你称心,你又何必匆匆忙忙?不如坐下来和我一起吃一把豆角。你的运气真好,豆角刚刚煮熟,你就到了。”
银匠看见老汉面前烧着一小堆柴火,橘红色的火焰上面架着一只装过午餐肉的洋铁罐,罐里煮着一把泥黄色的豆角。
银匠放下背夹坐下来,一股火光的温暖马上袅到脸上。
银匠说:“老哥,你心情真好,一个赶路的人还能在路边打野食。”
老汉从洋铁罐里抓出豆角递给银匠,呵呵笑着说:“我的路在我屁股底下。老弟,你看走眼了,我家在山那边的岩东村。我和你不一样,我不是赶路人,我在放羊哩。”
银匠说:“你的羊呢?”
老汉说:“你看。”他往河滩外的一个深沟指了指,那里有一群褐色的山羊像一群影子往茂密的草中推进。“我把它们舒舒服服地安排在草地上,那一块水草比庄稼还要肥美,羊们忙得连一点声音也没有。”
银匠说:“你真有办法。”他丢掉手里的空豆角,从火边掏出一个烤熟的洋芋,拍了拍灰尘,剥下一块被柴火烤得焦黄又泛起一阵清香热气的皮,放在嘴里咀嚼,说:“老哥,你知道有需要银匠的地方吗?”
老汉说:“老弟,你该跟上一个木匠。木匠出现的地方才有姑娘出嫁,只有当姑娘出嫁,人们才想到银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