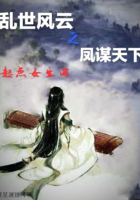他真想把小张的老表从床上拖起来,或者问问那个趴在死者脚边的儿媳妇,到底是不是真的要用这么糟糕的木料给他们的老娘打棺材?可是,这一切又与他有什么关系呢,他只是被请来的一个木匠,被一个叫张德贵的老朋友(谁知道算不算)托人请来的木匠,或者是经王桂兰推荐张德贵想起并首肯而请来的。是不是张德贵想起了他而托王桂兰、王桂兰又托刘玉堂请他来看来确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时候应该有一个人和他站在一起,一起反对使用这些腐朽的木料打一个棺材。这些人都蹲的蹲站的站看着他干,没有一个人有意见,也没有一个人没意见,这真让人难办。不过,张德贵也许可以懂他的意思,可以理解他,以至于帮他,他们合作过,虽然张德贵是瓦匠,有那个“隔行如隔山”这么句话,但因为曾经的合作愉快,他应该多少懂点。可是,话说回来,张德贵跟这个也没什么实质性关系。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无论是木匠还是瓦匠,都要遵守这一点。况且,木料的好坏与木匠更谈不上有什么关系,他只需要把这些腐朽的木料刨成木板,然后榫卯拼接,做成一口棺材即可,无论好坏,还不是最后腐烂在土里?!于是他拿起工具横在胸前,就像横下心来那样开始在众目睽睽之下干了起来。
因为腐朽,加工这些木料显得简便而快速。小张在他的身边帮着做着下手活,这更提高了他干活的速度。很快,所有尺寸的木板都做好了,他剩下的就是凿削榫卯。这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围观的人渐渐散去,偌大的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几个人在走来走去,也不知道他们忙什么。从正屋的大门望进去,那个趴在死者脚边的小媳妇已经醒过来了,她依旧呆呆地坐在那把椅子上。她的头发看上去有点乱,因为太远,也只能知道是乱,而不知道是怎么乱。也看不清她的眼睛是不是也穿过堂屋和院子与木匠四目相对或监视后者干活。总之,她的脸是朝这个方向的。木匠就边干活边朝她看。
有时,他会展开想象,她坐在那么明亮的堂屋内一动不动,真的很可怕,像一个僵尸,比那个躺在她身边的死人可怕多了。死人就应该躺下而不是坐着,也就是说,笔直地一动不动地坐着的人,而且是在明亮的灯光下,太可怕啦。为什么她不动一下?她真的那么孝顺吗?难道在她的婆婆生前,婆媳二人难得的感情深厚?想到这个,木匠突然觉得王桂兰是多么亲切的女人啊,她难得的和他相视一笑。她的身后总有那么丰富的传言,跟某某个眨了眼,跟某某在草垛里光着身子被人捉住了,跟某某的老婆分别抓了一把对方的头发……他情绪有点激动地想,如果这时候王桂兰出现了,再对着他笑一笑的话,那么他就娶他做老婆,决不会嫌弃她是个骚货。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对一个木匠而言,没有比他做活做不好更令人难过的了。因为那些木料的原因,所有的木板拿在手里都轻飘飘的,简直不像木板,像什么?不知道。他担心这些脆弱的木板加起来还没有死人重,担心最后大家把死人装进这口轻飘飘的棺材后,再抬着去埋的时候,死人会压断木板在路上漏出来,掉在了地上。最差劲的是,榫卯相接时,因为彼此的脆弱,经常会发生断裂、开叉之类的情况。为了弥补这些,他不得不使用铁钉把它们连接得相对牢靠。而那些穿过木板的铁钉又会在棺材内部露出它们锋利的顶端,他又不得不用铁锤将它们一一敲弯,从而防止死人入殓时被它们划破新衣服甚或冰冷的皮肉。
对他打击最大的还不是上面这些,而是,当他最终把所有木板拼接好之后,也就是棺材初具雏形之时,他发现了板与板的相接之处有缝隙,头顶的灯光直射入棺材内部,像水一样从这些缝隙中往外流泄。这很自然地使他联想到来塘村时所看到的那些门。那些门也像现在这样朝外面泄露着光。多么不幸,塘村的人就是住在露光的房内度过一生,死了也睡在同样品质的棺材里。木匠为这个发现感到难过。然后就是绝望:他到塘村无法受到欢迎和尊重,因为在塘村根本就做不好木匠活,请他来本质上是毫无必要的,之所以这么干完全可能是张德贵或王桂兰使然。塘村人为什么要如此粗枝大叶地生活呢?他们放了桦树,居然不把它们放到水里面去沤,而且还毫无常识地放到床下潮湿的地面上一摆就摆了十年。
木匠面对自己做好的这个轻飘飘、有缝隙的破棺材感到十分恼火。他握着工具停止干活站在那儿痛苦地想着上述这些问题,然后对自己说,是否应该把它拆除,重新来做?并且他还想征询一下在板凳上昏昏欲睡的小张。虽然他知道小张不会表示可否,但问问总该没错。或者,就这么停下来,先不急,等主家醒来,也就是死者的儿子从他母亲的床上爬起来后,问问他?如果那样的话,那么预期的工作时间应该会翻一番还不止。如果那样的话,明天早上他就不可能回到家,也就意味着不能给他的那些鸡喂食。早知如此,应该接受刘玉堂的好意,门不锁,或者锁后把钥匙交给他,请他帮忙到灶间靠近米缸的麻袋里取几根玉米棒揉给鸡吃。如果刘玉堂确实是好邻居的话,他应该能发现自己没有回家,没有及时给鸡喂食,那么他应该像这个死去的老女人那样给木匠家的鸡一些玉米吃吃。刘玉堂不会白做的,木匠回去之后会还给他几根玉米棒子,即便加倍偿还也未为不可。但是,他知道,刘玉堂不是这个死去的老女人,他没那么好。也就是说,自己长期以来认为的刘玉堂是个憨厚的人、是个不错的邻居的想法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并不符实。他是多么失望啊。
啊,打好了呀!从板凳上因为打瞌睡打过了头而差点跌倒在地而惊醒过来的小张一声赞叹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他看了看眼睛里布满血死的小张,痛苦地说,基本上差不多了,可是……小张很打断了他,精神焕发似的继续高声叫道,挺漂亮的,我这就去拿漆。他的语调是那么欢快,和那质量低劣的打瞌睡有点关系。木匠叹了口气,他知道,小张完全是外行,一点也不懂。不仅小张,全塘村的人都是如此:做的好,他们未必能看出来,做得差,他们也看不出来。手艺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多余的,他们只配守着往外泄露光的破门过日子,只配死后睡在这么破的棺材里。想到这个,他似乎不再像头前那么愧疚,安慰自己道,就这样吧,还能怎样!只是小张提着一桶漆来的时候,他将漆桶夺了过来,说,我来漆吧。他也像大梦初醒那样面对起了现实,考虑到棺材很可能在明天或哪天被塘村人抬往墓地,路上或许会被人看见,如果有内行的人看到,肯定会看到手艺的糟糕,自己来漆,是为了在缝隙处漆厚一点,把那些缝隙堵住,这大概是最后的补救方式了。
小张当然乐意漆棺材的事也交给木匠。他不再坐在板凳上,而是像许多醒来的人那样精力充沛地踱来踱去。后来,他抬起胳膊看了看手表,说了一声:快十二点啦。这话让木匠一惊,手一哆嗦,刷子在空中画了一笔,而不是棺板上。那个主家就快爬起来啦!这让他感到一种说不上来的紧张。那个人一直睡在那儿,在床边,木匠只看到过他半张脸,他的眼睛是闭着的,而且睡在床上的人的面孔和他站起来总有很大不同,也就是说,他到底长什么样,他的眼睛怎么看人怎么眨动,木匠一点概念也没有。看不清长相,没和对方对视过,我们就难以估猜他是什么人,就会无从了解,无从熟悉,无从把握。这是让他紧张的地方,另外,他当然也担心主家是个懂行的人,如果真是那样,那么木匠会面对自己干上这活以来最难堪的局面,会就此名誉扫地,多年来经营的一切将毁于一旦。
他无法阻止手的颤抖。刷子上的漆纷纷掉在了地上。小张发现了木匠的异常,好奇地问,师傅,你的手,怎么了?他的额上此时已在冒汗,他使用握刷子的手的手腕擦了一把汗,虚弱地答道,没什么,可能是累了。小张说,也是,那你歇会儿吧,不急的,说着他打算接过漆桶。听小张这么一说,木匠更急了,赶紧把漆桶拐向另一边,说,没事没事,我来我来。于是快速地刷了起来,几乎挥舞起了刷子,直到小张又走到一边去。然后他再次抬头穿过院子和堂屋看了眼那个笔直地坐在那儿的小媳妇,此时此刻她已不在那儿了。是不是她已经去了那个卧室,正在叫醒她的丈夫?是不是她的丈夫已经醒来,睁开眼睛与他的老婆四目相对?是不是他已经从床上坐起,然后用穿着袜子的脚在潮湿的地面上寻找鞋子?那双鞋子在他们之前搬木料时已被木匠拿到了一边,距离床大概有一米多远,那么后来小张带领别的人搬完木料后是不是又把鞋子放回了原处,好让他从床上坐起,直接可以把脚伸进鞋里呢?他大概已拔鞋跟,他站了起来,脚在鞋里矫正位置,他就要出来啦。
确实传来了响声。但不是来自正房,而是来自向北的院门。人们听到了金属相碰的声音,然后是一个男人的咳嗽声和一口浓痰吐在平整地面之声。这些声音因为深夜的寂静,显得响亮而辽阔。小张听到这些声音,高兴地从板凳上站起了身,他说,应该是我老子回来啦!说完就跑了出去。他那双非常白的球鞋就像两道光一样在院子黑暗的地面上划过并消失。木匠也放下漆桶绕过漆了一半的棺材走了出来,但手里仍然握着那把刷子。一些黑漆顺着刷子柄流在他的手背上和蓝色护袖上。他看到,在房子的直角拐弯处,他的老朋友张德贵正扛着那把还带着新鲜泥土的大铁锹走进了太阳灯照耀的院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