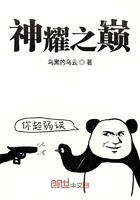美人眉毛一下就挑高了:“单位发的?什么牌子?”
韩一芊没把对方的语音语调往心里去,很老实的答道:“耐克。”
“耐克?”美人玩味的笑了笑,“哦,好多人都穿这个!对了,你用什么香水,味道很奇怪诶。”
韩一芊拽拽马尾,扯了扯嘴角,恶劣的笑了笑:“我没用香水。可能是洗衣粉的味道。”
“呀,你可真省!”美人言语间隐隐透露着优越感,开始苦口婆心的教育起韩一芊来,“哎呀,妹妹,这群人特别趁钱特别有势力,你瞎替他们节省啥?你看我用的就是香奈儿九号,你知道这个牌子么,Chanel?”
那还是知道的。韩一芊在心里默默的回了一句,却听美人鄙夷的看了她一眼:“你可真没见过世面。”
韩一芊难堪的垂下头,不再吭声。
身处战局的牧锦年忽然收杆,在一群人讶然的注视下走到两人面前,心里不禁有点恼火。
居然还有人敢这么胆大包天的奚落韩一芊,自己宠的女人,在自己眼里怎么都好,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疼还来不及,哪容得下别人指手画脚?
牧锦年占有欲十足的扣住韩一芊的肩膀,面色微沉:“这位小姐,既然您都把chanel念成channel,继续使用这个牌子恐怕只能辱没您的品位。”
美人当然知道牧锦年是谁。只怪牧锦年光芒过于耀眼,导致她根本没看清随着他出场的女人。
美人浓妆艳抹下的眼睛颓唐万分,她妄图解释,唯恐天下不乱的盛泽天早已蹿了过来:“这女人哪个没眼力见的带来的?给我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
一群人哪见过这种场面,别说是这样的剑拔弩张,他们连牧锦年生气的模样都没见过,顶多好死不死的撞上牧锦年正在阴风阵阵的邪笑。
现在却为这么个女人大为光火,实在不是牧锦年一贯的风格。在场的除了韩一芊,个个都是人精,肚子里算盘珠子一拨,墙头草纷纷倒向韩一芊,众星拱月般的涌向韩一芊。
韩一芊不太会应付这样热闹的场面,还是盛泽天一路把她引了出来。
牧锦年在旁边不远不近的看着。
盛泽天瞅瞅韩一芊,又瞅瞅牧锦年,笑了:“我可从没见过你家那位这样,韩一芊,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韩一芊惨淡的笑了笑:“打狗要看主人面。”就算是他身边的一条狗被羞辱了,牧锦年也是这个反应吧?
牧锦年的脸色倏然一白,把牙关咬得咯咯作响。
韩一芊,你可真会说话!
牧锦年的冷眼旁观和盛泽天的奋力解围,始终不能把一批批涌上来套近乎的人挡出去。
韩一芊站在那里,被肉麻的恭维话说得晕头转向,脸一阵红一阵白,平时的伶牙俐齿此刻无用武之地,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啊。
明明不喜欢却强颜欢笑的模样看得牧锦年异常火大,沉着脸,不由分说的拽住韩一芊的手腕:“跟我回去!”
韩一芊看着牧锦年紧绷的下颌线条了然一笑,嫌她丢脸了是么?这样的场合估计她连邱冉的千分之一都不如吧!
想到这里心里不自主的开始泛酸,嘴巴紧抿成一条线,极轻的嗯了一声。
两人回去后,时间将近傍晚。
一进门,韩一芊便忙不迭的冲进厨房,她不说,他也明白,她害怕和他独处,因为这段时间牧老太爷把曾孙子抱过去陪伴,家里只有他们两人。
当天晚上的菜色格外丰盛,隔着汤汤水水氤氲的蒸汽,韩一芊眼里那点期待分外明亮和诱人,咬着的嘴唇如同丰润的樱桃,盈盈的快要溢出水来。
牧锦年只觉得腹部一阵燥热,近乎贪婪的注视着韩一芊脸上阔别已久的亮色,一直到韩一芊微微发窘的埋下脸,把碗碟一口气堆在他面前:“吃饭吧。”
韩一芊憋着不说,牧锦年就有那个耐心不问。这种僵持的气氛一直持续到卧室,韩一芊卷了层薄被自顾自的缩在床角,拥着被子拔了好久的线头,才状似无意的说了一句:“我们剧团要去灾区慰问演出。”
牧锦年英挺的眉毛皱了皱,语气绝对够得上不悦:“那种地方?”
一不留神,一整根线头都被韩一芊拔了出来,指甲掐在肉上,很疼。韩一芊往被子里拱去,声音隔着被褥有些发闷:“你要是不喜欢,那就算了。”接着又自暴自弃的加了一句:“我不去了!”
牧锦年苦笑,伸手拉过韩一芊的被子,俯身替她盖好,又在被角上掖了掖:“我再不喜欢,也挡不住你喜欢。”手指不由刮去了刮某人小巧的鼻梁,天知道她这副呆呆傻傻的样子有多要命。
牧锦年隔着被子把韩一芊一点点拢进怀里:“只要你高兴,我什么都喜欢。宝贝儿。”
其实打心底,他不愿意她去那种偏远破旧的灾区去慰问,不是他没有同情心,而且他不想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去受苦,因为那里灾后重建,条件有多艰苦,可想而知,但是他又不忍心看她不高兴,他知道她想去,不过是逃避他而已。
‘只要你高兴。’,韩一芊一怔,脸埋进牧锦年颈间轻微的蹭了蹭。
一阵湿软的暖意侵入肌肤的纹理,牧锦年的指尖抖了抖,接着插进韩一芊柔软的发根轻轻抚弄。
女人的头发有多软,她的心就有多软,这句话真是一点没错。
韩一芊第二天便启程了。
牧锦年专门去送她,又怕她为难,特地把十八相送的地点定在某隐蔽角落。
牧锦年无比男人的口吻叮嘱起人来特别喜感,把同样一段话重复了足足七遍:哪些药是消炎的,哪些是防晕车的,还特地准备了驱蚊虫止痒的中药。怕她弄丢了,特地把每种东西都分成三小份,一份放在韩一芊的包里,一份放在行李箱,一份藏在某件外套的内衬里。
韩一芊不觉好笑:“也不想想你这三脚猫的功夫哪儿学的?”
很久没有用这么心平气和的语调说话,此言一出,两人俱是一愣,韩一芊的脸甚至可疑的红了红,晴暖的阳光在两人之间翩翩飞舞,牧锦年眼里投射着和煦的光芒,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次第炸开。
牧锦年自豪的笑了笑:“跟我老婆最能干的老婆学的。”
灾区重建的地方有点深山老林的意味,不过孩子们却异常可爱,知道城里的叔叔阿姨要来慰问他们,前一天就把自己搓得干干净净,黑黝黝的皮肤刷得红红的,像一排被蒸熟的虾子。
作为幕后工作的韩一芊的任务最简单,只需支着三脚架记录孩子们可爱的笑颜,镜头下纯真无暇的脸庞常常让她恍惚。
想到了自己的儿子牧子正,那个小东西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嚣张的挥舞着小胖爪子,扯着糯糯的嗓子,就连尿床了也哭得中气十足?
慰问演出为期三天。
最后一晚,韩一芊一手搂着一个孩子睡得正香。一股异乎寻常的闷响把韩一芊从黑甜乡中惊醒,怀里的小胖妞也有所察觉,不满的嘟哝了一声,扑棱着藕节似的胳膊划了划,慢悠悠的转过身,把肥肥的小屁股对准韩一芊。
韩一芊失笑,俯□亲了亲小家伙热乎乎的背。
闷响声却越来越重,越来越密,一种蠢蠢欲动的恐慌如同破笼而出的野兽,毫不客气的刺破黑暗,向韩一芊扑将过来。
正赶上雨水充沛的季节,山体石质松软,再加上刚刚地震过后,并不坚固,该不是这么倒霉,撞上山体塌方了吧?
接下来可怖的情景证实了韩一芊的猜想。
脚下的地面被接踵而至的石头砸得剧烈抖动,四处漆黑,却此起彼伏的想起孩子的哭叫声,玻璃的碎裂声和大人惊恐万分的咒骂。
雨势偏偏在这刻汹涌起来,如同流星般陨落,声势浩大如同擂擂战鼓,雪白的闪电争先恐后的擦亮天际,把韩一芊一张脸都映成惨白色。
她反应过来,立刻捞起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向外奔去,她力气不大,又在这种急惶的环境之下,一个不留神,背上的孩子就搂着她的腰滑坐下去,怎么也拽不起来。
韩一芊又怕又急,只好把小的那个先抱出去,放在一块较为安全的平地上,脱下自己的外衣披在孩子身上。
孩子小小的脑袋从衣服里拱了出来,两个眼睛如同雨洗过般的明亮,小孩子翘起嫩嫩的手指着韩一芊,喃喃的轻叫道:“妈妈”
童稚的呼喊把一颗心浸泡得既酸又软。
韩一芊眼眶一热,眼泪又不争气的砸了下来,女人与生俱来的母性被唤醒,尽管眼前的土坯房随时可能倾塌,她还是义无反顾的冲进屋里,把睡得不知今夕何夕的孩子扛了出来。
啪嚓一声巨响,房子的大梁被压塌,直直的坠落在韩一芊眼前,溅起的泥土飞扬到韩一芊脸上,韩一芊猛烈的咳嗽起来。
身之所在正在惊心动魄的塌陷着,怀里的孩子已经被吵醒,乌黑溜圆的眼睛里写满了惊恐无措和无条件的信任。
韩一芊心一横,便把用来逃生的最后一丝力气挪作它用,她拼死把孩子丢了出去,孩子软软的身躯被屋外的棚子一档,弹了弹,总算安全着地。
她如释重负的歪倒,整个世界都夹石带土的向她倾轧过来,四周漆黑一片,偶尔会被闪电照得发白,做工粗劣的窗子正在噼里啪啦的响,如同催命一般,一声急过一声。
哗啦一响,整间屋子的玻璃同时碎裂,瓢泼的雨如同鞭子般甩在韩一芊脸上,她又冷又累,缩在房里相对坚固的一角瑟瑟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