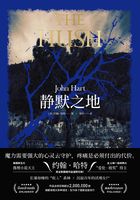两个孩子凑近一些,弟弟伸手轻轻笼住鸟。他的手黑黑的,像积了一层煤灰,手背裂了几个鲜红的口子。鸟的热量似一根灼热的细铁线,从掌心钻进去,他嘻开嘴笑了。小女孩羡慕地看着,欲言又止好几次,终于说,让我抱一下吧。两兄弟望着她,不知道抱一下是什么意思。小女孩脸上如同红墨水洇开。怎么抱?哥哥说。就和你一样,小女孩说。他们明白了。两兄弟对看了一眼,不置可否。小女孩脸上显出渴盼的神情,姐姐瞪着她,她丝毫不觉。哥哥最后吐了一口气,下了决心,好,你拿紧了,不能松手。小女孩伸出手,那是一双没干过活的手,白净,细腻,温软。哥哥的手慢慢松开,小女孩的手慢慢拢紧,哥哥神情凝重,确保不碰到小女孩的手。小女孩接过鸟,嘴唇裂开,露出洁白琐细的牙齿。两兄弟也笑了。就是这时候,他们放松了警惕。哥哥松了摁着鸟翅膀的手,扑塌一下,鸟使劲儿奓开双翅,低头啄了一下小女孩粉嫩的小手。啊——小女孩短促地叫了一声,松开手指;嘎——红胸脯的鸟悠长地叫了一声,纵身高飞。弟弟跳起,捞了一手空。四个孩子仰起脸,看一个红色的小点迅速冲向瓦蓝色的天空。他们脸上留下了一簇红色的影子。
四颗心猛地往下坠了一下,又奇迹般地,随了那红胸脯的鸟儿腾起,悠悠荡荡,高高地升到澄碧的苍穹。他们身下的村子,沉重泥泞,阴暗潮湿,缩成一个芝麻粒大小的黑点儿。
小女孩眼里蒙了一层泪水。我不着防……她说。哥哥却很大度,搓了搓手,不怎么,我们再抓一只。弟弟也学着哥哥说,不怎么。小女孩看着他们,看得他们脸红红的。小女孩两手揉着衣服下摆,慢慢退回去,这时,弟弟望着她说,你是金雨,又指着小女孩身后的姐姐说,她是金雪,我分得清你们。你是妹,她是姐,哥哥说,我也晓得。弟弟竟然抢先说话,他有点儿不满意。等我们再抓了鸟,再叫你们出来瞧,他又补充了一句。小女孩笑了,露出白白细细的牙齿,我也晓得你们,你是金东,你是金杰。她身后的姐姐张了张嘴,似乎想说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又什么也没说。两姐妹退回屋里,门在她们身后关上。她们仍旧掀起一角窗帘,偷偷注视院子里的两兄弟,暗暗希望他们再抓到一只鸟,可他们再也没能抓到。他们徒劳地守候了大半天,直到太阳燃尽白天的最后几分钟。第二天,他们也没抓到鸟,第三天,也没有。他们再也没跟那两姐妹说过话。
后来落了几场雨水,院子里的鞭炮屑彻底失去红艳,变成一点点黄褐色的碎纸片,逐渐融入泥土,成为泥土的一部分。大院子里,最后一点年味也随之消失殆尽。墙那边的菜地又长出绿油油的腾蔓了,再不往南边的墙头长,王贵芳每天看一遍,将每一根腾蔓拉到靠自己那边的墙上。金大庆很为此得意。两家人的敌意不紧不松地持续着,后来,两家的女人一句半句开始说话了,男人仍梗着,彼此不屑一顾。两家最终尽释前嫌,得等到十多年以后。
十多年,说来漫长,踮起脚尖也看不到头,真正过去了,想起来也不过一眨眼的功夫。这期间,大院子东边的那堵墙,在一场大雨过后,塌了。也不是一次性塌,先是土基给一次次雨水泡软了,一天一天软下去,如到了年岁的老人,渐渐矮缩了;之后,猪和鸡跑进院子里,免不了要踩上几脚,拱上几鼻子,雪上加霜,摇摇欲坠,土基今天少一个,明天又少一个,后来,就不剩什么了。墙,就那么残缺着。猪啊鸡啊,可以自由跑到菜地里,菜地也做了院子。夏天的时候,院子里跟那菜园一个样子,也是一片青绿,院子又做了菜园。金大年抱怨不已,可金大庆不修,他也没办法。
两家的女人呢,也不提墙的事。金大庆媳妇小心着,不再让猪和鸡到院子里。有时候,王贵芳掐了菜,会拿上一把,交给女儿,让送到对门。老远的,她听到金大庆媳妇热情招呼女儿的声音。金大庆媳妇没什么东西送王贵芳,心里就有些歉然,又有些处于弱势的感觉。有时,就会站在路上,和王贵芳说两句话,夸赞金雪金雨学习好,抱怨金东金杰读书不成器。过了几年,不知道什么原因——大约是赌气,那堵墙又重新修好了。空心砖,青灰色,比原来的要高和威严,沙子和水泥透着新时期的气息。又过了几年,大院子里的四个孩子长大了,鸟儿一样纷纷离开家。大院子愈加沉寂下来。
金杰要结婚了。这是老石死后,大院子里第一次办客事。一红一白两件客事之间,相隔十多年的遥远距离。他哥早几年在外面结婚了,婚事却没在家里办过。这时候,就是哥哥陪他,挨家挨户请人来做客。哥哥初中只读了一年,不读了,出去学修车,学得半会不会,出师了,帮人看修车铺子。金杰读得久一些,也不过挨到初中毕业,也到外面去,什么也不学,胡混了几年,又跟哥哥凑到一起,现在,跟这县里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两兄弟,都在几百里外的边境县城打工,每月六七百块钱,支付自己的花销还勉强。可金大庆在家里,逢人还要说,大那个,上个月给我寄了多少钱,小那个,这次回来又硬塞给我多少钱。
女人瞧不上眼,也不好说什么,只怕两个儿子学坏。那大的,脑门前留一撮头发,染成黄色,衣服也尽买那种披披挂挂的,有一次骑了一辆摩托回家,说是自己攒钱买的,问了几次,也是这话,可过了些时候,摩托不见了,也没个由头。小的骑了哥哥的摩托,在村子里乱窜,老远就听得见声响。母亲越来越担心,想着结了婚没准会好些,给他们说了人家,又都不要,没过多久,金东却带了个黑灰的女人回家来,说已经结婚了。金大庆咆哮如雷,没用,肚子里的孩子总不能不承认。失望之余,金大庆给小儿子念了几百遍紧箍咒,以为万无一失,不想,金杰又重蹈哥哥的覆辙。姑娘大着个肚子住到自己家来了,火烧眉毛了。
金东金杰请客回来,母亲问他们,你大爹家请了没有?请了,两兄弟回答。怎么请的?母亲还不放心。还能怎么请,就说到时候来吃饭,两兄弟又答。哪能这样?母亲大为不满,拉了金杰走到对门金大年家。王贵芳正在厨房里做饭。母亲走进去,王贵芳立即满脸堆笑,好像她们是多么好的姐妹。母亲指着金杰,狠狠数落了一顿,又向王贵芳赔不是,说,你可不要偷懒,不光要来吃饭,还要来帮忙,还有金大年,她们两姐妹,也要来帮忙。王贵芳拖长声音说,哟——吃你们家一顿饭还真不容易。心里却是高兴的。
客事前一天,王贵芳吃过早饭,拿了一把菜刀,到金大庆家帮忙来了。两个女儿给她派到洗菜处,不多时,回来了,也不说为什么,又钻进房里。王贵芳脸上挂不住,在厨房里,急匆匆做事,菜刀快起快落,砧板噔噔噔响。随时间推移,大院子里的人熙来攘往,布蓬搭起来了,灶垒起来了,灶洞里塞满干燥的劈柴,红艳艳的火苗呼啦啦窜上去,舔着锅底,锅里热气沸滚。执事的人,帮忙的人,这边呼,那边应。生活的气息热烈了,浓稠了。只有那两个双胞胎姐妹,躲在自己屋里,没有加入这有着巨大漩涡的滚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