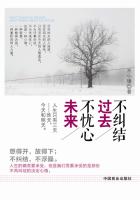一路向北徐行,气候渐以干涩寒凉,分不出究竟是春迟迟还是秋来早,沿途所见绿意浓苍,不折不弯恰若此地之山水。
自出都城后,我便还回寻常轻便的衣装,偶尔骑马而行。北燕人素来旷达,我的不拘礼法正对了他们的心思。想来要是寻常的南屏女子,那番矜持贵重闺中仪态,难免在这群北燕汉子眼中不成了矫揉造作。要是迎回一个如菟丝子般的新皇妃,他们会有多厌弃。
过武灵州,天气骤冷,满目青黄,尘沙初起。书中说,此地外百里皆为古时流刑之地,少雨疾风,谷粟不生,盗匪横行。
如荒原般的所在,稀疏间隔着破烂的房子,仍有人在此居住不舍故土。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实实在在的苍凉引一份幽咽卡在喉头。
天地坦荡,却不知我的前路又将如何,稳了稳心神,不自觉的抿了下干燥的嘴唇,有种淡淡的铁锈味,原来嘴唇已经干裂出些许伤口。
一只行军水囊无声无息地递到眼前,我愣了一下接在手中。方才胡思乱想,没注意容公子何时骑马来到我身侧。
我感激一笑,最普通的清水此时也有了甘甜的味道。
这一路来,宋柯大人和容公子对南屏诸人颇为照料。只是,随行的南屏侍者昔日只是在宅院里劳作生活,并不曾经历奔波,加之水土不服,一路来南屏众人病了大半,憔悴的让人惊心
甚至菡儿更是虚弱不堪,这几日食欲餍餍,整日昏昏睡在马车里。
眼下离大驿站还有数日的路程,眼下大家只能忍耐着上路。
“曲小姐不要担忧,下一站可多停留数日待众人调养好再上路也是可以的。”容公子稳稳地说。
我不禁苦笑一下,“曾听长辈讲,古时候是南屏的流刑地,如今总算能体味二三。”
容公子体谅的一笑,“让曲小姐担忧了,此地临近戈壁自是荒凉干涩,等过几日出了南屏地界往东而下又是夏临人间。北燕虽然较南屏寒凉,却四季分明,景致亦别有风味。北燕都城亦是繁华之至,等到入了都城恰逢蔷薇盛世,而冬日时分更有白雪红梅共太子妃赏阅。”
容公子的体恤让我心头一暖。但这些南屏随众仍让我忧心,若是能逾越礼法让这些人归返南屏,这一路紧缩的心或许可以宽宥。我不知会不是在将来的年月被刻骨的乡愁袭倒,却知此一行难免会有人客死在一路旁。想到此,不免郁郁,何以我曲秧歌一人竟牵累众人至此。
自出了长乐都城,容公子便一身轻便戎装终日骑行在马上。最初相识时翩翩儒雅,此时已经找不到痕迹,那如水的面容,专注而沉静,双眼目视着前方,虽然对众人言谈不喝不怒,淡然中却带着不可抗拒的威严。想来他定是北燕中位高权重之人。
不知为何,我并不畏惧他,在长乐时的恼怒也早随着路程渐远抛诸脑后。
“容公子。”我唤住他,声音竟然沙哑的可怕。
差异这样的声线是来自自己口中,不由失笑,“容公子,能否与我谈谈北燕?”
容公子看着我点点头,“曲小姐想要听什么?山川地理抑或风土人情?”
“这些都好,不过今日我更想听宫闱秘辛,还劳烦公子了。”我促狭地眨眨眼。
“宫闱秘辛?”容公子并未恼怒。
“我想听容公子为我讲讲北燕新皇。”一面打量容公子的表情,一面解释道,“寻常女子出嫁,纵使只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多少对未来的相公有些知晓。我这番仓促,甚至连未来良人的生辰八字都不知晓,简直是这世上最糊涂的新娘。”
容公子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笑意,“太子殿下年长曲小姐五岁。”
“那北燕的皇帝陛下是个怎样的人?”
容公子的笑,终于弯上嘴角,“是个……意想不到的人。”
傍晚时分,侍者送来一个白瓷瓶,说是容公子吩咐送来的。打开却是一瓶枇杷香露,没想到容公子竟会如此细致。心里的感激不禁又多了一层。
两日后,我们行至罗平镇,这是此行南屏东北翼最边陲的驿站。
“意想不到的人?”这两日来时而会想容公子话中的意思。传言中北燕太子是个荏弱之人,自幼便病患缠绕。当年新皇雨乔入质七年得以安然归返,和这传说中的北燕新皇定有关系。再观宋柯大人同容公子诸人的做派,这北燕新君果真算是不可思议之人。
本打算同容公子相谈更多,却不想这两日下来只看见容公子同宋柯大人在冗长的和亲队伍中异常忙碌的身影。
众人在罗平镇安顿好,随行的医官招来当地的医馆里的坐堂先生,一群人忙着照料诊治南屏众人。
人数之多让人忧心,于是我连同随行的南屏礼官与容公子诸人商议,奏请南屏帝南宫雨乔,让身体抱恙的南屏随侍暂且滞留罗平镇,待日后身体复原再由南屏专人将他们送还长乐。
容公子点头同意。
这些时日来,菡儿消瘦地消尖了下巴,我亲自把过脉,幸而并无大碍,但由着她继续衰弱亦然会危及性命。此时还在南屏境内,离那北燕都城尚有千里之遥,恐怕菡儿是无法再颠簸下去。我不敢想,如果菡儿不在了,那会有多可怕。长离长离,生离总好过死别。
我握着菡儿细瘦的手,轻轻跟她讲,“好菡儿,乖乖随其他人留下来,等身体好了就跟大伙一起回长乐去。”
菡儿蓦地抓紧我的手,眼睛里迅速蒙上一层水雾,大颗大颗的泪珠从眼眶直直地坠落,“小姐,小姐,小姐不要菡儿了吗?”
菡儿的眼泪打得我的心生疼,可是菡儿就像一朵清泠水间的一株莲花,离了生长的池水有怎么能过活下来?我的泪也错乱地淌下来,“不是的,不是的,菡儿!好菡儿听我说,小姐不是不要你了,小姐是希望菡儿健健康康。等菡儿身子好了,再来北燕找我。”
“小姐,菡儿撑得住,小姐就让菡儿陪着你,以后菡儿还能同小姐有个照应呀。北燕那么远就剩小姐一个人多孤单,就剩小姐一个人该怎么办啊……”菡儿一头扑进我怀里,身体因为哭泣颤抖着。我把脸靠在她的肩上,仍由眼泪不停的落下,手抚着菡儿的脊背,“菡儿,别哭呀,小姐是不会丢下你的,别哭呀……”明明是欺骗的话,偏偏想要让她安心,其实前路未卜,我也怕呀……
在罗平停了十天余,直到接到从长乐来的信报,说新皇南宫雨乔获准,前来罗平接滞留和亲侍者的车马已经在路上,不日便可抵达。而和亲队伍也不可继续耽误路程。
我们又再次启程,我并未说服菡儿留在驿馆,或许凭着自己医者的本事能让菡儿平安到达北燕都城。只是这样的赌注,让人隐隐忧心。
罗平镇外,丘陵荒草满目,隐约还有黄沙起舞,前方不远就是南屏西狄北燕三国交汇出,传说中通天的大漠,到这里就剩了个尾巴。
高耸的城门越来越远,这是真的离开了,百味杂陈的心,隐约地惊悸,又莫名的笃定。
还有三十五里才是北燕的驿站,此时暮色已经垂下。苍穹笼盖四野,星盈盈而稠密,这样的壮丽惊心动魄。
天边突然有鸟惊飞,“喈”的一声诡鸣,惊讶了静谧的黑夜。
菡儿不安地拉住我的手臂,我安抚地拍了怕她,却下意识的屏住呼吸,马车外面侍卫也都随着这声鸟鸣放缓行进速度,似乎周围都被凝滞肃杀的氛围笼罩。
宿鸟夜飞,必然是收到惊扰。我打开车帘张望,看见容公子一身黑色劲装飞快的对我使了个眼色。
果然!我心一惊,赶忙放下帘子。
“嘶”一支箭羽破空而来,插入肉体的钝响分外清晰,接着是躯体沉重的倒地声。车帘外是容公子低沉笃定的声音,“请曲小姐安心。”
夜行的火把点亮,火焰在乱风中抖动,人影趁在车帘上诡谲森森。
刹那间无数箭羽的梭梭声充斥着耳膜,车边的侍卫挥动着武器拨打袭过来的箭。幽闭狭小的车厢内感官敏锐无比,寒冷的箭头冷酷的武器尖锐的摩擦,所以的声音都剧烈的刺激着狂乱跳动的心脏。菡儿吓得张大了嘴却发不出半点声音,瑟瑟发抖的她竟不忘用自己的身体护住我。我拦着菡儿瑟缩在车厢底部。那些箭仍有从窗户散落进来。尖锐的疼痛从手背传来,我被流箭擦伤了,随着疼痛,一种近乎可怕的冷静慢慢在心底升起,凭借着一双耳朵紧紧抓住外面的每一丝声响。
刀划过皮肉的声音,厮磨成一种缓慢,缓慢地喷涌出鲜血。兵器碰撞,寒冷而决绝。然而,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听到车子周围的惨叫,只听痛苦的闷哼,随之而来是身体倒地闷响,或许接下来便是无声的生命消亡……
今夜遇上的绝不是盗匪,更有甚者便是传说中的死士,而护我和亲的这群侍卫亦不等闲。凝神静听,耳朵清楚的告诉我,外面最惨烈的恶斗分明是围绕在我的车子周围。莫非这场祸事因我而来!
马蹄杂沓,外面的人似乎又多了一些,打斗声紧密起来,却不知不知来者是敌是友。
“公子,请恕属下来迟之罪。”口音迥异的男声低沉沙哑透着懊恼。原来是北燕的援兵到了,我缓缓地舒过一口气,才发现周身早已被冷汗浸透。而菡儿早就颤抖成了一团,像小动物般低低呜咽,忽然怀里一沉,菡儿晕厥过去了。
不知多久,外面又恢复了安静,忽然有人拉开车门,“曲小姐,受惊了。”
是容公子,刚下的打斗让他衣着有些凌乱,手上还提着寒气森森的长刀。又看见他那沉静的目光注视着我,愣了一下,似乎刚刚的惊魂并未发生过,或者是阵疾风,刮过竟不着痕迹。手还在微微颤抖,想要站起身,才发现因为紧张全身早已僵硬,无奈地对着他开口,“烦劳公子先扶菡儿起来。”
容公子招来一名侍者抱起菡儿安置在另一辆车上,转过身来亲手要扶我起来。
“嘶。”手背上的疼痛让我不由倒吸一口气,刚才遗忘的疼痛感,瞬间变得无比清晰。
“医官!”容公子的呼喝声有点阴森,大概还未从方才的生死战中跳脱出来。
“容公子,小伤无须在意。”看着容公子严峻的表情我不由得轻声说道,一面试着把手从他的手里抽脱出来。其实伤口划过了整个手背,皮肉绽开,看上去还是蛮惊人的,方才在车中一直忘了理会,想不知流了多少血,现在反而有些凝合。只是,比起死里逃生,伤口确真真不值一提。
医官匆匆赶了过来,容公子拿过药箱一言不发的替我包扎。本来想说我自己也算是医者这点小事自己处理就好,可看着他阴沉的脸色,我也不好再出声讲话,好吧,被兵器所伤当然是武将医治起来最恰当。
“曲小姐方才可是受惊了?”容公子终于开口对我讲话了。
初见时的问话无非是礼数,这一句却是实实在在的关切。
我笑着摇摇头,“眼前的危及不是过去了嘛!”
容公子有用他那双如镜青瞳紧锁着我的眼睛,“原来小姐有这番胆魄。”
我无奈的摇摇头,“小女子最是胆小之人,因为无能为力,只好安下心来听天由命。”
包扎完毕,容公子放我在车中做好转身出去了。我惦记着菡儿,忙找出随身携带的药箱从车中走了出来。夜风凌厉的吹袭过来,不由得打了个寒噤。在火把映照下,我终于看清眼前的景象有多骇人。一地零落的箭羽,地上暗褐的液体成滩或是飞溅,更有破败的躯体倒伏在地上,致命的伤口皮肉翻卷,连着夜风都裹上浓重的血腥气味。
随行的侍卫有五人不幸死在了刚才的械斗中,还有十来个或轻或重负伤在身,重伤的侍卫被安排在后面车上医治,轻伤的侍卫就地坐下熟练的包扎伤口,没受伤的众人开始掩埋尸体。宋柯大人被保护的很好,除了有些狼狈,所幸毫发未损。
菡儿只是惊吓过度并无大碍,醒来片刻,又昏睡了过去。
一位年轻的劲装侍卫走过来对我施礼,“属下摩苏,见过太子妃。”
原来是刚才前来营救的北燕将军,我衷心施礼,“多谢将军。”
“恕属下冒昧,曲小姐看到这些不怕吗?寻常女子遇到今日之事怕是早惊恐万状,瘫倒晕厥,曲小姐却如此镇定自持,不简单,真的不简单!”
我抬眼认真的看着他,“将军,怕有用吗?”
摩苏爽朗一笑,“看来北燕迎回的真真是位奇女子!”话是对我说的,可他的眼睛却看向容公子。
我略略施礼,从他身边走开。
天边冷冷的月,冷冷望着人间。多想任由凄冷的风把骨肉都吹袭寒透,当心亦在风中冰冷,就会有眼泪有悲伤,就不会悲叹在每寸发肤间叫嚣,却不知该向谁怨怼。
若没有曲秧歌,就不会有今日之事。若没有曲秧歌就不会……泪在脸上铺洒,那些没有生命的躯体,孤零零的晾在惨白的月光下,我终于当年的弘儿和那些南屏兵士插满箭羽躺倒在这般荒原上,血一寸寸地渗入身下的土地……何以……
有人牵起我的手,温柔坚定的掰开我用力紧握的手指。
泪眼摩挲里我看见那人站在我的对面,披洒一身月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