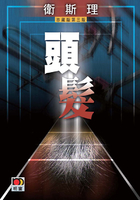“分家,不过了。我生了几个孽种,都他妈的没出息,全让老婆当驴使。”周老汉哭丧着脸,手中的棍子把地又捣得梆梆响。
“那你不给他们当家了?”乡亲们问。
周老汉把棍子狠劲往地上一捣,气冲冲地喊道:“不管啦——”
就这样,周老汉的大家分成了四个小家。经过家族里几位老人和村干部的调解分配,周老汉和老伴以平顶砖瓦房和已成果园的四亩承包地,外带几件农具灶具和一年的口粮单立了门户。分家最初的那一段日子里,周老汉不要说管他们儿子儿媳们的那些屁事,闲来喝茶晒太阳,连头都懒得往他们的方向转一下。开春犁地,积肥下种,锄草分苗,农括一茬接一茬,周老汉和老伴两人,除了给果树浇点水、施点肥外,还是喝茶晒太阳。这些年来指指点点惯了,看人家干不到点子上,嘴巴难受: “这棍子,这麻绳,这……都派不上用场。”一个春天下来,竟把挺富态的周老汉给急瘦了许多。端午节一过,他实在坐不住了,拄着棍子就往儿子们的地头上跑,边看边嘴里嘟哝: “你看这草。”“你看这谷苗东倒西歪的。”
“唉,这麦子重了行,这……这哪像个种庄稼的样子!”
“是不如您老当家那会儿了,你看你儿子种的那些地。”村里人的话更让周老汉心里不安,可这毕竟是分家另过了,周老汉有气也不能直接撒出来,他忍了忍,索性提上镰刀锄头,看哪里不顺眼就从哪里干起来。大儿子家的谷苗疏密不匀,他挨着给重新分了一遍。三儿子家的地里草称了王,他白天黑夜的去给锄了。二媳妇也一天几次地来找他撒农药化肥,说没有他这个老把式动手,今年这农药化肥肯定要把地里的新苗子一片片毒死,一块块烧死。就这样,到了秋收之后,三个儿子家的承包地收成,还是由村里的拔尖户落到了中不溜位置。
“怎么样?这叫女人当家驴犁地,不成。”周老汉终于让儿子媳妇们有机会琢磨琢磨他这死老头子的价值了。
最先感到没有周老汉不成的是二媳妇。她挥动着两片薄嘴唇,整天来找公爹,说没有了他老人家当家,日子过不下去,说把老两口放到一边不养活,心里过意不去,说最好是和她与二牛合家一起过。说了几十次以后,周老汉眉心渐开,脸上露出了笑容。
“那果园得给三牛。”周老汉似已考虑周全了。
“这……”二媳妇不吭声了。
“不过得把你妈派给大牛,这样公平些,我老汉一辈子就讲个公平。”
“那好,那最好不过。”二媳妇一听顿时高兴,连遮掩都忘了。
关于把苹果园给三牛家的事情,一说出来大媳妇就不同意,可周老汉一提起三媳妇流产的事情,她就不吭声了。大媳妇听说公爹把婆婆塞给她,狮子脑袋一甩,死活也不同意。这把二媳妇给急坏了,急得白天黑夜团团转,娘家邻里到处跑,都没个主意,跟看公爹抓脑袋摸鼻子的,似乎要改变主意,便咬了咬牙,直接去找她嫂子去了。
“房子和果园都归了你们,塞给我一个死老婆子,不干!”大媳妇任二媳妇的如簧之舌绕得再好,还是这句话。
“我说嫂子,你不是最讨厌烧锅做饭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喂猫喂狗这些破事吗?有了咱们那个妈绕着锅台转圈圈,又有一个能挣钱的男人,你能落个一身自在逛逛集不就行了吗?再说有老婆子在你这儿,那老头于还不把心往这里乘,还不来给你帮着犁地干活的,有几个男人不是围着女人转?平时你还落个人头少清闲……”
经二媳妇的两片嘴唇这么一拨拉,硬是把个母狮子给说动了,大儿子也托人带回话说他愿意赡养老母亲。“他狗小子不是靠他妈养老母鸡卖鸡蛋供他上学,哪能成公家人挣公家钱?他不养他老娘谁养?”周老汉以赞许的口吻一遍又一遍地当着恭维他处理家事妥当的那些人的面,大骂着他的远在省城的大儿子。
看来周老汉老两口又要和儿子们一起过日子的事情,已经成定局了。
“你们是否要合家了?”邻里们问。
“谁说的?我再不犯傻了。”
“那你这是……”
“我再不会做傻事了。儿子跟我亲,这媳妇跟儿子亲,可媳妇跟媳妇之间就不亲了。不亲怎么能凑成一家子?我是要和老伴分头去给他们帮帮忙,操操心,给他们做个主心骨罢了。”
“还是老队长想得周全。”
“那也用不着把房子和果园都交给他们。”又有人这样提醒他。
“嗨,我的就是儿子的,儿子的还不是我的?就是到他们门口讨饭吃,他们还不得给我一口?再说房子到哪儿我还不是住,果子下来还不是孙子们吃。”
“说得也是。”
就这样,周老汉指挥着老伴分头去给儿子们帮忙操心做主心骨去了。
果园给了三牛,周老汉个人的承包地从三牛家调整到了二牛家,这样二媳妇的心里踏实多了,再也不为八岁的儿子将来娶媳妇盖不起房子和死老头子不带承包地过来这些事情夜夜睡不着觉了,于是也有心情当着乡邻们的面,像鹦鹉一样不厌其烦地大表公爹当家的好处。她的话周老汉爱听,听起来舒心,听了后高兴得他嘴巴整日拢不上,跑起腿来屁颠屁颠的。
“年轻人毕竟年轻,看问题要有个过程嘛。”周老汉一遍又一遍地给他的那些老伙计们说。
新的生活开始以后,周老汉的心情也格外的舒畅,拄着棍子跑得更快,整天地颠来颠去,不是给地施肥,就是给果树浇水,要么就弯腰弓背地去拾麦穗谷穗,还要抽空跑到大牛三牛家的地头院落里去说肥道瘦和吆喝喊叫一番。他要让儿子家的农活都干在村里人的前边。要让自己供养过的那些田地重现昔日的风光。这样没明没夜地忙,可到忙得最舒心的时候,问题又出现了。
一天天下小雨,人们都闲着,二媳妇摇晃着两个肩膀走过来,冲着正弯腰提箩筐要给大牛家打猪草的周老汉喊道:“爹,你怎么老胳膊肘子往外拐,老跑去给别人干活?”
“怎么,我黑天半夜地忙乎,这家中里里外外的活,哪个不是我干的?”
周老汉理足,二媳妇出一口长气后转身走了。三天之后,她从集市上抓了两只小猪仔养在了家里,周老汉打的猪草就只好背回自家的院子里。
又过了几天,二媳妇看到这老骨头还挺硬朗的,给猪仔打的草堆得山一样高,又准备给大媳妇家犁地去。——大牛寄回来的钱买了一对大耕牛,有钱买的化肥多,这地里的粮食长得黄灿灿的,又有那死老婆子侍候着,这大媳妇狮子头梳得溜光,穿红戴绿的光知道逛集显人影。二媳妇越想越生气,心里早就忍不住了。看着公爹那殷勤样,气一下子就冒了出来,她跑过去夺过公爹手中的赶牛鞭子,大喊喝斥道:“去,老不死的,没事了洗石头去。”
“唉我的妈呀,这扫把还成精了。我活了六十多岁,还没有见谁吃了豹子胆敢这么给我说话。”
周老汉伸手提了提裤腰,右手执起棍子乱抡过去,打得二媳妇一阵乱跑乱叫。邻里乡亲听见后都跑过来看热闹,许多人都说周老汉的家法就是厉害,说人家毕竟是一辈子的队长出身,想当年四百多号人他说东都不敢西,哪能像有人说的几个毛头媳妇把他的威给灭了呢。周老汉听着心里畅快,身上的劲更足了,他提着棍子把二媳妇一连追了好几里,直到看不见人影才回来。回到家门口看到二牛低头掉脸不吭气,就没好气地骂道:“狗日的没出息,还不赶快把她休了,爹明年给你再娶一个黄花闺女。”
这一夜二媳妇没有回家。第二天天没亮,她的父亲来了。二媳妇的父亲是位闻名远近的屠夫,他晚上边翻肠子边听完了女儿的哭诉,听完后连手都没洗就摸黑出门上路了。他连翻了两座大山后直冲周老汉家的院门面来,连踹了两个木门,进屋后从炕上一把提起周老汉的衣领,一连就是几个嘴巴子,打得屋里臭气熏天。
“听说你老认为跟儿媳妇不亲是不是?说不亲都不亲,那你为什么要吃着我姑娘的饭,却偏要给你大儿媳妇犁地?你给我说说。我告诉你,你二儿媳妇跟你不亲,那可跟我亲,我今天就要看看你这个周扒皮是扒不成全村人的皮了,又怎么扒我女儿的皮……”
屠夫说得满嘴的唾沫星子乱飞,两只臭手抓住周老汉的衣领就是不放。周老汉的脖子快勒断了,他从牙缝里冒出几个字:“亲家,快……快死啦。”
“不是亲家是冤家。”直到屠夫的光头上蚊子打架,他才松了手。
太阳升起来了,漫山遍野的人都在抢种小麦。秋雨绵绵十几天,难得遇上这样的好天气,农民们都不愿错过好时机。可屠夫往门槛上那么一蹲,任二牛端水洗手送饭和磕头求情,就是不放周老汉出门,快到中午时他要去茅屋方便,顺手抽走了周老汉腰中的绳子,说:“你提着裤子去给你大儿媳妇犁地去吧。”
大媳妇在家里急疯了,一对大牛已套上绳索在院子里转圈圈,眼看太阳已挂中天,就是盼不到公爹来按犁把子。当她得知是妯娌做梗,便火从怒来,挥起鞭子打得黄牛直上墙。“妈的,没有男人老娘还不种地了。”她挽起裤腿自己赶黄牛上山去犁地了。这膘肥体壮的一对黄牛长年养在圈里,一出门就兴奋得摇头摆尾左蹦右跳,死活不走犁沟。大媳妇脾气大,牛的脾气更大,牛不走犁沟,大媳妇就晃鞭子,这鞭子一落,牛就像箭一样往前冲,一冲一停,一蹦一跳,犁过去的地弯弯曲曲生熟不均。山上山下的人看到这母狮子跟牛较劲,喊着喝倒彩,看笑话,把个母狮子婆娘整得栽跟头。大媳妇欲罢不能,只好扯开嗓子喊婆婆去帮她拉牛。
周老汉的老伴晃动着两条麻秆瘦腿,硬着头皮来拉这两头犟牛。可怜她刚抓住牛头上的笼套,大媳妇手中的鞭子正好落在牛身上。牛往前一冲,老太太的麻秆身体就被顶下了十米来高的陡坡,翻了几圈后落地,当场断了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