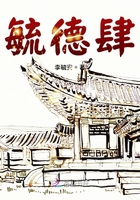大哥像被骨头卡住一样,愣在那里。好一会儿,我听到“叭”的一声响。那是大哥把碗砸了,那截猪爪子也滚落在地。大哥起身,回屋,甩上房门。父亲站在大哥的门前,张了半天嘴,终于转过身,将那截沾上泥的猪爪子捡起放在桌上。打那,父亲再也没吃过猪爪子。
第二天,大哥就离家去了南方。大哥到南方并没混出多少名堂来,最大的收获就是混回来我嫂子。回来后,大哥在村里做起了文书,后来不去了。大哥盖瓦房的那年,父亲曾送去两千块钱,被大哥冷脸推了回来。大哥说:“我们是仇人,我就是要饭也不会到您的门上去!”
果然,十几年,大哥再也没跟父亲说一句话。
这十几年,我们家也起了很大变化。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上了大学,还混成个作家,隔三差五在地方晚报上挤一块豆腐丁。于是,每天,在晚报上苦苦寻找我的豆腐丁成了退休后父亲的一大乐事。这几年,父亲的日子好过了,手头也小有积蓄。父亲经常对我说:“如果在十年前有这个样子,你哥就不会这样待我了。”
可是,毕竟,十年前没这个样子呀。
当然,这几年,我也曾多次劝过大哥,可大哥就拧着那根筋不放。没办法呀。
当父亲从伤痛的记忆中回到现实时,吴书记已经站起来,他说,“好,就这样吧。”
几个村干部又像泥鳅一样滑出窄小的屋门,滑到空阔的院场上。他们都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同时仰脸看天。他们的脸上像抹上一层脂膏,泛着油亮的光泽。不知谁踩着了花生,发出了一种清脆的声音。这时,他们听到屋里传出来父亲急急的声音:“吴书记,你等一下。”他们同时扭过脸。他们看到父亲从里屋出来,将一个纸包放在了吴书记的手上。吴书记接过来,握住父亲的手说,“邓老师,您是个好人呀,一品会理解您的。”这话是阳光,父亲的心像场上的花生一样,暖和起来。
只是父亲心里的暖意并没有持续多久。第二天,父亲到小街去卖黄豆,回来的时候遇到了我嫂子。嫂子跟我大哥一样,几乎不跟父亲说话。但那天,很意外地,嫂子说话了。嫂子说,“您上了那帮狗日的当了。”见父亲皱着眉头茫然不解,嫂子说,“一品曾给村里白耍了两年笔杆子,应该得八百块钱,可村里到现在一分钱没给。他们赖,我们凭什么不能赖。”
嫂子还说,“您教了几十年书,都教哪去了。”
父亲愣住了,父亲倒没有去计较嫂子那不合身份的语气。父亲真的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后来,父亲果断地回转身,拎着空口袋向小街上的村部走去。
直到下午,父亲才回来,据说是吴书记留他喝了酒。父亲不顾多年的胃病,喝了几杯。父亲对我嫂子说,“他们答应了,欠一品的工资一分不会少。”嫂子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很不屑地说,“那帮狗日的,没一个说话算话的!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但太阳真从西边出来了。当天晚上,村会计就将八百块钱送了大哥的手里。大哥和大嫂都有点发晕,他们都没有注意到村会计始终挂在脸上那诡异的笑意。
一连好几天,大哥和大嫂都处在一种晕晕乎乎的状态。
可是,村里又有了一种传言,说那八百块钱工资,其实是父亲垫上去的。为此,父亲还请在场的村干部们喝了一场酒,让他们保守秘密。村干部们也都当众拍了胸脯。
有人向父亲提起这事,父亲瞪眼说,“我怎么能做这样的傻事!”可是心里却骂,那帮狗日的,果然说话不算话。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快到十二点钟了。小村屋顶上的炊烟渐渐淡了,家家户户都端着碗围坐在自家树阴下的小桌旁。父亲从小街上回来,一路上,不断传来热气腾腾的招呼声:“吃饭啦,邓老师。”父亲微笑着表示谢意。
父亲的脚步移过大哥家的门口。从大哥家的屋里飘来浓浓的肉香味,那是熟悉的烀猪爪子的香味。父亲忍不住深深吸了一口气,眼里泪花闪烁……
我意识到自己身上有种使命,我相信它是我一切行动的内在动力。
爱心三明治/胡英
迈克尔·克里斯蒂亚诺在纽约市的一家法院供职。不论刮风下雨、阴晴冷暖,也不管是工作日还是节假日,他总会在每天凌晨4点起床,走进自己的三明治作坊。不,他并非熟食店老板,那只是他家的私人厨房,里面摆放着各式三明治馅料。他做的三明治已经小有名气,不过只为那些极需靠它们抵御饥饿的人熟知。凌晨5点50分,他往返于中心街和拉斐特街的临时流浪汉之家,那一带靠近纽约市政厅。一会儿工夫,他已送出200只三明治,力求在上班前帮助尽可能多的流浪汉,然后赶往法院开始一天的工作。
一切始于20年前的一次善举,他为一个名叫约翰的流浪汉买了杯咖啡和一只面包卷。从此,迈克尔日复一日地为约翰送去三明治、奶茶和衣物。最初,迈克尔只是想做件好事。
但有一天,一个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催促他采取进一步行动。迈克尔回忆道,“我意识到自己身上有种使命,我相信它是我一切行动的内在动力。”
迈克尔想到了制作三明治,就这样,他开始了自己的使命。他没有接受任何企业的赞助,他说:“我并不是想发起什么能载人史册或吸引媒体眼球的慈善创举。我只是想尽自己微薄之力做些好事,日复一日地坚持下去。但这的确是我力所能及的:从今天做起,从我做起。”
“遇到滴水成冰的下雪天,我实在不愿离开温暖的被窝和舒适的家,去市区送三明治。可每当此刻,那个声音又会在心里不住地催促,令我不得不起身行动。”
过去20年来,迈克尔每天都要做200只三明治。他解释说:“我分发三明治的时候,不是单单把它们摆在桌上让人来拿。我会直视每个人,和他们握手,向他们送上一天的祝愿。每个人在我眼里都很重要。我没有把他们当成‘流浪汉’,我只把他们看作需要食物充饥的人,他们需要一个鼓励的微笑,需要人和人之间美好情感的交流与传递。”
“一次,科赫市长跟我一起去派发三明治。他没有邀请媒体,就我们俩。”迈克尔说。与市长并肩工作固然难忘,但更令迈克尔难以忘怀的,却是与另一个人的合作……
常来取用三明治的流浪汉行列里少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迈克尔常常惦记着他。他盼望这个人的处境已经好转。一天,这个人出现了。面貌焕然一新,穿着整洁、保暖的衣服,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还带来了自己预备分发的三明治。迈克尔每天递送的新鲜食物、暖人心怀的握手、眼神中传递的关爱和声声祝福给了这个人希望和鼓励,这些正是他极为需要的。每天能感受到作为人的尊严,而不是被编人“另册”,他的人生因此被改写了。
此刻无需任何言语。两人肩并肩、默默无声地忙碌着,分送着他们的三明治。纽约街头又迎来了新的一天,所不同的是,这一天也承载了一份新的希望。
父亲步伐稳健,面带笑容,而母亲的手,正搀在父亲的臂弯里。
藏在拐杖里的爱/杜红
父亲是一个粗线条的人,脾气有些暴躁;母亲则是一个细致入微的人,性格又很固执。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总有吵不完的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父亲在一起意外事故中摔伤了腿。
事故并不是很严重,但父亲却有一段时间不能行动自如,必须拄着拐杖走路。我看见他在一瞬间消沉下去,苍老了许多,脾气也收敛了一些。而母亲也变了,从没看见她照顾一个人如此细心:每天给父亲端茶送水,陪父亲聊天;天气晴朗的时候,还会搀扶着拄拐杖的父亲到屋外散散步。母亲用她温柔执着的耐心一点点化解了父亲心中的失意。对于父母前所未有的和平状态,我看在眼里颇为惊讶。心想,或许因为父亲是整个家庭的支柱,他不能倒下的原因吧。
医生曾说,一个月之后父亲就可以离开拐杖的支撑了。可是一个多月过去,父亲的腿伤似乎仍不见好转,离开拐杖他就无法走路。母亲着急了,怕是伤口恶化,非要带父亲去医院检查。父亲这才悠悠地说:“拄拐杖的这一个多月,我好像又回到了年轻时与你相处的岁月。真希望每天在你的搀扶下去黄昏的夕阳中漫步,跟你平静地说说话。其实腿伤早好了,只是害怕丢掉拐杖就失去了你的搀扶。”我看见母亲的眼圈红了,我的心也湿润了。原以为吵了几十年的夫妻之间哪里还有爱情可言,它原来就深深地藏在父亲的拐杖里。
第二天,母亲精心地收藏好那支弥补了裂痕的拐杖,在温馨美好的夕阳中,又和父亲走在了屋外的那条小路上。父亲步伐稳健,面带笑容,而母亲的手,正搀在父亲的臂弯里。世事的繁杂琐屑,生活的磨难坎坷,粗糙了一颗颗原本温润柔软的心灵。
其实爱并没有远去,只是掩盖在层层艰辛之下。好在一个意外的创伤竟然修补了被岁月遗漏的爱与温馨。“牵手”成了一组永不褪色的照片。
她这是将生命送进狮口,为丈夫铺设生还之路。
狮口中的爱/左左
威尔逊和妻子驾驶着一辆满载生活用品的卡车奔驰在无边无际的热带草原上,他们要去处于草原深处的建筑公路的一基地。
就在这时,突然在他们的近前闪现出一头凶猛的狮子。卡车加大马力狂奔,试图甩掉狮子,狮子却紧追不放。
他们越是心急,令他们恼火的事情偏偏发生:汽车陷进一个土坑,熄火了。要想重新发动汽车,必须用摇把把车子摇醒。可狮子就趴在车外,眈眈而视。
大声吼吓,抛掷东西,两个人办法施尽,狮子却丝毫没有走开的意思。无奈中,威尔逊拥着妻子在车里度过了漫长难耐的一夜。可是狮子比他们还有耐心,第二天早上,这头猛兽还守在车外,向这两个要到口边的美味垂涎。
太阳似火,空气仿佛都在燃烧。妻子已经开始脱水了。在热带草原上,脱水是很可怕的,不用多久,人就会死亡。威尔逊只有紧紧拥住妻子,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不让死亡把她带走。此时,他们内心的绝望比狮子还狰狞。必须行动了,否则只能坐以待毙。威尔逊说;“只有我下去和狮子搏斗,或许能取胜。”其实两个人心里都很清楚,即使他们的力量加起来也未必抵得过那头猛兽。妻子像是在自言自语:“不能再呆下去,否则不是热死,也会筋疲力尽,最后连开车的力气也没有了。很多人都在等我们回去,再不回去,他们连饭都吃不上了。”
车外,狮子一点都没对他们失去兴趣,它欲耗尽对手的生命,以延续它的生命。没有刀光剑影,生与死在沉寂中却铿锵相对。
不知过了多久,妻子轻轻地说道;“我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快说!”威尔逊多么希望听到她能把他们引向生路啊!妻子默默地伸出双手,搂住他的头,深情地凝望着,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一定要把车开回去!”说着,眼里涌满泪水,嘴角禁不住地颤抖着。威尔逊突然明白了妻子所谓的办法,抓住妻子的肩膀吼道:“不行!不!”妻子扳开他的手:“你不能这样,不能冲动。你下去,谁开车?”她话没说完,就猛地推开他,打开车门,跳下去,拼命向远方跑去。
狮子随之跃起,疾迫而去。
她这是将生命送进狮口,为丈夫铺设生还之路。
一旦送去的财物用尽了,便“桥”断缘尽,而用你的关怀搭起的心桥,却会久久地连接着你和他。
真情人间/蒋梅
朋友从家乡回来,用平淡的语气给常胜讲述了一件事,听后他就忘不了了,而且心弦被轻轻地拨动:一个少年16岁那年离开贫穷的山村出外闯荡,近二十年过去了,他成了富翁,于是衣锦还乡,将一些礼物赠给了亲友们。有一天他怀着敬意去看望一位村办小学的老师,一个昔日曾结下仇怨的同学,因为他从亲人们嘴里知道这位同学在一贫如洗的境况里为孩子们牺牲了很多。他没有带任何礼物去。在同学寒酸的家里,两人由于长时间的分离与以往的隔阂没能聊上几句。后来,他又拜访了好几次,两人渐渐地聊起来,再后来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但这位富翁直至离开也没给这位老师带什么礼物。许多人对此不解。老师说:“也许他会给别人不菲的礼物,可他能抽空来我这儿聊聊表示自己的敬意,而且真正关怀我的生活,这便是他给我的最好礼物了,因为他把自己的真心当作礼物送给了我。”
常胜很佩服那位脱离了暴发气的富翁,他没有恃财做人,不靠散发钱财,而付出自己的真心,捎去自己的敬意和关怀。是的,一份真心的付出,可以拉近时光造成的距离,可以化解过去的隔阂,可以消除卑微和富贵的界限,在人和人之间架起一座相通的心桥。
不由得怜惜起人际交往里常有的失误,我们经常会以礼物的多寡来衡量一份心意的厚薄,除了这座物化了的桥梁,我很少想过把自己的真心关怀当作一份礼物送给需要的人,而是任其风化失落。一旦送去的财物用尽了,便“桥”断缘尽,而用你的关怀搭起的心桥,却会久久地连接着你和他。
十几年过去了,我总也忘不了那白色搪瓷杯里蛋炒饭的滋味。父亲错了,那实在是我一生中吃的最咸的蛋炒饭,因为他不知道,我在其中掺进了多少眼泪。
最咸的蛋炒饭/行树
父亲很少下厨。这事儿应归咎于我那烧得一手好菜的母亲对他的纵容。几十年来,父亲在厨房里只有过寥寥数次的“表现”机会。也真难为他能将每一盘菜都折磨得色香味形一塌糊涂,而且无一例外地挥“盐”如土,咸得我猛往肚子里灌水,活像烈日下拉车的骆驼祥子。
五分自知之明,三分乐得清闲,加二分不思进取,父亲“君子远庖厨”已经很多年了。但他那特色鲜明的菜肴风味,尤其是多年前的一顿蛋炒饭所留给我的记忆,至今难以抹去。
13岁那年的我突然不可救药地厌学,同时物以类聚地结交了不少热血沸腾的“狐朋狗友”。在十三岁的天空里,道德与法律的空气是稀薄的;周润发演绎的一个个快意恩仇、街头喋血的银幕故事,点燃了懵懂少年心中的英雄情结,真是“老房子着了火——没得救的”,一些天真而荒唐的错误就那么发生了。然后,当然是被发现了!东窗事发的我被迫转学到离家五十里外的一个县城中学。
我自由落体般的堕落速度让一向以我为傲的父亲目瞪口呆,一生好强的母亲更是气得病倒了。父亲破天荒的没有揍我,只是每天沉默寡言地照顾着惟悴的母亲,勉力经营着咸得发苦的一日三餐。压抑的气氛让心虚的我喘不过气来,于是当其他同学尽情享受双休日时,我却在热切盼望每一个周一的来临。
某个周一的早晨,我顶撞了父亲几句,早饭也不想吃,就匆匆搭乘班车赶回学校,肚子里装着一副富有叛逆精神的漉漉饥肠。
第二节课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发现有同学向教室外探头探脑地看;循着他们的目光,我看到父亲来了。他显然不想打扰正在上课的老师,所以只是静静地站在窗外,手里还捧着一个很大的白色搪瓷杯,杯口上用橡皮筋蒙着一小块报纸。
然而,老师终于发现父亲了:“您有事吗?”我垂下头,耳畔隐约传来父亲的声音:“……早晨没吃饭……孩子胃不好……送点儿饭……”我暗暗埋怨父亲“真鸡婆”,害得我在同学面前好没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