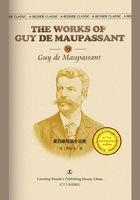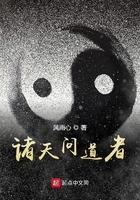在非常情况下做上了领房人的二斗子并没有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仅仅在第二年就出了事。我们早就说过,自古以来驼道就非是安靖之所在,比如驼队被强盗所劫,比如遇上黑沙暴驼队在沙漠上迷了路或是不慎让驼队在不宜扎房子的地方休息,骆驼吃了断肠草、喝了有毒的水……;真可谓是七灾八难时时在等待着你。
二斗子刚当上领房人的第二年就在走新疆的时候遭遇了一场大沙暴。那是在乌兰布和沙漠的边缘,突然刮起的大风迫使行进的驼队停下来。人都藏在了卧倒的骆驼肚子旁边。就是到了世界末日,连天接地整个世界全都变成浑黄的颜色。分不出上下,分不出东南西北;就像有一个巨人在天上向抛下土似的。很短的时间内落在人身上的尘土就积得非常沉重。货驮子上、行李上、骆驼的身上。翻滚的沙尘逼得人睁不开眼。张不开嘴,喘不过气来。尽管这样嘴里仍然塞满了沙子。本来是一个中午的天气,却是只隔十几步就对面看不清人。空中飞漫着黑色的沙粒,只有最近的距离内才能免强看到形体巨大的骆驼的身影。也只不过是浓雾中的影子似的。
“二斗子……”
不知谁在喊。但是人的呼喊声显得十分可怜,瞬间就被呼啸的沙暴吞噬了。风的呼啸声充斥了整个世界。
所有的人都原地爬着,不敢轻易走动。眼看着驼屉被风刮走也没人敢去追。若是离开大家哪怕仅是一瞬间的功夫,就可能永久地失踪。沙暴之后驼夫掌柜们一个个从沙堆下面爬出来,抖掉身上的沙土,向一起聚拢。
沙暴将人的面目都弄得无法辨认了,眼睫毛嘴巴周围全都被沙土涂抹,彼此没有差别了。一个声音玩笑着说:“我们全都是土地爷的儿子了。”
另一个凑近说话的人拿手在对方的脸上摸着奇怪地问:“你是谁?”
“他妈的!连我也认不出来了?认不出来你还听不出来吗?”
“认不出来,就象你说的我们都成了土地爷的儿子了。声音也变了。……等等,你好象是刁三万吧?”
“日他,还能是谁。”
于是大家都笑了。
二斗子喊道:“赶快清点人和骆驼的数目。”
人们也只是根据矮小的个头认出说话的是二斗子。
还好,贴蔑尔拜兴的驼夫、掌柜全都是常年在驼道上跋涉的老手,竟然没有损失一人一驼。待各家的掌柜把清点结果报上来,二斗子长长嘘了一口气,说:“关老爷保佑!起程的时候没有白给你老烧香磕头。”
但是刚打算上路的时候,驼队已经开始移动了,蹇二掌柜突然跑到二斗子跟前拉住了他的马缰绳。
“出了什么事?”
“我的一条花狗不见了!”
“不能吧?你再找找。”
“找过了哪都没有。”
二斗子邹着眉头翻下马背。
外人有所不知,护卫狗之与驼队那可是重要得很,狗是驼队保卫力量,其重要某种程度比人差不了多少。
二斗子招呼大伙帮助蹇二掌柜找狗。很快就在一个巨型的沙包上面找到了。准确地说大家找到的已经不是一条狗,而是被沙暴的力量剥得干干净净的一付白森森的骨架!
蹇二掌柜是从那狗的牙齿上认出是自家的花狗。兀自哭了一阵之后把狗的骨架就地掩埋了。
真正可怕的事情发生在驼队起程之后。由于风暴改变了地理地貌二斗子找不到路径了!就是说驼队就迷了路。于是驼队在大漠里打起了转转。
两天后严重的后果出现了,第一个牺牲者倒下了,是一只年老的护卫狗。二斗子听到一个男人粗野的叫骂声:“二斗子,你这个小王八蛋!都是因为你,害死了我的狗!……”
相比而言,在驼队中生命力最脆弱的除了马就是狗了。马只有领房人骑的一匹,因为有特别的呵护——水和料能够得以保障不容易出事。狗就不一样了特别辛苦,体力消耗也大因而最容易牺牲的往往是狗。
二斗子没有回头他不用看,单凭着那汉子的哭声他就猜出来那是刁三万。
驼队停下了。
刁三万一阵旋风似的扑向二斗子,抓住二斗子的衣领,声嘶力竭地喊道:“二斗子,你赔我的狗!你算什么领房人?!呜呜呜……”
二斗子被疯狂的刁三万摇晃着,面无表情。
刁三万就像狼一样放开嗓门嚎啕起来。
一只大手拧住刁三万的手腕把他和二斗子分开了。痛苦中的刁三万扭头看看见是胡德全。
“刁掌柜,你不想活了?这样大声地哭闹,你知道这样会消耗多少体力吗?”
刁三万跌坐在沙堆上,立刻不响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只死狗,从旁边看上去就像是一樽木头刻成的人似的。
“我做领房人还没出二年呢……”二斗子喃喃地自语着,“我咋这么不走运?刚刚没了把兄弟海九年和师傅没几天就把驼队带入了绝境。”
“我们不能就这么等死,”休息了一会儿胡德全从地上爬起来问二斗子。“好歹你也是个领房人,你好好往四下里看看,哪个方向是北?”
二斗子站在一座沙丘上往四面望了一会儿,回到胡德全的身旁。他指了一个方向说道:“那边。”
“这回你可认准了?”
“我认准了。”
在驼队移动之前,刁三万用铁锨镢了一个坑,把他的爱狗掩埋了。吝啬的驼夫爬在狗的坟堆上哭了好半天。
驼队又缓慢地移动起来,没有歌声没有人的说话声甚至连狗都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悄没声儿地跟在驼队的旁边走着。驼铃声有气无力地响着,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传来似的。……
只有人驼狗夸张地喘息声在沙漠的寂寥的上空回响着。
二斗子看见蹇家老三和胡德全段五十六都使自己的驼列停下来,把自己家的一只护卫狗抱起来,放在了一峰骆驼背上。
晚上。临时扎起来的“房子”中,挤在一起的驼夫们想起了家。想起了那个偎在大青山脚下的可爱的村庄,想起了村中的女人和孩子们。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谈起了各自的孩子老婆,都说起自己老婆的好话来了。就连脸上布满了麻点字的麻三婶在丈夫刁三万的嘴里都变成美女了。“你们可是不知道,我那麻脸老婆做起家务那可是一把好手哩。”
不知怎么的驼夫们就把议论的话题转到了戚二嫂身上。
刁三万问胡德全:“说说吧,”
“你想听什么?”
“就说说你和戚二嫂的事,都把人馋死了!”
“你他妈的忘记了死了?”胡德全骂道。“这都性命攸关的时候你还说什么女人!”
“听一听就是死了也无怨了。”刁三万转向二斗子,“都说你和戚二嫂早就有一腿了,是真的吗?”
“不是真的怎样,是真的又怎样?”
“我就想听听,嘻嘻嘻,没别的意思。”
刁三万拿舌头舔着满是黄色燎疱的嘴唇。
“是真的。”王锅头望着刁三万的嘴替胡德全回答说,“你就当作是对一个垂死人的最后要求,满足他的愿望。”
“哇!你真的上过了?没骗我?”
“真的,不骗你。……好!他妈的我这一生要是能上一回死都闭眼了!”
“还是你小子有福气”刁三万没听清楚胡德全的话,兀自感叹道,“唉,其实我也下了不少功夫,到了也没弄成。……”
睡到半夜刁三万突然惊叫起来,他的神经有点不正常了。要水,一个劲儿地要水。嘴里不停地喊:“我要喝水!我要喝水……”
听到动静王锅头爬到刁三万的跟前。
晚上蹇二掌柜的另一只狗也死了。那只狗像人似的坐在骆驼的背上走了几百里冤枉路。
人们都进入到可怕的半疯狂的状态。蹇家兄弟给死去的狗剥了皮,架在篝火上烤。肉还半生的呢蹇二就开始吃起来,他嗄嚓嗄嚓地咀嚼着,他把狗肉里的水分咽进肚子里去,将嚼成干柴似的肉渣“噗”地吐出去。
骆驼尿也成了珍贵的饮料。
戚二掌柜跪在一峰骆驼的肚子旁边,手里拿着一个牛皮水袋等待着。他把骆驼的尿接进了牛皮水袋里,还没等骆驼尿暄嚣的黄色泡沫沉淀下去,就不顾一切地喝起来。
那个火一样的中午,太阳悬在人们的头顶,那奇怪的圆球一会儿是黄色的一会儿又变成了黑色的,在人们的头顶上肆意地呼啸着、旋转着,就像是一个法力无边的魔鬼在施展着它的威力;无有穷尽的热量从令人眩目的天上一批批倾泄下来,热蒸烤着大地,沙漠就像被煮沸了的黄色的大海,沸腾着翻滚着。一缕缕的蜃气扭摆着婀娜的腰肢就像是魔鬼宫殿里的一群舞女在这里在那里摇弋、舞蹈。到处都是令人头晕目眩的金黄色,到处都是无边无际的黄色的炎热,人们身上的水分、意志和希望正在一点一点地被耗尽。
不远处有两座沙丘就像巨鲸翘起的尾巴,无动于衷地在那里迎住了驼队。就在那两座沙丘的中间驼队倒下来。驼夫们都喘着气倒在了地上,几十张被汗水和尘土涂抹得脸脏兮兮的,变得陌生了,全都是野兽一样的表情。大家沉默着,在沉默中等待着死神的降临。没有止境的跋涉耗尽了力气的骆驼们都失去了往昔的风彩,全都自动卧倒了,护卫狗们一个个都躲在庞大的骆驼身旁边,在阴凉地儿里把长长的红舌头伸出来喘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