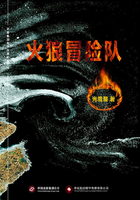秀儿过门之后便被村人称作戚二嫂。戚二嫂的公公戚五十六自年轻时候起就是吃驼道饭的,拉骆驼一干就是几十年。给两个儿子都娶过媳妇,辛苦了一辈子的老驼夫也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不久就去世了。风里来雨里去戚五十六拼着性命拼着血汗挣下了一百二十峰骆驼的家业。临死前戚五十六把两个儿子叫到跟前,亲自主持着给他们分了家——不偏不倚一百二十峰驼的家业一人一半。
末了老人拉着二儿子的手说:“我本来盘算着给你再盖一处院子,可惜来不及了……。爹对不住你,你自己张罗着盖吧。谁都知道的,你哥他能耐不如你还不争气染上了大烟瘾。这处院子就留给你哥。你的宅基地爹已经替你看好了,那地场就在村子东边挨着刁三万家的院子。我请王锅头看过风水了,王锅头看得仔细呢,说那是块好地场。”
戚二嫂和丈夫跪在炕前泣不成声。
老驼夫又说:“别怪怨爹,你妈她死得早,……。往后你们哥俩要好好处,你哥他不如你,我死了他能守得住分在他名下的这些骆驼,不受穷苦,九泉之下我也就放心了!”
或许是老驼夫原本就没抱什么指望,他没来得及听完大儿子指天划地地向他发誓许愿保证戒掉大烟辛勤劳作,便咽了气。
果不其然,戚五十六死去还没有一个月,戚老大的大烟瘾便又发作了。开始是悄悄抽,隔个十天八日的寻个借口到城里的烟馆过过烟瘾。后来渐渐地就又管不住自己了,隔三岔五地往归化城的烟馆里跑;没有银子就把自家的骆驼牵去卖了换大烟抽。没有多久就把父亲留给他的那六十峰骆驼全都化作蓝幽幽的毒气吸进肚子里去了。再没有什么可变卖的东西了,戚老大就开始偷;不管是左邻还是右舍,见着什么拿什么。偷到后来就偷起了骆驼,公驼母驼健仔驼只要遇在他的手里捉住了就牵到归化城的驼桥上换了大烟。
戚大做这些事都选村里的驼队走外路的时候,男人们都不在,被偷了驼的人家就去寻戚二嫂。戚大是丈夫的亲哥,这事戚二嫂不能不管没办法只好把自家的骆驼让人家牵了去。一个秋天和一个冬天戚二嫂替大伯子抵债损失了自家的三峰小驼。……
……
但是等戚二从驼道上回来,事情立刻就爆发了。正是黄昏时候戚二走向驼圈,一看到自己家的骆驼不够了数,立刻就向老婆发了火。
“咦!咱家的骆驼咋不够数了?”
“这事么,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你立马给我说清楚。不然我可是饶不了你。”
戚二嫂陪着笑脸拉着丈夫的袖子:“有什么话咱回屋里再说。”
“那不行!”戚二一扭身子把戚二嫂甩开了,“我的驼都哪儿去了——你立马就得给我说清楚!”
“干什么呀你这是……,”
戚二嫂依旧是陪着笑着,面色桃红撒着娇去抓戚二的手。
戚二掌柜啪地一下把媳妇的手甩开了,吼道:“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你立马给我说清楚!”
红晕迅速地从戚二嫂的鼻梁上向两腮消退下去,她的变白的双唇抖动着,吐出来的字已经是冷冰冰的了:“你想知道我就告诉你,那些驼全都被你哥哥换了大烟抽掉了。”
“什-么-?!——”戚二掌柜一下扑到戚二嫂脸前,眼睛瞪得牛大牙齿咬得咯吧咯吧响,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戚二嫂说:“我还不是为了你,戚大再不好也是你的亲哥哥,俗话说一笔写不了两个戚字,他的事别人可以不管,咱不能不管。再说了你又不在家,我撒手不管还不让人笑话我,你脸上也不光彩。……”
“我要那光彩熬蛋吃!一滴汗珠摔八瓣儿,那些驼是我流了多少汗水才换回来的——你不知道吗!你这个败家的玩意儿……”
戚二掌柜伸出手一推,毫无防备的戚二嫂便倒下去在尘埃里一连打了好几个滚儿。
性子起来戚二掌柜脚步咚咚地走进哥哥的院子,将骨瘦如柴的戚老大一只手提溜着牵到院子里,简单地问了几句抬手就扇耳光子。直打的戚老大口鼻流血痰倒在地方才罢手。众人好说歹说把戚二掌柜拖出了戚老大的院子。
曾经在许多个失眠的夜晚被戚二嫂热切盼望着的久别胜新婚的激动人心的场面没有出现。当天晚上,被失去心爱的骆驼折磨着的戚二哭了几乎一整夜,他的哭声像狼嚎似的冲撞着房间的四壁和顶棚。
三天之后他们夫妻和解了。夜里,戚二嫂冷淡地偎在丈夫的怀里,听戚二解释着:“……咱哥是个败家子,他染上了大烟那就是没救了!你管得了他一时,能管得了他一辈子吗?既然他能把自己的六十多峰驼都抽没了,他也就能把咱家的这些驼都给你抽光!咱能陪伴得起吗!?”
第二天戚二就向村人郑重宣布:往后戚大的事他不再管,任戚大偷了谁家的东西他戚二概不赔偿!谁也别再找他戚二的麻烦。
戚二放出这话不久,戚老大就因为偷了胡德全家的一峰崽驼被打折了腿。
胡德全是村子里仅次于养驼首户蹇家的养驼大户,拥有健驼四百余峰;胡德全本人还担任着贴蔑儿拜兴村驼队驮头的重要职务。贴蔑儿拜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村庄,村中清一色住的全都是养驼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驼运专业村。这个村子的养驼户集体加入了归化城的万驼社,一应业务往来全都由驮头胡德全负责联络、组织和安排;除了胡驮头贴蔑儿拜兴村再没有其他的行政负责人,因此驮头的权威在贴蔑儿拜兴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
胡德全本人生得熊腰虎臂,身高在一米八零以上,浓眉豹眼,左脸上斜着嵌着一道刀痕那是十几年前在驼道上暴客留给他的纪念。那一次贴蔑儿拜兴的驼夫在胡驮头的带领下与抢劫驼队的土匪整整厮杀了一个下午,胡驮头手里的黑蟒皮鞭在暴客们的头顶上“嗖_嗖”嘶叫着,那一天黑蟒鞭是既啃骨头又咬皮直打得暴客吱哇乱叫好似鬼哭狼嚎。好一场恶战,当下死在胡德全的蟒皮鞭下的暴客就有三个;被打折了骨头抽得浑身鲜血淋淋的暴客更是难计其数!那一场厮杀使胡德全的名声传遍了归化驼运界。戚老大偷东西偷到了胡德全的头上算是兔子撞到枪口上了该着他自找倒霉;当下胡驮头掐着戚老大的脖子带他去见戚二掌柜。
“戚二掌柜,你哥他偷了我一峰半岁崽驼换了大烟抽了,你管还是不管?”
戚二正在自家院子里的马厩旁给他的杏黄马拾掇鞍具——他要进城去办事。他从马肚子下边看了看,见自己那不争气的哥哥被胡德全像掐小鸡似的掐着脖子在往院门前推搡。戚老大又瘦又细的脖子被胡德全的大手掐着只能喘上半口气来,抽抽着嘴巴一个劲儿地朝他弟弟眨巴眼睛。
戚二掌柜没有搭理他哥,继续着他手里的营生。
胡德全又说:“戚二掌柜,你说这事该咋办?……我等你一句话。”
村子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有几十号人围在胡德全和戚老大的身后看热闹。戚二掌柜觉得心里非常别扭脸上就有些发烫,但是他没有发作,压了压性子朝胡德全看看又瞄了瞄他哥戚老大,答复道:“我说过了,今后我哥的事我一概不再管。我戚二历来说话算话。”
言罢戚二掌柜不再搭理胡德全,只管使劲勒着马肚带,也不知道是手劲使得太大了还是怎么的杏黄马很不舒服地直踏蹄子。戚二掌柜将缠在掌心的马缰绳往怀里使劲一揽,杏黄马就老实了。扣好了马肚带戚二掌柜又把马鞍子朝正了搬了搬。
“你当真不管你哥的事?。”胡德全又追了一句。
“吐口唾沫是颗钉——我戚二的脾性胡驮头你该知道的——请别再废话!”
“那好,”胡德全说,“你把话挑明了就好,那么我怎么处置戚老大你就管不着了,话我可是递给你了,你别怪怨我!”
胡德全手指头一使劲儿,戚老大疼得嗷嗷叫起来。
“你别吓唬我——没用!愿告官愿私了随你胡驮头的便,我哥的事与我戚二无关。”
戚二抻了抻缰绳牵着马走出了院子。
眼睁睁看着戚二掌柜从自己脸面前走过去,胡德全恼了,说道:“哼!让我告官,我才没那么傻呢。一峰骆驼的钱不够给二府衙门的官老爷抹油呢。——我要你哥的一条腿!让他以后长点记性,看他还再敢偷我胡德全的驼!”
“随你的便!”
戚二掌柜纫镫攀鞍翻上了马背。
戚二掌柜抖了抖缰绳,催动着坐骑从胡德全的面前走过去了。
但是还没等戚二掌柜的杏黄马走出几步,一阵鬼哭狼嚎般的惨叫就像旋风似的蹿起来。杏黄马被那陡起的怪叫声骇了一跳嘶鸣着竖起了前蹄,没有防备的戚二险些被掀下马背。戚二在马镫上站了起来胸脯紧紧地贴在了竖起来的马脖子上,他控制住了自己的坐骑,把缰绳狠狠地往怀里搂着,听了听身后的动静,接着又催动着马走起来。
人群发出一阵阵的惊叫。被惨烈的情景吓坏了的小孩子“哇哇”地哭叫起来,女人们都拿手捂上了自己的眼睛。
戚二嫂扑到院门外面喊道:“戚二!……你回来!——”
戚二掌柜好象什么也没听见,坐下的杏黄马却越走越快了。
“戚二!——你哥的事你不能不管!……你这畜牲!……”胡德全冷笑一声说:“骂得好!……戚二嫂。骂得好!”
戚老大抱住一条折断的腿身子缩成了一团儿,惨叫着在地上打滚儿;衣服上裹满了尘土,被剧痛逼出的汗珠子像黄豆一样大在他蜡黄的脸上迸溅着,鼻涕眼泪都出来了。
胡德全冷眼看着在他的脚下翻滚着的戚老大,说:“这是第一次,只要你一条右腿。下次再敢胡来,我就再打折你的左腿;我把话撂在这儿了——俗话说得好,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倘若是第三次让我抓住,就折断你的脖颈!……”
话音未落,就见戚二嫂像股迅疾的旋风冲向了胡德全,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也不知道戚二嫂是用手推的还是用头撞的,众人就看见胡德全“咚”地一声跌坐在了地上。
胡德全被戚二嫂的突然袭击搞懵了,愣在那里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好,只是直着脖子听戚二嫂叫骂。
“姓胡的!——你也不是人!……你和戚二一个样你们都是畜牲!”
胡德全嗖地一下窜起来与戚二嫂扭打在一起。
他们一起在土地上翻滚着,一会儿你把我压在身下一会儿我又骑在了你的上面,“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同时在嘴里断断续续地咒骂着对方;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的一来两个人互相撕扯着一起从地上站起来。戚二嫂的一只眼睛肿胀起来眼见着就现出了青色,胡德全嘴角上淌出了血,两个人同时拿双手狠狠地揪着对方的衣领不肯放松,四只强有力的胳膊像麻花似的拧结在一起。就那样相互揪扯着在人群围成的圈子里忽而东忽而西忽而左忽而右地打着旋子。
围观的人一会儿像受惊的鸟儿惊散开去,一会儿又聚拢过来;村子的上空飘旋着女人的尖利叫声、孩子的嚎哭以及男人们的各种嗓门的一阵阵沙哑的呐喊:
“啊!……啊……停下!……”
“别打啦!……”
“要出人命啦……”
“流血啦!……不得了哇……”
“刁三万——你他妈的看什么热闹——快上前去拉架呀!难道你没看见吗,这里除了女人、娃娃和老头子就只有你一个壮汉了,你还看什么!?”
一个麻脸妇女拿放驼用的哨棍敲打着身边的中年人的脊背,把他推出了人群。
这个名叫刁三万的驼夫汉子长着一颗南瓜似的长脑袋,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与脑袋同样粗的脖子像狼一样不能够自如转动,这是因为在他的脖子两侧一边长着一根结实有力的大筋,两根大筋直接将他的脖子固定在了脖子上;这样他要想朝后就必须先扭转肩膀,这样的动作非常像狼,于是人们送他一个外号——狼人。
由于紧张狼人刁三万的脖子上的那两根粗壮的筋络绷直起来,他扭转了肩膀朝自己的麻脸老婆看了看,犹犹豫豫地走向打架的人;同时把两只粗糙的大手攥成疙疙瘩瘩的拳头。“他妈的!我说——别打啦!……”
打架的人对刁三万的话根本不加理会,好象没听见一样继续扭打着在人群围成的圈子中间旋转。显然无论是胡德全还是戚二嫂都不把刁三万放在眼里。狼人刁三万说话没有分量,在贴蔑儿拜兴刁三万只是一个仅有三十几峰骆驼的小驼户的当家人。
过了两袋烟的工夫,蹇家老爷子跟在王锅头的身后到了。人群闪开让出一条道,白头发白胡子的蹇家老爷子拄着拐杖走进了圈子里。
蹇老头八十多岁的年纪,中等身材,面色苍古,清癯而削瘦的脸上有一双鹰鸷般的锐利眼睛;在胡德全之前贴蔑儿拜兴驮头的职务一直是由蹇老头担任,历时有二十年之久。蹇家有八个儿子且个个如虎狼一般强壮,其中蹇大在父亲交卸驮头职务时意欲继承父亲的职位,但是蹇老头说:“出头的鸟儿挨打,出头的椽子先烂;……。”
老头子制止了自己的儿子,把权力交在了胡德全的手里。这是蹇老头积半生经验做出的明智之举。蹇老头虽然放弃了驮头的职务,可是蹇家在贴蔑儿拜兴的首户的显赫位置却无人能够替代——蹇家拥有骆驼八百余峰占去驼村骆驼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强,再加上蹇老头膝下有八个儿子个个如狼似虎,其势之大没人可以动摇。所以说来说去贴蔑儿拜兴的事情最终还是蹇老头说了算。蹇老头放在手杖上的手有规律地颤动着,另一只手掠掠胡子,厉声喝道:“都给我松手!……你们是吃了疯狗肉啦,还是咋的!?……简直是无法无天啦!”
蹇家老太爷一挥拐杖,跟在老爷子身后的蹇老大蹇老二蹇老三蹇老四蹇老五蹇老六蹇老七蹇老八呼呼啦啦地拥上前,七手八脚嘁哩喀喳立刻就把胡德全和戚二嫂分开了。
蹇老头把胡德全和戚二嫂带到村子北边的关帝庙跟前,老头子自己在高高的台阶上站好,居高临下地望着并排站在台阶下的胡德全和戚二嫂,问道:“这件事你们是愿意经官呢还是愿意私了?”
“愿听蹇老太爷发落。”俩人同时回答。
“好!”蹇老头说,“那我就裁决了——戚家老大偷了胡德全的骆驼理应照市价赔偿;胡德全打折了戚老大的一条腿理应为其疗治;戚老大赔偿胡德全的骆驼钱与胡德全为戚老大治伤的钱相抵,现在你们两清了,从今往后谁也别再找谁的麻烦。……散了吧!”
一场争执就此了结。
过了三个月,在驼队即将起程的时候胡德全又一次来到戚家,他们和解了。在驼运业务上胡德全特意地给了戚家些许照顾。
但是戚二夫妻之间却因此而结下了怨怼,当夜戚二嫂拒绝了戚二的亲热,她把自己的行李搬到大红躺柜上去了。对丈夫的厌恶在戚二嫂的心里从此牢牢地扎下了根。
贴蔑儿拜兴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在一座座赭黄色的房屋里男人们女人们和孩子一起消磨着许多个相同的白天和夜晚;但是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在每一个贴蔑儿拜兴人的梦境是多么的不同,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的梦中都会出现骆驼;没有骆驼的人在企盼着拥有自己的骆驼,而有骆驼的人则盼望着自家的骆驼越来越多!
可怜可悲的戚老大整整在炕上躺了一个月不得动弹。直到两个月的头上村人才看见戚老大在村中露面,他拄着一根红柳枝拐杖横着身子在村道上一挪一挪地移动,已然是衣衫褴褛面呈菜色没了人样,谁见了他都避着走。好端端的一家人家就这么败了,眼看着日子没了希望,灰了心的戚大老婆就跟新疆来的一个驼队走了,去给一个哈萨克族的驼夫做了老婆。又过了不到一年,戚大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