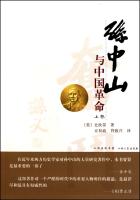“呃,呃!不行,不行。”许夫人拉住郭德洁的手说,“白夫人一开始就订了个规矩的,不行中途退场哟!”郭德洁难为情极了,硬走吧,不妥,这不得罪了三位夫人吗?三张女人嘴,当得三把刀,日后不知被说成什么样子;不走吧,这样有天无日头地和她们搓下去,“饱汉不知饿汉饥”,她们倒是逍遥,哪知道你心急如火呢!
“三位姐妹,实实在在,我还有事。”郭德洁神情已经有三分躁绪,“要不,就照白夫人定规矩讲的,罚我的款好了。”“罚,重罚。”王夫人笑着,“你实在要走,罚20 块大洋。”“20 不行,李老总大把进钱,要罚起码罚50 !”“嗯,嗯……”郭德洁支支吾吾,急得眼角都有些湿润了。
马佩璋见她这个样子,也不好再强行硬留,笑道:“罚款的事,我只不过说说而已。我们这些人也不愁吃穿,只图个好玩吧!德洁要走,究竟有什么要事,恐怕不是军事机密吧?”“一定是李老总明天离桂了,今夜要多陪陪。”许太太俏皮劲起来,不顾那么多了。
“是啰是啰,只要她承认是这个原因就放行吧!”王夫人见不好再僵持下去,想打圆场。
众抬一,郭德洁估摸僵持下去无益,又不好发火,归心似箭,只好支支吾吾地似承认非承认地点了点头,破涕为笑,急冲匆匆地走出门去。
“德洁,德洁!”马佩璋见郭德洁不辞而别,果真要走,急追出门去,叫道,“你真就走了?等下张师傅那米粉担来,我请你们吃牛腩米粉!”“多谢了!多谢了!”郭德洁哪里还肯再留。只侧过身,招招手,不停脚地往院门口走去,远远地还留下一句,“白夫人,明天的庆祝大会,你可一定要来啊!”军号声毕竟是能够激励和振奋人心的。省公署大楼前的宽阔广场上,人山人海。着灰军装,戴捷克钢盔的兵士;穿短制服,戴布军帽的学生;穿长衫的公务人员和教师,还有那些穿蓝着黑的市民,各个眼里,都闪射着激奋的光——“七七事变”,全国宣布抗战后的第一个双十国庆节,民族的魂灵,民族的尊严,若无形而强有力的风,把国民心中抗击侵略者的帆满满地鼓起。省公署大楼前那根高高的旗杆上,一面青天白日旗在并不寒冷的北风中飘扬。
大楼前的平台上,扎起了双层三开的松门,虽然纸花和小彩旗点缀得有些过分,但登上这平台的石栏云阶,却显示出非凡的庄严。这里曾是明朝时的靖江王府承运殿,殿宇虽几经重修,这云阶和石栏却风雨不动,水火无伤。
松门上方,悬着块红底黄字的横幅,“庆祝中华民国廿六周年国庆暨欢送李宗仁司令长官北上抗日”两行方块大字,赫赫醒目。
没有太阳。本该是爽朗的桂林秋日,天却灰灰白白,幸好北风给人几分爽意。
松门前的两溜长条桌旁,已经坐着不少军政要员和地方名士。省主席黄旭初着一身藏青色中山制服,坐在前排的左侧,头发剪得很短,那双沉稳得有些狡黠的眼睛,不住地盯着广场的侧门。他是在等待李宗仁那辆灰黑色的美国吉普。说定了八点半钟,大会准时开始,现在只差五分钟了,他心里不免有些焦急。
军号一阵阵地吹,军人和学生和着节拍,唱起了歌,多是鼓动抗日的,有的歌是从陕北那边传来的,群情激奋,歌声荡漾着一种民族气概。
正在这时,李宗仁和郭德洁从松门内走了出来。和往常一样,李宗仁一身戎装,举止稳健,脸上那庄严的笑容,平日里很少得见。郭德洁呢,兴许是想让人知道她曾是一位北伐巾帼英雄吧,不知何时也找人帮她做了一套薄呢料军装,脸上淡淡地扑了些胭脂,那双金叶耳坠也取掉了。和李宗仁一样,她脸上也带着几分严肃的笑容,只是走起路来依旧那样爱跷起脚后跟。
“黄主席,黄夫人、白夫人都还没来么吗”郭德洁扫视了一番松门前的座位,不待坐下,就问黄旭初。
“她们都不太习惯这种场合。”黄旭初并不知道郭德洁昨夜去邀过马佩璋。至于他的夫人,不到逼上梁山的地步,是绝不在公开场合露面的。他转而问道,“没见到你们的汽车,怎么就到来了?”“从北面城门进来,东西两门人太挤。”郭德洁心里有些悻悻,黄夫人不来,那似乎合情合理,因为她乡味太浓,木讷而不善应酬,确不适应这种场合;而白夫人,既是大家出身,也见过世面,今天是国庆节,无论如何也该来露露面。更何况昨夜还专门去邀请过,不看僧面看佛面嘛!
无论是万绿丛中一点红,还是万红丛中一点绿,总是格外惹眼的。松门前的两排座位上,坐着的不是金刚般的军人,便是长衫马褂的遗老,唯有郭德洁是一位女人,而且因为是李司令长官的夫人,就更加招人的眼光。
“请坐,请坐吧!”黄旭初要把右边两个座位让给李宗仁与郭德洁,而郭德洁自感坐在李宗仁和黄旭初中间,未免也太过高格,只好左推右让,坐到第一排的右侧边上。
她没有看台阶下的情景,想暂时回避一下那千百双兴许正注视着自己的眼睛。“马佩璋,怪脾气。”她心里嘟哝着,带着几分怨气。她希望她来,不过是要避着“出风头”的闲言罢!郭德洁这些年大概从丈夫身上学到几分老练,总想把事情做得名正言顺些,面面俱到些。
21 响铁炮在独秀峰下炸响。省主席黄旭初领着大家念过一遍总理遗嘱之后,说了几句简短的套话,便请李宗仁讲话。在李宗仁面前,黄旭初总是那么谨慎小心。他当过李宗仁的参谋长,搭档多年,深知这位德公的脾气。一直把目光停留在台阶石栏上的郭德洁,这才慢慢地抬高头,把目光投向台阶下那黑压压的人群。大概是心比刚才稳定了吧,郭德洁感觉到台下的人群并不像她所想象的那样以一种好奇的目光盯着她。注意她的人,甚至那些戴着捷克式钢盔的兵士投过来的,像是带着敬佩与羡慕的目光。
她心里舒坦多了。马佩璋不来,她也觉得无所谓了,家庭妇女型的人物,不来也情有可原。自己毕竟是参与过北伐的“功臣”,又是省党部的委员,她觉得自己本就该高一筹呢!不期而然,她又想起了李秀文。听说李秀文已经从广州回桂林了。到了,还是没到?如果已经抵桂,那才好呢——让人把李宗仁带着郭德洁出席双十国庆大会的事,传到她李秀文耳里去,也可以气气她,给她点火色看。什么“大夫人”,“小夫人”,有本事的,能干的,出头露面多的就是好夫人。
李宗仁在讲全国抗日的形势,讲他“焦土抗战”、“抗争到底”的主张,言辞激昂慷慨。被爱国的火种点燃的兵士、学生和百姓,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台阶下每鼓一次掌,郭德洁自然极力附和着,那抹过淡妆的脸,红得像5 月的榴花。她听过丈夫无数次讲话,在公开场合或在家里,但平时总是稳健有余,激昂不足。今天,她却也听得很满意。她不时用眼瞟瞟他,觉得他今天很雄壮、很练达、很受拥戴,大不像前些年倒霉时,那副抑郁、沉闷、痛苦的样子。
天,越来越灰蒙;风,也比先前大了些。郭德洁不时抬腕看看手表,秧塘机场,那架专机还在等着李宗仁呢!天,晴起来才好。郭德洁的一时激奋与喜悦,又被这灰蒙蒙的天压抑着。她本是想来吐吐气、扬扬眉,抖散这些年来一直积郁在心中的压抑感的。广西这块地盘,从把老军阀陆荣廷和沈鸿英打垮后,“桂”字第一号的人物该是李宗仁。可是李宗仁却从没像“南粤王”陈济棠那样也在广西称“八桂王”,这几年来,却让白崇禧主管了,她似乎觉得丈夫有些过分忍让谦恭。去年双十国庆的庆祝会,因为正在迁省治,加上李宗仁刚从广州回来不久,一切都还是由白崇禧出面的,唯有今年才算拨云见日,她郭德洁也才能如此名正言顺地出头露面,成为这长官台上的“万绿丛中一点红”。马佩璋不来正好!她真不该来。
郭德洁的思维又倒转过来,初来时的那份悻悻心理一扫殆尽。她挺直身子,抬头看了看天,虽然依旧灰蒙,但她觉得它高了些、亮了些。
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宣告李宗仁讲话结束。李宗仁神情严峻,掌声刚落,他便点燃了一支烟。
郭德洁想说话,想对李宗仁说,也想对台下的人说,但说些什么,她自己也没想清楚。
黄旭初照例要按官阶等级,尊卑长幼一一点请在台上那些要人说几句,多数的,都摇头摆手婉辞谢绝了,唯有她郭德洁却很想说一通,她觉得让别人听自己说话,也是一种愉快和荣耀。过去,她不曾有过这样的机会,而今天,夫人们都没有来参加会议,她自有一种鹤立鸡群之感。可是,不知是李宗仁对黄旭初打过招呼,还是黄旭初的粗疏,他始终没有点到她的大名,会议便转入团体游行程序了。郭德洁无可奈何地跟着李宗仁上了停在台阶后侧的那辆有篷盖的吉普车,随着一阵阵锣鼓声,被游行队伍缓缓地送过了桂林南门的善济桥。
吉普车沿着中山路南行,过善济桥后右拐朝西,出五里圩后,便颠颠簸簸地在桂林市西郊的黄泥沙石公路上奔驰。
天,比刚才更加阴沉。风,卷着尘沙,滚到吉普车的前面,秋日的东北风,是雨的报信。李宗仁没有说话,只默默地看着车窗外闪过的黄澄澄的畦畦稻田。田间,间或有几处摆着方形的谷桶,农人们举着稻子,“砰砰”地在桶壁上摔打着。南方稻谷收获的季节,比北方五月收麦更忙。
“德邻,这次出去,你估计要多久才能回来?”郭德洁这几年多跟随着丈夫,过惯了夫荣妻贵的生活。这次李宗仁要到前线去,她不免依依惜别。
“这次去打日本鬼,我心甘情愿。”李宗仁把视线收回来,看了看神情有些怅然的妻子,“不过,日本鬼子可不是那么容易打败的,‘九一八’到现在六年多了。”“我还是想做些事,不愿意太闲。”郭德洁凑近李宗仁说:“搓麻将打扑克牌过日子,我不甘心。”“做吧,做点于民于己都有利的事更好。你也可像前些时北伐那样,动员妇女来支持、宣传抗日嘛!眼下,一致抗日已是全国百姓的众望,内战恐怕可以暂停了。”“我想筹办一所中学、一所难童教养院,还买些地种植桐子,那东西三几年便可收成,是本少利强的活路。”“你做得到?”“北伐时跟着你北上打仗,护理伤员,那么艰苦的事都做了,在后方做这点事算什么。”“那就好,就好!”李宗仁点点头。他当然知道郭德洁总喜欢做些有名声的事,总想进取些什么,因而,他不伤她的自尊心。他沉思了片刻,又问:
“我们的家当就那么点,办学的经费从何而来?”“我自有办法,你等着看吧!”郭德洁话语激昂起来。她很自信地说:
“你说,我办所中学,取什么校名好?”“眼下,国难当头,无论办中学,办难童教养院,首先是要教育学生爱国,不做亡国奴。你看就叫‘爱国中学’好不好?”车还在颠簸,李宗仁显得有些疲惫。
“‘爱国中学’,好是好,只是太通俗,一般。你不是常说要‘教人以德,诲人以智’吗,我看就叫‘德智中学’,如何?”郭德洁皱着眉头,但情绪还亢奋,车的摇晃,使她脸色有些青黄。
“‘德智中学’,嗯,好,好!”李宗仁有些兴奋地拍了拍郭德洁的肩膀笑着说,“你真乖!你叫德洁,你妹妹佩瑜现改成了智洁,干脆把她也叫来,姊妹俩一起办吧!德智德智,哈!”郭德洁见李宗仁一语道破机关,也会心地笑了。刚才在省公署前未能讲话的不快,像被突来的一阵风,吹跑了。
飞机的引擎已经发动,卫士和随行人员都已经上了飞机,郭德洁还守在李宗仁身边,像是有桂林的山那么多说不完的话。
“德洁,你自保重!”李宗仁看了看怀表,10 点10 分——真太巧——今天是10 月10 日,四个十凑在一起了。他事先并没有这样安排,自然的吉祥圆满,这次出征一定会成功。他心里一兴奋,便毫不犹豫,转身大步登上了舷梯。
“一路平安!德邻——”郭德洁眼里含着惜别的泪花。
云层似压得更低了,飞机照样跃上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