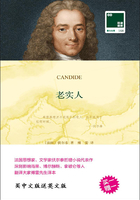在中国儿童文学中,评论柯岩就是在评论一段历史。
柯岩的创作主要分两个时期:“文革”前十年和“文革”后十年,中间十年是一段突兀的空白。前十年其实不足十年,从作者最初发表作品的1955年算起,未到十年动乱全面展开,作者的创作已接近停止了。后一个十年略有延伸。《他乡明月》出版在九十年代初。以后仍有新作,只是较少很集中地进行创作了。前十年主要写作儿童诗,后十年也写作儿童文学作品,如题画诗和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但更多的还是报告文学和成人小说。作者两个时期都创作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但就儿童文学而言,其影响和成就主要在前一时期的儿童诗。我们说评论柯岩是在评论一段历史,指的也主要是解放初到“文化大革命”的这一段时间。
一
在“文革”后有段时间的一些评论里,柯岩曾被视为“主旋律”的或接近“主旋律”的作家。这虽然是就作者“文革”后的创作及作者当时在文学领域一些活动而言的,但评论柯岩的作品,包括评论她五十年代的儿童诗,仍是一个不得不首先面对的问题。
“主旋律”是“文革”后作为一个很正面的要求提出来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求文学要努力塑造正面的人物形象,创造色调明亮、能鼓舞人积极向上的文学作品,以表现人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热情,引导人民,特别是引导年轻人更好地进行两个文明建设。提出这一要求的背景是十年动乱之后,改革开放,长期闭锁的国门被打开,许多先进的思想观念、思维方法、科学技术被介绍进来,同时也传进一些格调不甚健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文学领域也显出某些多元化的趋势。其中包括一些在内容和色调上都与传统的革命文学不一致、不相融的东西。人们不能完全阻止这些东西在中国的传播但要求正面的革命文学占主导地位。但这毕竟是一个从主流意识形态立场给出的大视角。中国文学受“写中心”“画中心”之类的伤害太深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一下子将提倡正面描写的“主旋律”和“写中心”之类的东西区分开来,因而对一些“主旋律”的和接近“主旋律”的作家带来一些误解。柯岩一直是一个有个性的作家。面对纷繁复杂的生活,她一直坚持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有自己的价值尺度和判断力。据她自己说,1958年大跃进,许多人一窝蜂地人造共产主义,她因不肯跟着赶潮流而被视为“右”。特别是五十年代后期以后,当整个社会越出常态地向政治化的方向偏转,文学,包括儿童文学也越来越成为形象的政治讲义的时候,作者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并悄悄地与之拉开了距离。我在年20前的一篇文章中曾说:“评论一个作家,不仅要看作家写了什么,一定程度上还要看作家没有写什么。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柯岩一点没有写这类东西,而是明显地放慢了创作进度,表现出作家的明智。”此话后来得到柯岩同志的肯定,但我觉得我只是说出了一个事实。五十年代后期以后,“文化大革命”尚未正式展开,但许多前兆已非常明显。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抓特务,斗地主,越来越多地成为儿童文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柯岩总体上仍坚持写与儿童文学相宜的东西。真写不下去的时候,就选择沉默。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的选择,是一个对艺术负责的作家的选择,也是柯岩儿童诗不像一些应景赶时髦的作品随着运动、时髦的退潮而迅速褪色的主要原因。比较有点出人意料的是“文革”以后,当许多人由于时代和环境的改变而疏离社会性、意识形态的大视角的时候,柯岩却突然强化了她的意识形态立场,在她的作品中表现出她在五六十年代都极少表现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内容。如《寻找回来的世界》,本只是一批工读生受教育的故事,且主要材料在十年动乱前已搜集完毕,一些故事和人物的雏形已构思出轮廓,可在“文革”后的实际创作中,故事、题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原有的材料被放到十年动乱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背景上,工读生的故事变成了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在工读战线上的一种反映。如《中国式的回答》,一首以残疾女青年张海迪为表现对象的长诗,本是一个很人生化、很个性化的内容,却也渗入过强的政治色彩,将人物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了。解释这种现象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作者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情,特别是与作者政治思想紧密相连的许多事是局外人无从知晓的。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另外一些人身上。但有一点我觉得人们可能误会了柯岩:仔细阅读《寻找回来的世界》等作品,会发现它和作者五六十年代的作品的差别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寻找回来的世界》虽然写了较多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但它突出表现的并非所谓的路线觉悟而是人的献身精神,是徐问、黄树林、于倩倩等人对工读事业的忠诚和热忱;《船长》中的贝海廷是作者心目中的硬汉形象,驾驶着中国自己的轮船跑遍世界几十个国家,不仅和自然界的风浪搏击,还要和社会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阻力抗争,无论环境多么恶劣,都无法改变他献身祖国的一腔热血和铮铮硬骨;《奇异的书简》写科学家陆琰、罗辽复对科学、对友谊的忠诚;《红蜻蜓》写杜嵋等中学教师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奉献。还有吴丙治、李英娥、韩美林等等,作者称他们是“追赶太阳的人”“美的追求者”“仅次于上帝的人”,都是将他们作为这个民族的脊梁、这个国家的中流砥柱予以表现的。这样,有些坚硬的路线斗争的内容也被心灵化、情感化、柔和化了,一定意义上仍是作者五十年代儿童诗积极热情、充满情趣的阳光主题的延伸,和那些一味“写中心”“画中心”,借儿童说事的作品是不同的。
这儿肯定还有一个社会、文化语境的问题,即柯岩“文革”以后,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一些颇带情绪、颇带政治论争色彩的诗歌、小说、报告文学及理论文章主要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主要是相对什么而说的。《寻找回来的世界》设定的故事背景时间比较早,其材料、思想主要来自十年动乱和十年动乱结束后一段时间的生活积累,思想情感及观照世界的方式带有明显的路线斗争的印迹;最具火气的长诗《中国式的回答》和理论文章《关于诗的对话》都写于1983年,应是对十年动乱的批判清算告一段落、改革开放已提到议事日程之后。我觉得,柯岩这段时间的愤怒主要是针对“文革”后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如信仰危机、政治热情消退、社会责任心淡化、个性化个人主义抬头等而说的;换言之,就是对作者理解中的带资产阶级思想色彩的自由化倾向而说的。这是一场贯穿八十年代的思想论争,是十年动乱之后,中国究竟向何处去的方向性探讨。事关紧要,说话时有些冲动,带点火气是可以理解的。坦率地说,我并不是很同意柯岩在这段时间一些作品和理论文章中表现出来的观点,我觉得她将改革开放,特别是西方文化引进后带来的负面效果看得偏重,而对包含其中的正面因素看得少了一些。中国毕竟闭关锁国太久了。十年动乱,不仅割断了和优秀的中国古代文化的联系,也割断了和优秀的世界文化的联系。一旦国门打开,人们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惊讶、兴奋、感叹、模仿,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等的冲击是巨大的;我以为,所起的作用主要也是积极的。但是,我还是想尽我最大的努力去理解柯岩,包括理解她那段时间在一系列作品、讲话中表现出来的颇有些愤怒的情绪。改革开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从长期的封闭中走出来,出现变化时的阵痛,带来现实生活及人们思维中的某些裂变、混乱、不适应是正常的。特别是引进一些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有着巨大差异的西方文化时更是如此。西方文化自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有古典的,有现代后现代的;有科学技术的,有人文社会的;有精英的,有大众的;有统治阶级,有人民群众的;有积极进步的,也有腐朽落后的。“文革”后中国国门一开,人家在几个世纪中积累起来的思想、文化一起涌进来,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特别是经过中国某些人的转手、改造,走了样,夹进些私货也未始不可信。我理解,柯岩批评的主要是这类文化、生活方式中她认为的最消极、最带腐朽性的部分,如反权威、反崇高、反英雄、反理想化、反集体主义,鼓吹审美享乐主义、虚无主义、及时行乐,声称只为自我活着,“他人是自己的地狱”,包括文艺领域中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过分否定,一些年轻作家带自由主义倾向的创作及一些理论家对他们过分的抬高等。应该说,这种现象在当时是存在的,其对思想意识、社会生活,尤其是年青一代的成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不管柯岩的批评是否完全准确,在一种潮流袭来,许多人裹挟其中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其消极方面的时候,有人勇敢地站出来指出其中的错误及其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总是值得肯定的。在批评的同时,柯岩还身体力行地创造出许多正面的、体现主旋律的人物形象,更是积极和让人钦佩的。
这里肯定还有作家个人艺术理念、美学理想方面的原因。柯岩是一个从五十年代走过来的作家,具有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作家普遍具有的一些特点。从现在的眼光看,五十年代也并非一切美好。但比较而言,毕竟是二十世纪中国较为和平、安定的一段时间。绵延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结束了,全国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整个社会充满一种温馨、和谐、积极向上的时代情绪。这种情绪感染了作家,也包括受到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的影响,人们几乎是情不自禁地用一种积极明亮的调子共同创造一个美丽诱人的光明梦。如果说“主旋律”,那个时代的作家都是主旋律作家。柯岩当时只有二十多岁,没有太多从旧社会带来的重负,她的情感、她的心灵节奏与那个时代几乎是天然地合拍。而且,一开始就选择儿童诗这种艺术形式,使她刚走上文坛就找到一块最适合自己个性、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园地。儿童的情感、兴趣天然地朝向未来。他们喜欢积极向上的思想情感,喜欢欢快明朗的调子,喜欢热烈绚烂的色彩,喜欢幽默喜剧的情趣。这样,时代精神、读者需求、作家创作个性正好汇在一处,形成作者五十年代儿童诗欢快明朗又充满喜剧情趣的情感基调,她的最能代表她创作个性的作品如《大红花》《做客来》《小建筑家》《妈妈下班回了家》《眼镜惹出了什么事情》《看球记》《通条,通条不见啦》《小兵的故事》《“小迷糊”阿姨》等都是那个时期写下的。十年动乱以后,作者经历的事多了,思虑深了,许多内容无法再用儿童诗这种艺术形式来表现,所以她主要转向报告文学,成人小说,作品的色调也发生了不小的改变。但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论及的,积极、热情、欢快明朗、热衷描写正面的英雄人物,即一种在整体上显得十分阳光的艺术追求,仍然是她创作的底色、基调。若说“主旋律”,这便是柯岩的主旋律,一种贴近时代又发自她生命、个性的主旋律。
二
在处理如何既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大视角又保留作家创作个性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有一个因素在柯岩的作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作者的女性视角。柯岩作品中的艺术世界主要都是从女性视角中呈现出来的。作者五十年代的一些儿童诗多带有叙事性。作者一般都未告诉读者是谁在叙事,叙事者一般也不在作品中出现,即只有声音而无实体。但根据这个声音透露出的某些标志性的信息,特别是其与故事中人物的关系,我们还是可以对这个叙述者的身份进行某种判断。比如,在《小红马的遭遇》《看球记》《眼睛惹出了什么事情》《通条,通条不见啦》等作品中,处在描写中心的人物都是“小弟”。“小弟”不是人物的名字,而是叙述者对人物的称谓。能够称人物为“小弟”的人只有两种可能:哥哥或姐姐。再从作品的叙事语调(带着一种亲切和自豪)、故事细节(故事场景主要在家庭内外)及人物的某些性别标志(“哥哥嫌我衣服穿得太花”)来看,这个叙述者更多的时候是“姐姐”。以“姐姐”的目光看“小弟”,“姐姐”的目光是一个平台,“小弟”就是在这个平台上演出他的故事,故事自然带上“姐姐”的情感特点。
“文革”后作者最重要的少儿文学作品是《寻找回来的世界》。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叙述者也是只有声音而无实体,和人物不处在同一世界,不参加故事也从无机会自称。但和许多高视点权威叙述不同,这部小说中的于倩倩既是作品的主要描写对象又是作品的视点人物。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她是被看者,被述者,她的经历是故事的主要构成部分;作为视点人物,叙述者又叙述她听到看到的事情,通过她去看别人。这时候,叙述者又常常隐藏在视点人物身后,视点人物走到哪里就陪同到哪里,作品的情感倾向也常常在这二者不断变化着的距离中表现出来。《寻找回来的世界》故事开始时,出现在故事中的于倩倩是一个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工读学校的女教师,满腔热情却毫无经验,她的目光是陌生的,她对工读事业,对黄树林、徐问等人的了解也还是较为表面的。但是,随着她越来越深地走入故事,特别是越来越深地卷入学校内外的矛盾冲突,她不仅感受到工读战线的复杂性,更看到工读事业作为一个改造、净化人的心灵、引导人走向美好人生的诗意,看到黄树林、徐问等人崇高的内心世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她自己的内心世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她克服一度出现的迷惘,找回一度失去的世界,自己也成为崇高的工读事业的一部分。通过于倩倩的变化,《寻找回来的世界》将叙述者的视角和女主人公的视角和谐地统一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