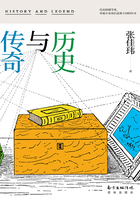不过一炷香功夫,郑管家便从游廊拐角处走了出来。众商人之前见翼王殿下面色不豫,又将郑管家唤走,心中俱是惴惴,担心情况生变,也不知今日手中货物是否还能顺利出手,一时庭院中人人屏息凝神、鸦雀无声。
不想郑管家一派神清气爽,也不曾理会眼巴巴等着他的商人们,一开口就吩咐王府账房老丁:“再去库房搬十口空箱子来!”众人闻言心下一松,俱都重新笑逐颜开,纷纷挤上前去将郑管家众星捧月地围在中央,巧舌如簧地推销起自己的货物来,中庭重又喧闹如一锅热粥。
人声鼎沸之中,丝毫不曾有人发现,先前指挥十几个侍卫清点封箱的侍卫长林笙已然悄悄离开了中庭。不多时,人迹罕至的王府后门吱呀开了,一队共计一十二名、身着石青色劲装,披着同色大氅头戴风帽的年轻男子牵着马鱼贯而出,一字排开静立门外,最后待一架木轮青盖的二驾马车从王府后门粼粼驶出,十二名男子便迅速散开三人一组护卫马车前后左右,为首之人低喝一声“启程”,众人便翻身上马,纵马向偏僻的西城门而去。马车厚厚的帷帘紧闭,看不清车上动静。马上的十二名骑手面容俱隐在风帽的阴影之中,暗沉的天光下,只能窥见他们紧抿的薄唇和线条坚毅的下颌。
马车上其实并没有人,只满载了一些干粮腊肉、火石油毡并露营的帐篷等物。翼王殿下景祯换上了侍卫的劲装骑在马上,他的马稳稳地跑在马车右翼第二位,为了不扎眼,他事先换了普通的良驹,流光留在了翼王府里。右手边与他并驾齐驱的是寸步不离的贴身侍卫林笙。一行人未时三刻便悄无声息地出了临阳城。
这一路北上,几乎千里冰封,越往前去越是寒冷。仿佛存心自虐一般,景祯冒着风雪风尘仆仆地赶往翼州,毫不犹豫,一往无前,带着他自己不愿承认的一丝赌气。
就在景祯踏上漫漫长路之时,误打误撞坠入异时空的晏晴,已经在这个陌生的朝代生活了近一个月了。
这一个月来,她的救命恩人、年轻的猎人青虎果然说到做到,带着她费尽千辛万苦,踩着厚厚的积雪,攀爬湿滑的山道,将西山方圆百里能走的地方都走了个遍,也访遍了散居在各处深山里的猎户,可却没有一个人见到过她所描述的朱天余模样的少年。
这一个月来的每一个清晨,晏晴都充满希望地出发,每一个晚上,都拖着疲惫的身躯失望地返回,看在青虎青豹的眼里,端的是十分不忍。其实他们私下里都觉得,晏晴的“弟弟”多半是遭遇了不测了。
须知西山上的悬崖峭壁下,多的是深不可测的山谷,若是遭了贼人毒手被扔下或者失足掉下,被厚厚的大雪那么一埋,就算神仙下凡也难寻。如今正是严冬,积雪起码要到来年三月中旬才能融化殆尽,山谷里的景象才会重新显露人间,不过,到那时就算找到,肯定也就是一具尸体了,又或者压根等不到来年,早已被过冬觅食的野兽啃了个干净。
这些话青虎自然是不会说出口的。每日一大早,他只是默默地背着弓箭与干粮,陪着晏晴一同出门,一边陪着她寻人,一边辛勤狩猎。这几日家中地窖里已经储藏了不少野味,有三只狍子、五只山鸡、两对野兔,甚至还有一只幼鹿,足够他们三人饱饱地过完这一季寒冬了。
其实青虎虽然一直都是个很勤奋的猎人,对储藏食物这件事却从来未曾如此上心过。以往家里的地窖里存上半个月左右的野味和粮食也就尽够了,西山本就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宝藏,缺少什么出门去猎也就是了,但最近他的心态却有了些许不同,总想着多猎一些,将地窖填得满满的,好好儿过个肥年。他心里回避这个变化,有些羞于究其原因。
在青虎眼中,从天而降的晏晴坚强冷静得不同寻常。在风雪中进山,即便是壮年男子也颇觉吃力,何况需要整日在山路上行走探访,可她竟然咬牙坚持了一个月之久,以致眼见得瘦了一大圈,满面风霜之色,脸上手上都冻出了冻疮,料想穿在粗布棉鞋里的双脚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青虎从未见过大户人家的小姐,但本能地,他觉得那些养在深闺的千金小姐必然是娇滴滴的,一定不会是晏晴这般。
所以晏晴让他迷惑。他想,也许是因为她的家族遭受巨变,心性才变得如此罢。想想一个弱女子,竟有胆子带着幼弟跋涉千里到翼州来,一路上得吃多少苦头?行为举止又怎么会如那些承欢在父母膝下的娇小姐一般?如此想来,心里便也释然了。
而想到这里,青虎心里总是会浮现出一种十分陌生的、一般我们称之为怜惜的情绪,恨不得替她生受了那些苦才好。
这一个月来,虽然奔波劳累,他却是甘之如饴。两人结伴而行时,她说话不多,大多数时候他们总是沉默地一前一后走着。但当她开口时,总是语气真挚,眼神清亮,虽然谨遵礼数,却让人感觉不到丝毫隔阂,直让他如沐春风。
而每当他射中了猎物,她含着笑意站在一旁看着的时候,他甚至会有一种微醺的感觉,这比每次在翼州城里卖完猎物,到酒家要一碗浓烈的烧酒,更令他感觉浑身发烫,他似乎都能听到自己血脉之中血液加速流动的声音。
其实他隐隐感觉到,她身上似乎有一些秘密,但她不想说,他也不想问。作为一名自五岁起就拉弓射箭的猎人,他相信自己天生敏锐的直觉。她的双眸清澈如林间山泉一般,绝不会是心怀不轨之人。
青虎虽然常常思绪翩飞,面上却丝毫不显,凡事格外注意避嫌,晚上回到家,用完饭稍事休整便去院子里料理猎物、劈柴烧炭。须知家里突然多了个人,一应柴米油盐用度均增加不少,仅仅晏晴屋里取暖用的火盆子整夜不熄,每日便要多烧许多炭。
青豹要比他直接得多。因为他们的娘生他的时候难产去了,他自小就没有体验过一丝一毫母爱,此时看到一下子闯入他凄凉童年的晏晴,穿着娘留下的粗布旧棉袄住在他的家里,又生得那般好看,让自家的土坯屋都亮堂温暖了许多,小青豹的孺慕之情如便如滔滔江水一般,简直不可收拾。
每日里青豹都恨不得变做一条小尾巴跟着哥哥和晏晴出门。只可惜山路难行,无论他如何撒赖耍泼,青虎都坚决不允,只好搬个板凳坐在门口,从早到晚眼巴巴盼着晏晴和哥哥回来。
一看到门口那条通往山下的小路上出现哥哥和晏晴的身影,青豹就呼地一声站起来,欢叫着迎上去,围着他们团团打转,直如一条欢迎主人回家的小狗儿一般,就差没有摇尾巴了。
看见自家弟弟这副黏乎的模样,青虎这做哥哥的心里又好笑又有些酸。虽然自己小时候也没有玩伴,但好歹那会子爹娘都还在,一家三口每日里其乐融融,却也不觉得多么孤单。而青豹一出生就没了娘,爹一身病痛、郁郁寡欢地苦熬了三年也去了,自己从此便整日里忙于狩猎养活家里的两张嘴,小小的弟弟只好如那山沟沟里照不到阳光的荆棘草一般,自己顽强地长大了。
对于青豹,青虎心里一直是十分内疚的。爹去世前千叮咛万嘱咐青虎,别想着下山谋生那些有的没的,只需恪守猎人本份,带着弟弟老老实实在西山里头住着,待到合适的年纪,便在本地娶个老实忠厚的媳妇,两人齐心合力,无论如何要将弟弟好生拉扯大。想起爹去世前放心不下,涣散的眼神死死盯着懵懵懂懂的小青豹,枯瘦的手几乎将皮褥子撕破,青虎就是一阵阵揪心地难受。
这些年青虎恪守爹的遗愿,除了下山卖些猎物换些过日子的必需品,几乎不出山一步,又当爹又当娘,尽心尽力抚养小青豹。可这山里到底太过冷清了些,因为极少见人烟,是以青豹的性子养得十分内向,加之他的样貌又随了娘亲,清秀得很,看起来倒像是个女孩儿。
难得的是,这孩子对着晏晴倒是不怎么认生,恨不能时时刻刻黏着,这些日子青虎在一旁瞧着,发觉他的性子也明显开朗了许多。
其实之前青虎也曾养了一条狼犬看家护院,兼给青豹做玩伴,三个月前不慎被蛇咬了一口,毒发死了。这三个月来,青豹过得别提多寂寞了。青虎暗暗寻思着,看来明年开了春,还得再下山弄条好狗崽子去。不知那时候,晏晴是不是已经离开了呢?每到此时,青虎总是有些怅然,不愿再想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