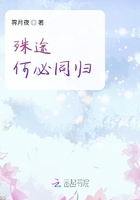明顺是个老实人,听人家说得诚心,也便打消了去冰面的念头。再说,他准备去受那天寒地冻无热饭的苦,多半是想冒险为琴儿挣几个陪嫁的钱,说来说去,还是为了成全他世良。
两个打鱼人匆匆告别了明顺,在老汉久久的瞩目中,悄然隐进了浓浓的夜色。
为了避人眼目,他们绕来拐去,一直走到第二天黄昏。
沙丘如月,护卫着坑坑窝窝的盆地。趁着黄昏时分明晰的亮色,人们紧紧张张做着安营扎寨的一切。有帐篷的扎帐篷,没帐篷的挖沙坑、罩布单,然后便是垒锅拣柴。惟独马存德不同,在盆地东西南北转了一遭,然后悄悄招呼世良快跟他走。
他们两个人来到湖边时,西天的霞色已经燃烧到将尽而未尽的时刻了。淡淡的绯色的光柱打到玉色的冰上,形成了一种梦幻般迷人的彩色的行道。他们就是沿着这条彩色行道踏上冰岸的。程世良以为,马存德是来带他先捞几条今晚上解馋的鳇鱼的。谁想,马存德连打冰窟窿的意思都没有,倒背网具,将那根敲冰的钗犁横搭在肩上,来回走动着。
“见了吧!这是一条鱼群早晚都要经过的路。”马存德指着冰面说,“我们两张网,明儿一上来,东打一个窟窿,西打一个窟窿,中间相隔至少得有一百步。三天过后,我保你……”突然,他不说话了,翘起下巴,痴望冰岸那边一个隆起的黑色大包。
程世良禁不住问:“鱼也有路?这么大的湖,它哪儿不钻?"
马存德没有吭声。而程世良也已经发现了他脸上异样的表情,双眼滴溜溜转向前方黑包,又转向马存德的脸。
“鱼?”程世良喊道。但他并不明白,马存德的惊喜并非仅仅因为那是鱼,而是从天色已晚,四周无人而鱼堆赫然这情况中知道,那是一堆无主的鱼,或者说暂时无主,或者说,谁最先看见了谁就是主。主儿呢?走啦!被人撵走或被人抓走啦。肯定的。这年头,辛辛苦苦捞出来的鱼转眼就会变成自己的赃物。用马存德的话说,就是用几天挨冻受饿的辛苦换几年坐班房的保吃保穿的日子。
因为冰滑,马存德只好用小碎步朝前跑去。程世良也快步跟了过去,只是他远不像马存德那样因为意识到了某种意外的收获而格外兴奋。等他来到鱼堆跟前时,只见马存德僵立在那里,两眼发直地瞪着前面,舌头不时地吐出来舔舔干裂的嘴唇,鼻翼轻轻颤动着。看得出,他有点不知所措。片刻,他眯起眼,冷笑一声,很有气派地朝身后这个呆愣着的同伴挥挥手,兀自上前,手伸进鱼堆缝隙,“嗐”的一声,整个身子朝后仰去。然而,他没有扳下一片鱼翅来,手一滑,屁股重重地坐到鱼堆下的冰面上。
程世良赶紧上前扶起他,小声问道:“这鱼是谁的?”
“我的!我们的!”
程世良不禁打了个寒颤,眼珠飞快地左右滚动了一下。
马存德瞪了程世良一眼,吼道:“你是来看稀罕的么?就等着老子把钱放在你兜里呀!”
程世良搓搓手,跑上前,也像马存德刚才那样扳起来。大概他扳住的正好是没冻结实的地方,“咔嚓”一声,两条粘在一起的冰鱼滚落到马存德脚下,发出一串金属撞击似的声音来。马存德低头看看,又用脚踢踢,高兴地冲程世良眨眨眼:
“好!你就这样干着,我去铁路道班找个买主去。”说着,他从自己腰际撕出一条布袋,躬腰将几条程世良扳下来的冰鱼抬了进去,手拎着走了。没走几步,他又回来,脱下自己的棉衣,扔给程世良,“我再说一遍,冻死也不能离开。”
程世良点了点头。
他足足干了一个钟头,等夜色吞没了整个湖面,头顶闪现点点星辉时,马存德才领着一个拉架子车的老汉来到冰面上。这人叫金库,是道班的合同工,算是半个鱼贩子,一些没有门路出售冰鱼的渔郎常把货物卖给他。他白天干活,晚上将鱼提价零售给路过客车上的人。
“你估估。”马存德将自己刚刚装好的一布袋冰鱼搭在车辕上,对那个满脸胡茬的金库道。
“顶多四百斤吧!”
“四百斤?哈哈!你把这话对世良说,他还相信,对我,哼!不过五百斤,我就姓骡子。”
鱼贩子发出一阵狞笑来:“说大话不怕人笑,唾沫星子也当点灯油啦,山羊头上长鹿角,人比天大,天比人小,你咋不说一万斤?我这个车箱有卡码,多装一斤就往外溢。”
“那就算四百八十斤吧!”马存德妥协了。
“不!四百斤,加上你这一布袋,算你四百三十斤就已经让你占尽了便宜。”
“好!好!我们吃亏吃定了,凑个整数,就算四百五十斤。”
金库执拗地摇摇头:“四百三十斤,多一斤我不要。”
“不要算了!买主满天下,满天下都有我老马挣钱的地方。”
“算了就算了。鱼我不要了,明儿一早你把车子给我送来。”金库说着,扭身就要走。
马存德看着,突然“噗哧”一声笑了,接着又长叹一声,上前拍拍金库的肩膀:“快人办快事,拿来。”
“四百三十斤?”
“行!依你。” -
鱼贩子“嘿嘿”笑了,撩起衣襟,从裤腰带上拽出一个牛皮烟袋,拉开袋口,从里面撮出一叠脏腻的钱来,数数,递给马存德:“你点点。”
马存德将钱举到眼前瞅瞅。他不能点,有风,还有身后的同伴和他那双此刻盯死在钱上的眼光。他想着,毫不迟疑地将钱塞进了衣兜。
一直呆然不动的程世良突然尖声叫道:“点点,你怎么不点一点呢?”他上前捅捅马存德的胳膊,又向鱼贩子投去不信任的一瞥。是的,他此刻并没有觉察马存德的微妙心理,只是从刚才鱼贩子的言行中感到:这个人不老实。他觉得冰鱼的斤量放在那里,是多少就是多少,怎么能依鱼贩子说了算呢?他没拉过一架子车冰鱼,但他从村边河滩里拉过石子,多重的东西使多大的劲,这个他明白。
“怎么,你不相信我?”这时的马存德更加确信,身后的这个同伴实实在在是个包袱。“我少给你一个子儿,我就……我就是四条腿养的。”他误解了程世良的意思。
程世良愣了。他猛然意识到不管马存德以后分给自己多少钱,但刚才老马脑子里是有过多贪多占的念头的。这个老实巴交的穷惯了而从未产生过非分之想的小伙子,突然感到,那种他在胆战心惊中怀揣了一夜的欣喜和激动,那个他尽最大努力渐渐靠近了的从天而降的希望,已经变得渺茫了,迷蒙了。他也火了,嗓门骤然变得粗壮起来:
“你少给我一分,我就告你!”他停顿了一下,声音马上又变得哀婉起来,似乎马存德已经少给了他许多,“我哪样比你差?你让我大风里头守冰面,我守了;冻得直跳,直抖,直恨亲娘生养时没给我披一张狼皮,我也忍了。想你是个公平人,不讲村社邻友的情面,也得顾顾天地良心,可你……”他说不下去,气得两片厚重的嘴唇直哆嗦。
“嗐!”马存德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我算瞎了眼,领了你这条疯狗来……”要不是听了金库的话,他还想狠狠地骂几句。
“你手里怎么还有两条鱼?”金库冲程世良道。
程世良一愣,眨眨眼,又看看自己的手:“放不下,布袋子里都装满了。”
“那你放车上去。”金库的下巴朝架子车翘翘。
程世良朝架子车走去,突然又侧过身子来:“你还没给钱呢!”
“钱?”
“你不是说一车箱加一布袋一共四百三十斤么?你没把这两条算在内。”
“哦?”鱼贩子金库愣了一下,突然朗声笑起来,笑罢,对马存德大声道: “这个年轻人,鬼机灵,好!有出息。”他又拍拍程世良的肩膀,“这年头就得这样。”说着,手伸进腰里,从那牛皮烟袋中抽出一张两元的票子来,“拿着,这是我奖给你的,鱼你带回去,让家里人尝个腥。”
程世良接过钱来,牢牢捏在手心里。但他还是走到车边,将那鱼摞在了上面,然后低着头,来到了马存德面前。
“存德大哥……”他已经不再生气了。
马存德“哼”了一声,掏出钱来,数了七十元,递给程世良,又道: “三个人平分,你点好。”
“三个人?”
“你把琴儿忘了?”
“琴儿……”程世良自语着,不禁感到酸酸的一阵难受--给琴儿钱的,应该是他程世良啊!他愣怔着,半晌,道,“把钱给我。”
“啥钱?你写状子的纸墨钱?”
“纸墨钱?纸墨才值几个钱?拿来,琴儿的钱。”
“你自己挣去。我可没欠你的。”马存德冷冷地说着,又提醒他道:“你快点点你那份吧!”
程世良这才将钱凑到眼皮底下数起来。他激动了,双手搓揉着那票子,不时地抬眼感激地望望马存德。
夜色沉沉的湖中冰上,重归一片死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