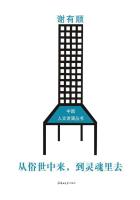他与她是中学时的同学,当初爱上彼此的时候,并不了解对方的家境,只是在去上学的公交上,碰到了,一个眼神,那心底的柔情,便排山倒海地来了。那是多么单纯无忧的少年时光,两个人能守在一起,感觉便已是整个世界;至于外人的阻挠和议论,在他们自己看来,不过是如那外面的风雨,关上窗户,便只剩了掌心的温度。
后来他们考入不同城市的大学,但爱情并没有因此而降了温度,倒是愈加地醇厚芬芳了。四年大学毕业,他们收获的,除了优异的学业,还有上百封情书,上百张电话卡,和上海与北京之间的火车票。它们见证了他与她的爱情,那样地温暖又饱满,如一粒被充沛的雨水滋润着的种子,终于开出了绚丽动人的花朵。他们在恋爱的时候,无数次谈论的一个问题,便是未来的婚礼,他许诺一定给她一个独一无二的浪漫纯美的仪式,让她成为所有人羡慕的新娘;而她,也一直期盼着,能够以最唯美的方式,为这份成熟的爱情,画一个完美的句号,亦开启另一份更为天长地久的幸福的门窗。
他们为此有过许多的设想,她希望他们能去西双版纳或是神秘的西藏,让一路美丽的山水为他们的爱情祈福;她也希望他们能去一个杳无人烟的小岛上生活一周,过尘世间最静谧纯净的蜜月;她还希望他们能租一辆环城的公交,让全城的每一个人,都能分享那一刻她的喜悦,他的温柔。而他,也曾设想过许多新奇别致的仪式,譬如找十几个要好的哥们,骑了扎花的自行车,在夜色里,浩浩荡荡地开到她的家门口,而后站在楼下,齐声高喊她的名字,载她回家后,相拥着睡一晚,醒来便成了世间那最相爱的一对。或者像读书时那样,他背着她,从她的家里,气喘吁吁地一直到他的家里。
如许多的美好设想,无一例外地,都没有那花团锦簇、喧哗吵嚷的世俗喜宴。爱情,是两个人的事,那么,婚姻的开启,他与她,也希望,能够以同样温柔缱绻的方式,欣然来到。而那满座的高朋,象征家财与显赫地位的筵席规格,代表俗世中幸福指数的钻戒与金银首饰,显然是与他们这一场优雅绽放的爱情,不相匹配的。
但这样曾经无数次温暖过他们的设想,却是还没有开口,便被他们的父母,瞬间熄灭在指间。她的父亲说,婚礼必须要足够豪华和气派,不能丢了小城最高医院院长的面子。她的母亲则补充说,低于3万的钻戒,坚决不能要,这么好的宝贝女儿,怎能如此轻易地就被那臭小子娶进家门?况且,女人在婚前不积攒点私人财产,以后男人会更难得为你购买什么有身价的东西。他的父亲则说,唯一一个儿子的婚礼,当然要办得隆重又上档次,不能让女孩子家小瞧了我们,也可以借此与相关的领导沟通一下感情。他的母亲也说,送出去的那么多喜钱,也是到了该回收的时候了,不办一场喜宴,即使别人会笑话,自己也损失不小呢。
他与她都理解小城攀比奢华的喜宴方式,但没有想到,本是只与两个人有关的婚礼,却是两个人都没有决定的权力。她只不过是想要一场私密的仪式,他也不过是想给她一个刻骨铭心的浪漫记忆,但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却是连实现的丝毫可能,都没有。
他们最终还是屈服于父母的压力,接受世俗喜宴的方式。为了给她好面子的父母一个完美的答复,他跑去北京,买了4万元的钻戒,将那个她戴了7年的十几元的玉石戒指,换下。他们又千里迢迢地飞到上海,拍摄了价值1万元的婚纱照。而按照风俗,结婚前夜去她的家里迎接新娘时,是花费1万5千元,雇的加长林肯车。化妆师,也是专门从省城聘请来的,时时刻刻地跟着,为新娘补妆。至于烟酒糖茶和喜宴的规格,更是全部选用了小城最好的标准。几乎所有前来吃喜宴的人,都羡慕他家的富有,和她家的荣耀。他的同事们都说,这场喜宴,给一个男人长足了面子。她的闺中密友们也说,真真是嫉妒死她了,一生有这样一场盛大的仪式,即便是婚姻不能长久也值了。
但没有人知道,这场喜宴,给他与她带来的烦恼与负累。他们为此两夜不曾合眼,而双方家长的意见,又像那细小的波纹,看似不值一提,但还是时不时地,就乱了他们的心。为了伺候好那些所谓的“贵宾”,她勉强地绽开笑容,一个个地敬酒,连每一个人该怎样问候,都事先要想好,以防不经意间,得罪了某一位,给他们的父母,带来此后工作或人际交往上的麻烦。他们都是喜欢过平静生活的人,素日也不擅长且不喜欢这样的场合,但为了父母的面子,却要装出由衷的讨好和真诚。
可即便是这样,他的父母,还是嫌她不够大方,敬酒时没有做到尽善尽美;她的父母,则抱怨说,他的家人,有些小气,普通客人的烟酒,完全可以再上一个档次。而他与她,则在这些琐碎繁杂的礼节里,于畅想了无数次的洞房花烛夜,疲惫不堪地躺倒在床上,便沉沉睡去。
是第二天醒来,他看着她脱落的妆容,她闻着他身上依然浓重的酒味,这才有些尴尬地想起,他们已是成为一直想往着的幸福的夫妻。可是,为什么,那些想象中的甜蜜与欣喜,并没有来到,深深涌起的,却是无以复加的失落和惆怅?那场渴盼中的浪漫经典的婚礼,终于还是被这吵嚷世俗的一切,给取代了。
澄明的心。
母亲刚过了五十岁,眼睛便慢慢地看不清楚。偶尔两个人拌嘴,我一生气走出去了,她还一个人坐在床边,边摸索着找手绢擦眼泪,边絮絮叨叨地数落我的百般“恶行”。
我看了常不忍心,又退回来将手绢递给她。她当然看不见,继续在床头上找,直到我颤着声,喊她,这才循声转过身来,“看”我一眼,怔一会儿,便高声地,继续“抨击”我。
找到第二个男友的时候,当然要遵守她的命令,带回家来给她“看”。她高声地与男友说话,又很认真地看着他,眼睛睁得很大,里面满是欢喜和幸福。好像,被爱宠幸着的,是她自己。我看得出她对这个男友还算是满意,否则不会这样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而不像对上次那个男友,看也不看一眼。顺理成章地,便要结婚。把这个消息说给母亲听时,她没言语,转身进了自己的卧室,取出一对银镯子来,戴我左手腕上,这才低低地,恳请似地说:你们在这儿住上一星期,再商讨结婚的事不行吗?不愿意惹她生气,只好从命。男友却是不怎么高兴,说给我一大堆住起来不方便的理由。我知道他其实是自由惯了,不愿意有人在眼边晃来晃去地监督着,便说:怕什么,反正,你做什么事,我妈都是看不见的。他很是吃惊,悄声说:可我明明觉得,她的双眼,能深深看到人的心里去。
我只当他这是心理作用,便叮叮当当地走开去,准备午饭,任母亲又过来,“缠”住他,滔滔不绝地说。没过两天,男友便明显地烦了,尽管声音依然是温和,脸色却鲜明地难看起来。有时候母亲正与他拉着家常,他便要起身走开,被我用满是洗衣粉泡沫的手哀哀地挡住了,这才烦乱不安地又陷进沙发里去,继续听母亲的唠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