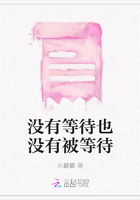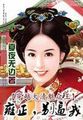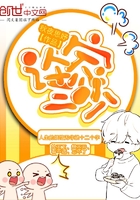老外们都诧异地望着母亲,他们奇怪一个人的手掌怎么会变成这样。我站在一边,心中充满了酸楚和苦涩。
我记得那时候还带着母亲和弟弟一起去看《同一首歌》的演出现场。《同一首歌》是那时候中央电视台最火暴的一个节目。那天演出现场人山人海,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母亲可能是所有观众中年龄最大的。母亲看着无数张激动的面容,听着山呼海啸的声音,她异常惊讶,这些人口中同时喊出的一个个名字母亲都没有听过,那一个个名字代表着一个个曾经或者正在走红的歌星,而母亲一个都没有听过。像母亲这样年龄的农村老人,已经完全被抛弃在了现代文明之外,他们年复一年关心的只是一日三餐和春种秋收,那些霓虹闪烁的场面和霓裳飘飘的画面,对于他们来说,是完全奢侈和陌生的。
就像观看美国交响乐团演出后,母亲只记住了那个黑人大胖子;多年后,母亲向我提起那天夜晚的《同一首歌》演出现场时,她说:“那么多人,比咱这里庙会上的人多多了。娃娃们一直都在喊,不知道都在喊些啥。”
母亲除了关心那些娃娃,还关心演出票价,一张票就高达680元,让母亲每次提起来就惊讶万分,“那么高的票价,怕怕的死呀,还有那么多人看。城里人咋来这么多钱?”
美国交响乐团和《同一首歌》的演出门票母亲一直保存了好多年,似乎在母亲的眼中,那两张票就代表着南方大都市的生活,那是一种他们完全陌生而又心驰神往的生活。我的一位同事说,在他小的时候,他们村子里有一个人去了一趟北京,回来带了一包点心,点心吃完了,而包裹点心的草纸被那个人珍藏了很多年。
城乡之间巨大的差别,完全超出了母亲这辈人的想象力。只要一走在大街上,来自偏僻农村的母亲就会惊讶万分,她像走进了一个无法想象的神奇世界。马路上那么多的小卧车,一辆接一辆,都是私人掏钱买的,这一辆车就要几万几十万元;而一个农民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么多钱。超市里那么多的商品,堆积如山,想买什么就有什么,想买多少就有多少,啥都不缺,啥都能买到;而乡村每隔十天才有一个庙会,庙会上也仅是一些有限的商品。市中心的名牌服装专卖店,一件衣服就几千元,一双鞋子也高达千元,还排着队购买;而母亲此前一直穿着自己手纳的布鞋,一件20元的洋布衣服穿了十几年,这次要来我打工的城市,才在庙会上买了一双布鞋和一身衣服,花了近百元,让她一直心疼地念叨个没完……
《同一首歌》的票是报社一个女同事给的。每逢有演出的时候,演出单位就会把一些票送到报社,报纸上就会刊登一些演出的消息。每逢有票送过来,报社就会在公告栏张贴启事,员工认领,先到先得。一些女同事特别喜欢观看演出,所以就特别留意公告栏。那天,报社一个胖胖的女同事听说我母亲从遥远的乡下来了,就把自己领到的三张票送给了我,而此前她是准备带着自己的父母去看的。
那位女同事非常乐天,又高又胖,体重高达200斤,她有一句在圈子里流传甚久的格言:“因为善良,所以丰满。”她曾经发起了一个“胖妹俱乐部”,定期举办活动,让很多因为肥胖而自卑的女子摆脱了自卑。现在,这个俱乐部的会员已经多达千人,遍布全国。
有一次,我带着母亲和弟弟去了肯德基店,弟弟看着窗口上的价格表说:“我不吃了,我不爱吃这些东西。”他其实是舍不得让我花钱,那些高昂的价格让弟弟感到恐惧。无论我怎么劝说,弟弟就是不吃。
后来,我只给母亲买了一个汉堡和一杯可乐,还有一包薯条。母亲吃着汉堡的时候,我问:“好吃吗?”母亲说:“好吃得很,不知道人家这是咋做的。”母亲把汉堡吃完后,我问:“还吃吗?”母亲为难地看了看我,犹豫了一下说:“吃饱了,不吃了。”我故意说:“这东西很便宜的,没有吃饱我再买。”母亲小心地问:“刚才吃的那个东西,要多少钱?”我说:“不贵,只要一块钱。”母亲终于释然了,她笑着说;“那就再买上一个。”
母亲吃饱后,我们一起走出肯德基店。母亲回头看着肯德基门口的那个大胡子老头儿,高兴地说:“今儿个跟着我娃把外国人的东西也吃了,妈真是有福啊。”
然后,我就上班去了。
晚上回来后,我突然看到母亲很不高兴,就问怎么回事,母亲说:“你咋能骗我呢?你今儿个晌午就花了40块钱,啊呀,吃一顿饭就花了40块,早知道我就不吃了。”我知道真实情况是弟弟告诉母亲的,40元钱的一顿饭,是母亲想也不敢想的。一直过了很多年,母亲还在念叨着那40元钱的一顿饭,觉得太浪费了。
母亲在城市的那几天,我们每天晚上都睡得很晚,经常会说起小时候的一些事情,说着说着,就会突然流下眼泪,感觉既心酸又温馨。
和父亲一样,母亲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这一生苦,母亲总是和“低标准”的年代比较。所谓的低标准,就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那三年,官方口中所说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很多人被饿死。母亲说那时候连榆树皮都吃光了,只有牲口才吃的野草也都被人吃光了,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绝户。绝户,就是一家人全都死了。还有些地方出现了“易子而食”,互相交换孩子吃。
母亲说,现在的日子不知道比以前好了多少倍,“过去的都是好年景”。和父亲一样,母亲也总是这样说。这对老夫妻和绝大多数中国农民一样,这一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抱怨,再苦再累也不发一句牢骚,他们对生活总是充满了感恩。
有时候,钟封夫妻也会来一起聊天,房间坐不下了,我们就搬几张小板凳坐在楼顶上。遥远的城市里,灯如星河,而脚下的村庄,声如波涛,空气中飘荡着煎炒的油香。“城里面就是繁华,就是好。”母亲说,“和乡村比起来,真的是天壤之别。”
钟封夫妻听不懂母亲的方言,总需要我充当翻译。当我把母亲口中的“繁华”和“天壤之别”翻译给他们时,他们深深地惊讶,怎么农村老太太也会说成语?他们不知道我的家乡尽管是一个偏远的乡村,可在先秦的时候,那里就有人居住,此后,秦汉三国、隋唐宋明,那里一直作为中央统治的区域,各朝各代官府的文告张贴在集市上,那些文言词汇就走进了老百姓的耳朵里,留在了心中。
有一天晚上,我们突然就说到了盗墓。我们那里的古墓很多,历朝历代无数的官吏死亡后,都会把尸首埋在那里,以求荫庇后世。据说,我们那里的风水很好。那些机关算尽的人没有想到,他们为后世的盗墓贼提供了发财的机会。
曾经是文物商人的钟封说,盗墓是一个古老的行业,确实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三国时期,盗墓曾经合法化,曹操的军队中,有一种官职叫做“摸金校尉”,其实就是带着人去盗墓。三国时期由于连年战争,百姓普遍都很穷,曹操诗歌中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在这样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筹集军饷?所以,曹操就盯上了盗墓这一行。三国中的蜀国位于天府之国,吴国位于稻米之乡,都比较富裕,而最贫穷的就是魏国了。但是,挖人祖坟毕竟是不光彩的事情,在曹操时代的所有文献中,都没有记载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只流传在民间。
这时,弟弟突然说:“狗剩叔现在就盗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