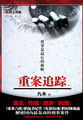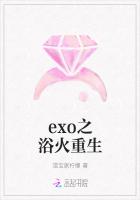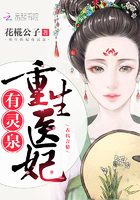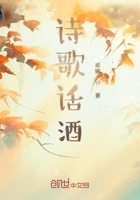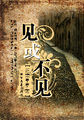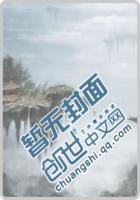那年初秋,母亲来到了我所工作的这座南方城市。
这是母亲第一次来到大城市。此前,她连县城都没有去过,她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与家乡相隔十多里的山下的乡镇。那个乡镇每隔十天就有一次庙会。母亲每隔几个月,就和同村的婶子们提着竹篮,去庙会上购买生活用品:肥皂火柴、油盐酱醋什么的。每次去山下的乡镇赶庙会的时候,母亲和婶子们都像孩子过新年一样兴奋,她们提前几天就会做好准备,而去“上会”的那一天,都会穿着平时舍不得穿的,一直压在箱底的洋布衣服。
母亲是我们村第一个来到大城市的人,而且是南方的异常繁华的大城市。她是由在县城蹬三轮车的、见过世面的弟弟送来的。
此前,我给家中邮寄了1000元钱,这些钱足够母亲和弟弟买两张卧铺车票。可是,他们舍不得花钱,他们买了两张绿皮车厢的硬座车票,在闷热的车厢里摇摇晃晃了30多个小时,才来到了我生活的这座城市。
这是母亲和弟弟第一次坐火车。
我在火车站接到母亲的时候,母亲和弟弟都穿着厚厚的棉衣,他们在大街上单衣短袖的人群中显得异常抢眼和臃肿。他们站在出站口的墙边,惊恐地看着身边来来往往的人,用胆怯的目光在人群中寻找着我。他们一看到我,脸上的怯懦一下子荡然无存,拉着我的手用粗笨的家乡话又说又笑,惹来很多好奇的目光。
他们的脚边放着两个蛇皮袋子、两个帆布提包。那两个提包是我当初上中学时用来背馍的,已经洗尽了原来的黄色,变成了不灰不白的颜色。我问:“怎么带这么多东西?这么远的路,太难拿了。”
母亲说:“村里人知道我要来你这里,都给你送东西,这都是你叔你婶的心意,我就都带上了。”
我拎起蛇皮袋子和提包,感觉每个都沉甸甸的。我问里面都是些什么,弟弟说:“有大红枣、核桃、绿豆、坨坨馍、花生仁、辣椒面、花椒面,还有脆瓜。”
弟弟说,当时脆瓜在我们那个偏远的山区还没有上市,这是村里一个种脆瓜的叔叔专门挑选了几个熟了的脆瓜,让带给我的。脆瓜,在一些地方叫香瓜,最好吃的是一种叫做“小白兔”的脆瓜,用拳头砸开后,香气四溢。我知道这个种瓜的叔叔,他种了一辈子瓜,小时候我们偷过他无数次瓜,我们趁着月色潜进瓜地里,摸到大大的圆圆的东西就摘下来,然后,西瓜在前面滚动,我们在后面爬动,一有风吹草动,就赶快停下来,全身贴紧地面,心跳如鼓。那时候偷到的瓜几乎都没有成熟,我们到了安全地带后,将这些半生不熟的西瓜用拳头砸开,用手抓着瓜瓤吃,吃完后满手都是黏黏的糖汁……有时候,我们还偷脆瓜,没有成熟的脆瓜瓜瓤很苦,我们只能啃吃瓜皮……第二天,种瓜叔叔看到瓜皮瓜瓤,总会在村中悲愤地叫骂。
没想到,多年后,种瓜叔叔把他的头茬熟瓜给我送来了。
我们先乘地铁,后坐公交车,我们在公交车上用家乡话大声交谈着,完全没有顾及到身边诧异的目光。家乡话咬字很重,尾音较长,即使轻声说话,也像和人吵架一样。而南方话发音轻柔,莺莺燕燕,显得非常好听。浓重的西北方言在南方婉转的语言中,显得极为另类,就像鸟语林里突然传来了粗犷的叫声。
母亲对城市的一切都感到很好奇,她问我地铁是什么,我说,地铁就是地下跑的火车。母亲想了想后,感慨地说:“啊呀,这城里人就是行,地底下还能跑火车,我回去给村里人说,他们肯定都不相信。”
母亲最感慨的是城市的高楼大厦,还有街道上川流不息的车辆。母亲站在一幢大楼前面,仰着头看着,她说:“这楼这么高,都要踮起脚后跟看,嘎嘎肯定都飞不过去。”家乡人把喜鹊叫“嘎嘎”。
我说:“城里就没有嘎嘎。”
母亲疑惑地说:“城里咋能没嘎嘎呢?嘎嘎是益鸟,专吃虫子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母亲想了想,似乎想通了,就说:“城里没有庄稼,可能就不要嘎嘎。”
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在路边等候了很长时间,红灯才转为了绿灯。母亲抓着我的手臂,小心翼翼地迈动着脚步,惊慌不安地看着身边的汽车。母亲说:“这车咋就这么多?一个挨一个,一眼望不到头,就像蚂蚁一样。”
我说:“在城市生活,有房子有车子,就算成功了。”
回到我居住的城乡结合部的那个村庄的时候,母亲兴奋地说:“今儿个跟着我娃来了一趟大城市,坐了地铁,还坐了公共汽车,看了洋楼和这么多的小卧车,这一辈子妈没白活。”家乡人把小轿车叫小卧车,还有的人叫屎壳郎,它确实像屎壳郎一样又矮又小。
母亲还骄傲地说:“恐怕在咱整个乡镇,妈是第一个坐地铁的农民。”
我说:“可能是的,这地铁不是每个城市都有,现在也只在少数几个大城市才有。”
母亲神情严肃地说:“我娃在大城市给国家干事,就要好好干,把国家的事情一定要当回事,不要叫人家戳脊梁骨。”
我点点头。以前每次回家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都会叮咛我“把国家的事好好干”。
弟弟说:“哥,你以后也在城市买房买车,做个城里人。”
我嘴上含糊答应着,其实我知道,要在大城市站稳脚跟,谈何容易。我居住在城乡结合部,这里的每个人都和我一样,都想在这座南方大都市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们现在都还爬在梯子的第一个台阶上,不知道往上还有多少个台阶需要攀登。
我的居住环境很简陋,只有七八平方米的一个小房间,一张床一张桌子就占据了所有空间。迟刀听说母亲和弟弟要来,他就搬到了私立学校去住,把他的房间让给了我。
报社听说母亲和弟弟从遥远的西北来到南方,就将三张演出门票给了我。母亲来到这里的第二天,一家美国交响乐团环球演出,来到了这座城市。
我记得那天晚上,坐在我身边观看交响乐演出的母亲,眼光一直在盯着台上那些高鼻深目的老外,面上带着惊异的神情,她悄悄地对我说:“这些人咋都长成这个样子?和咱的人一点也不一样。”
我说:“那是美国人。”
母亲问:“美国在哪里?比咱家还远?”
我说:“美国在地球那边,比咱家远多了。”
母亲感慨地说:“这些人也恓惶,跑这么远来给咱演出,让咱看。”
母亲和父亲一样,一觉得谁恓惶,就对谁产生了同情。母亲觉得这些漂洋过海的老外们很恓惶,日子肯定也过得不好,才给人演出,就像乡村里那些只有在红白喜事上才会演唱的戏子一样。母亲看着这些老外演出的时候,眼睛里就多了一种怜惜的神情。
那天晚上,给母亲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又高又胖的黑人。那个黑人体重足有300斤,身材像一个圆球,似乎一跌倒就会骨碌碌滚起来。母亲说:“这人咋这么黑,还这么胖。”母亲还说如果这个黑人生在我们村子里,都没人能够养得起。
演出结束的时候,很多人争抢着上前和老外合影。我带着母亲也走到了台下,让母亲更清晰地看这些她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老外。那个300斤重的黑人友好地给母亲打招呼,并伸出手来。母亲也下意识地伸出手去。黑人一握住母亲的手掌,就惊叫一声,赶紧放开。母亲的手掌全是老茧,一辈子被农具磨出的老茧,像砂纸一样粗糙;手指关节处的老茧开裂了,又像刀片一样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