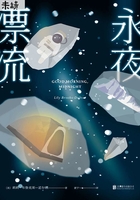太变态,这条街是什么传统,莫非买房买到恶人谷?好汉不吃眼前亏,死在城管刀下老子还是英雄,死在小姐刀下连个讣告都不好写。我奋力逃跑,一定要把这变态菜刀妹甩掉。我跑啊跑,从街东头跑到动物园,又从动物园跑到后面的油菜地……再跑,就是清衣江了。
回头,菜刀妹居然还跟在后面,我指着她大吼一声:再过来,老子就跳河。
菜刀妹冷冷地:你跳,要不我砍死你。
我苦笑:不就多摸了一张牌,至于千里寻仇吗?
菜刀妹:我就是看你不爽,还偷偷换内裤。
我大奇:偷看男人换内裤,变态。
菜刀妹:前列腺老男人有什么好看的,我告诉你——男人一脱裤子,皮带金属扣会发出响声,你毛线毛线的,皮带扣在地砖上敲得叮当的,外裤没换,肯定在换内裤,那就是换手气了。现在,你跳,不跳就砍死你。
这时高姐满脸掉粉地赶过来,抱住她赔笑,又对我说,哎呀,她对男人耍流氓脱裤子之类的很敏感,工作需要……虽然惊魂未定,但我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天才,天才小姐,连这个细节都掌握,当鸡是可惜了,该去当刑警……
高姐脸色大变,对我急急摆手,菜刀妹大喝一声:你才是鸡,你是鸭——挥刀砍来。我眼睛一闭,纵身跳下清衣江。其实很浅,才到膝盖,差点把脚脖子扭到。我站起身来,湿漉漉地回看菜刀妹,惊住。
岸上的她正脱下帽子,转身向我挥舞,上午的风银子般吹过,一袭长发飘扬如旗,她鼻子挺拔,双眉入鬓,像春天里一棵瘦削的银杏树,只是笑容很冷,对我傲慢地说:滚上来。
我确定她真的不会再砍我,又让高姐作保,才爬上来。
一上岸,她就把刀架在我肩膀上,一字一句地说:我不是鸡,是司机,公交车司机,专抓车上耍流氓的,你连喊我三遍姐,公交车司机。我看着高姐,她点点头,我满怀疑云,还是大声说了三遍:姐,你是公交车司机、姐……
她满意地笑了,很漂亮,然后一脚把我踹下河。
这是我第一次看清玖儿的样子,当时我还只叫她菜刀妹,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看到肉铺、餐馆、刀具店里的菜刀,都会眼前发黑,风云滚滚,一女一刀奔袭而来……我支持菜刀实名制,觉得都该叫玖儿系列。
包一头他们确认菜刀妹远去,才嗫嚅着过来,纷纷奋力谴责菜刀妹之残忍、反人类以及没有女人味,要是当时在场,一定把她打成变形金刚再扭送派出所。
我叹了气:包一头,不要以为老子没看见你躲在奥迪车里装睡;毕然,下次不要假装在油菜地里吟诗了;肖咪咪,你逃跑的速度已接近光速了,但下次发射时不要把我当成反作用力……他们羞愧地看着我,不说话。
我忽然哈哈大笑:为何发笑,这里民风剽悍,连一个女子拎把刀当街追杀良民都没人管,理发店的师傅刮胡刀都不见抖一下,多么有潜质的钉子户,丁香街大有前途,油条房大有前途……他们恍然大悟,跟着我哈哈起来。
过户手续下午就办好,产权证本来加急要七天的,两天后也拿到手,肖咪咪虽然喜欢吃回扣,但这货总能把事情办好。我们现在真的是万事俱备,坐等收钱。
熙熙攘攘的房屋交易中心,我忽然有些苍茫,我分明看到每个人大脑里都有两条疯狂的狗在追逐,一条叫“增值”,一条叫“按揭”,全力拼杀那根叫“房子”的骨头。20年、30年……一辈子,所谓中国人房子的理想,就是用自己青春的骨头熬了一锅理想的靓汤,喝下去如饮甘饴,如毒断肠。
而我、包一头、毕然、肖咪咪,是其中最敬业的狗。
站在路,忍不住对天狂吠三声,吓了路人一跳,骂我精神病。我认真地告诉他们,我不是精神病,是神经病,这几天太兴奋了,上火,牙痛。我确实值得兴奋,终于拥有自己的房,自我爸老年痴呆走丢以后,我就不知哪儿才是自己的家,有晚喝醉开了间钟点房给我爸打寻人电话,半天接不通……清洁工把我踹醒才发现,老子睡了一晚的公用电话亭。
我妈死后,我爸就郁郁寡欢,中年时就提前老年痴呆,从军服厂提前病退。他时时不认得我,见我还热情地拉着:你知道李可乐那狗日的跑哪儿偷鸡去了吗……他也不是一直痴呆,清醒时喜欢推演沙盘,制订收复海外两个岛屿的武力计划,由于地理知识较差,常常把东边那个和东南那个搞混,武器配置就不合理,常常让我军深海驱逐舰卡在浅礁中,还算不清比例尺,导弹常常打过了,打到夏威夷。有一次他在一片大面积开阔地带运兵,发现怎么都找不到敌军主力,非常恼怒。我看了看,说你地图拿反了,你那三个集团军此时正在南极,旁边那一堆,企鹅……我说这样下去,你以为保护得了一个岛,其实只保护得了一只鸟。我爸就怒了,在追杀敌人之前就先行追杀我,误伤了邻居家好多鸡鸭。
后来达成协议,他在家里继续推演沙盘,我去省城学地理,学成之后可以帮他制订准确一点的计划……我刚到省城,他就走丢了。据邻居说是跟着一只鸟穷追不舍,再也不见踪影。我其实后悔,不该把那只鸟,跟那个岛,混为一谈。
出去摆个场面,找包一头借他的奥迪,他又说不借。我指着他说,境界。他才肯借,但非要亲自驾驶,说上次我借他的车不仅玻璃窗摸花了,地毯也弄得乱七八糟的,一看就是上车没戴脚套。
包一头就是这么一个烧包,坐他的奥迪车是要戴脚套的,怕我们不从,就要亲自帮我们戴上脚套。变态的是,怕弄脏桃木仪表盘,他甚至还要亲自戴上白手套;怕我们拉车门时指甲把漆刮伤了,还抢先帮我们把车门拉开。这是中国私家车史上一个奇观,一个奥迪车主跑上跑下帮别人开车门、戴脚套,他不司机,谁司机。
我对包一头其实是很失望的,这么优秀的一个养猪大户,前途无量之时,竟为了一个女人,一夜之间性情大变,输得只剩一辆奥迪了,还要学品位和贵族范儿。
他是分不清MBA和NBA的区别的,却一周三天要去理工大学上课,分不清竖琴和弹棉花的弓的区别,却请了一音乐学院老师天天在家弹得乒乒乓乓,他戴着假发套参演莎士比亚剧,那川东腔的吐逼哦裸吐逼,听上去特别像骂脏话。对了还有爵士舞,我看过他一次,那不像爵士,更像烈士,一脸的视死如归,全身的前赴后继,推到红岩上面就是英雄雕像……
曾经跟他深聊过一次,希望以后他还是本色出演,朴实是一种美德,免得让大家心理上有阴影。他叹了一气:嫉妒,你的名字叫女人。戈壁的,我们嫉妒你个屁。那天他还忽然想起什么,透露最近发现喜欢NBA的人多,喜欢MBA的更多,境界已经低了,所以他瞄上了更高级的ERBA。
我看了他很久,建议他连续地大声地念出ERBA。这货果然就连续地念ERBA、ERBA、ERBA……然后惊慌地停下。
我点头:是的,这ERBA读到最后,其实就是一二B哎,还是别读了。
但包一头不管一B还是二B,坚持亲自驾驶,对于一个贵族的要求,我只有从了。
出发前,肖咪咪飞快算了一笔账:油条房花了78万,红包花了3万,我们四个凑了88万还剩7万。我说这笔钱暂时不动,当钉子户就要当职业钉子户,打点关节、宣传造势、武器装备、据守油条房的吃喝拉撒都要用钱,就在这7万里了。他们有些心疼,但觉得我有理,交给我了。
其实我是有私心的,因为索拉拉要用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