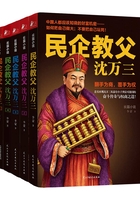于怀是在酒后给袁莓莓打的电话。
袁莓莓在学校的时候大家都叫她红草莓,因为袁莓莓的嘴边总是挂着一层浅笑,脸蛋红扑扑的,所以大家叫她红草莓。
接电话的是一个男音:“喂。”
于怀认为他打错了,因为在那个厚厚的电话薄上,袁莓莓一共有六个。打这个电话他是凭着酒后的感觉。于怀有些吞吐了,可能是酒的作用,甚至舌头有些打结。“是,是……袁莓莓家吗?袁老师,在红瓦学校的袁老师?”
“你等等。”于怀的心一下放松了。
他知道接下来就能听到那个久违的声音。
果然,声音还如草莓那样的甜,她像刚吃过草珊瑚含片。“喂,我是袁莓。”袁莓莓竟然把一个莓字丢了。竟然说我就是袁莓。生活的快节奏使好多事情都这样地剩下去,好多人的名字就是这样把三个字缩成两个,亲呢的时候再减掉一个。那些恋爱的宝贝已经剩掉了感情的孕育,刚建立关系就利利索索地进入实战。
该报自己的名字了。
“袁莓莓,我,我是于怀。”
“于怀?”
“对,于怀,还记得么?”
“记,记得。怎么能忘记呢?于怀,你现在在哪儿?还在那个机关,在那个所?”
“不,不说,我在w市,在晚报做编辑,有时候也出去采访,写一些文化通讯。袁莓莓,刚才的男音……”
“哦,孩子,我的孩子。”
“对不起,我以为是你家的主人翁。”
“没有,没有,没有,哦,不是,不是。”
“方便吗?说话。”
“说吧,于怀。”没有想到电话打得这样顺利。于怀胆大起来,简直要直奔主题了。“我们,我们能见次面吗?人到中年了,静静地谈一谈……”
“好吧。”
“在W市行吗?”“行,行吧。”
“到底行不行?要不,我过去?”
“就在市里吧。”
电话是十天以后打来的,是一个周六的午前。袁莓莓已经在心湖公园等他。
看到袁莓莓时,他心有些颤,他把手握过去。他们站的地方是一片竹林,苍翠的竹子在风中晃动,竹叶发出哗哗的响声。袁莓莓竟然跑了过来,把头伏在他的肩上,低声的抽泣从肩头往心里拱,把他的心一点点润湿。这让他有些发蒙,他抱住她,抚摸着她的长发,往事的影子一下子回到心头。那时候袁莓莓留的是一条长长的独辫,每次下课亭亭地拽着长辫绕过讲台,仰着的脸带着笑意。每次下课袁莓莓不走出教室,他总是纹丝不动。正是这头秀发使他在毕业两年后给袁莓莓写了一封情绵绵的信投石问路。
当然是一口回绝,不然他们可能是另外一种情景。
绕过竹丛,他们在一处荷塘边坐下。
袁莓莓说:“时光真有意思,毕业十几个年头,好像不过睡了一个长觉,在长觉中做了几个梦而已。”
及至问到各自的生活,于怀才知道袁莓莓原来一直沉浸在一种无奈之中:丈夫和另一个女子发生故事,袁莓莓离异和儿子生活在一起。儿子是她的寄托,事业也是她的寄托。她在孤独中敬业,记载她荣誉的红本儿已经装满了一个抽屉。
于怀把一杯酒递过去。
于怀的心情很复杂,但还是有一些耿耿于怀。他提到那封信,说那是他对感情憧憬最炽烈的时候,当时,他把写与不写揉成了几个纸团,又把那些纸团抛到城外的河里,他怕捏住的是一个“不”字。
袁莓莓手握酒杯,仰着细长的脖子,掩下长长的睫毛,吐出如兰的一口长气。“你,你不懂女人!你那样地经不住回绝。”袁莓莓站起来,脸向窗外。“于怀,我曾经一直等待你的第二封信……”袁莓莓猛地转回头,把手中的酒一饮而尽。
多少年了,心情一直这样沉浸着,因为酒后的电话有了这样的一次重逢。直到看着袁莓莓远去的身影,他才知道:爱,需要执著!
再回头,他看见草丛中一串红红的草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