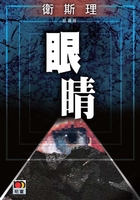父亲的一亩三分地在村东。
我们村都把那地方叫黑土坑,说那块地土中浸油,极肥,是长庄稼的一片好地。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对土地有一种深挚的爱,没事的时候就守在田里,把一亩多地侍弄得干干净净,不见一根荒草。
我进城里以后,几次劝父亲和我们一起进城,母亲去世后,我越来越放心不下我的父亲,他毕竟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可父亲一直执拗地不肯。
这年秋季,父亲捎信让我回去一趟,并嘱咐我一定要带回那部照相机。
我匆匆地回了家。
父亲把我带到了田头。父亲说:“你爱照相,报纸上发过你拍的什么照片,今天你给我也好好地照几张吧。”
我问父亲照哪儿。
父亲说:“照这地啊!你看这庄稼多好啊。”我望过去,是啊,齐胸高的玉米杆绿盈盈的,风吹过来,长长的叶子悠悠地晃动着,半空的鸟儿在翩翩飞舞,白云在鸟的头顶兀自地白着。
这天,我为父亲拍了好多照片,回到家,父亲问我:“知道为什么让你拍照么?”
我摇摇头。
父亲说:“你不是一直让我丢地吗?”
我惊喜地问父亲:“你同意了?”
父亲沉重地点了点头。父亲说:“等收了这茬秋就丢。”
秋后,父亲又让我回去。
父亲说:“地,转租给你旺叔家了,按别人转租承包的条件,给咱个口粮。”
我说:“行。”
父亲说:“让你回来,写个简单的手续。”
手续写好,父亲唤了旺叔,我们一齐往地里去。我们站在土地前,站在田头看着土地,收获后的秋天一望无际,到处是收割后的空旷。行动早的人家已经在犁地,拖拉机的嗡嗡声震动着田野,地头的野菊花在风中绽放。
父亲给旺叔点了地界。父亲说:“老旺,地就交给你了,要种好,我虽然不种了,但我要回来看我的地,地的主人毕竟是我。”父亲深情地看着土地,一层湿润浸上了他的眼角。
好大一会儿,父亲叫我。父亲说:“你好好认认咱家的土地吧。”父亲指指地头的一根树桩:“这就是咱地的记号。”
我点点头。
父亲很专注地站着。尔后又对我说:“孩子,你看到了什么?”
我仰起头,看着眼前的土地,看着土地那头氤氤着雾气的河水,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父亲。
父亲又一字一顿地问:“你看到了什么?”
我支吾着:“就、就是地啊。”
父亲忽然很严厉地说:“你个不孝子啊。”
父亲的话使我浑身一颤。我猛地抬起头,看见了我家土地的那头一方小小的土丘,坟丘上长着青青的葛巴草,坟前竖着一块矮矮的墓碑。那是母亲,那是已经离开人世整整十年的我的母亲啊。
父亲说:“这地咱种了十几年,我陪了你母亲整整十年了。这是你母亲临终前我许她的愿,现在我还愿了。”
我们无言地走向母亲的坟前,在坟前默默地站着。我再也忍不住流下泪来,为母亲,为父亲的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