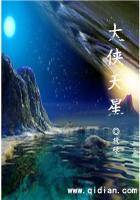要知道,当时在我们农村,除了电影和广播不常播放,电视更是稀罕之物,至于其他的文艺活动,诸如唱戏,文艺会演,除了过年过节以外,平时几乎碰不上,这些憨厚纯朴的村民们日常生活惟一的乐趣就是三五成群,凑在一起谈天说地,讲古道今,他们热情洋溢如临其境的讲述和表演,令我收获颇丰。
我的美丽的家乡大冶,地处鄂东南。往东,距离革命老区大别山区咫尺之遥,往北,距中国革命红色根据地南昌和井冈山也只有200里。昔日的革命烈火曾在这片土地四野熊熊燃烧,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家乡曾是红军从鄂南进军井冈山会师的主要通道,当时家乡热血男女纷纷背井离乡参加红军,誓死追随中国共产党干革命。先后涌现了开国战将余立金、伍修权、石海山(石继明)等战功赫赫的革命名将。在大冶阳新交界的南山头,濒临阳新的刘仁八镇,共和国元帅彭德怀和大将滕代远等人当年就是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小镇成立了令国民党反动派闻风丧胆的红三军团。彭总和数千名红军战士在此生活了大半年,并在在此与国民党反动武装进行过上百次激战。由当年的红军著名将领程子华领导的闻名中外的“大冶兵暴”,就发生在我们大冶县城。
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了这一大片沸腾的土地。为了缅怀革命先烈,教育后辈新人,新中国成立后,当地党和人民政府不但在这些烈士的长眠地成立了南山头革命纪念馆和红八军革命纪念馆,还在大冶的青龙山公园内建立了一座高高耸立于青松绿野之间、由聂荣臻元帅亲笔题名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多年以来,大冶南山头革命纪念馆和红八军纪念馆的负责人就由时任殷祖文化站站长的殷显扬兼任。这一方红色土壤催生了许许多多的革命歌谣,我为了搜集整理这些民族文化瑰宝,经常往来于多个乡镇间,寻找多位会唱革命歌谣的老红军和烈属。记下了一首首令人激动的红色歌谣,每当我听到一首好歌,总是如获至宝。
笔会结束后,我与殷显扬老师就开始了书信来往。我常把自己写的文稿寄给远在殷祖文化站的他。如果不是特殊的原因,他总会在一周内给我回信,不但在我的原稿上密密麻麻地写满的他的修改意见,而且另外付上一两页嘘寒问暖的信。
在这些书信里,他不但关心我的学习和创作,更像一位慈善的长辈一样关心我的生活。知道我爱读书,他还经常随信寄来几本诸如《长江文艺》、《当代作家》等省内外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学杂志。
有一次,我将一篇五六千字的小说抄在无格的白纸上给显扬老师寄去,很快接到他的回信。他在信里批评我说:如果我这是正式投稿的话,责任编辑一般是不会看的,写稿子应当用方格稿子认真誊写,切不可字迹太草……殷显扬老师知道我很可能是没有稿纸,几天后,我收到了他寄来的一大包共十大本方格稿纸,捧着稿纸如同捧着一颗热乎乎的心,尤其见老人随同寄来的信:如果不够,请随时来信告诉我,好歹我现在是文化站长,又兼任大冶南山头革命纪念馆长和红八军纪念馆长,免费的稿纸还是有的……
我双眼一下湿润了——这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样的纯朴而又真挚的感情而令人感激涕零的呢?那个时候,我不但与老师经常书信来往,而且只要一有空,就会特意跑五六十里的山路前去看望他,向他当面请教有关写作方面的问题,向他借书看。后来,我立志告别贫困的家乡外出打工,朝着南方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地流浪;再后来,我又应征入伍,成为南海舰队海军陆战旅的一员,并很快在部队里担任连部及团部文书,逐渐以发表几篇习作的作品而受到舰队政治部有关领导的关注,随后调入军区机关专门学习文学创作……
我的生活总在动荡与变迁之中,然而这十多年间,无论我置身何处,脚步又将落往何方,都会写信向这位家乡文学前辈问声好,报个平安。记得就在我入伍的第一年,由于那时我已经在军地的几十家报刊上发表了一大迭各种各样的作品,老人又推荐我加入了黄石市的作家协会,成为了家乡作协的一名会员。对于我们这一老一少长达十多年的深厚真情,殷显扬老人曾于1998年1月,在自己身患癌症的情况下,充满感情地在我们家乡《黄石日报》上撰文写道……
《南方都市报》有位名记者叫石野,人称“打虎记者”。由于他追踪报道了“广州市银河村治安员打人”一事,在广州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响。由于《南方都市报》为民众仗义执言,使该报获得特好的声誉。这位撰稿人石野得到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有关领导的支持。他是何许人也?其实石野是我们大冶市大箕铺石应高村的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农民,名符其实的打工仔。他在中学里读书就很爱好文学,每年寒暑假他都要拿着文章来找我看,多半都是他写的故事和小说之类的作品。我是个文化站长,自然有创作辅导的义务。不过我和他隔着公社,后又隔着乡镇,他写作认真使我大受感动。当时他家庭非常困难,跑五、六十里路到殷祖来,我再忙也得放下手中活来看他的稿子。记得高中他刚毕业那年,县文联在一个乡镇召开重点业余作者培训班,我推荐石野去了。那次主要是给这个乡镇搜集整理编一本民间传说故事集。在这次培训班上,小石就在他写的文章里崭露头角,文章发出来受到名家的赞誉和夸奖,同时我也感到很欣慰。后来他参军了,还常常给我寄信来。石野在南海舰队里服兵役,而且是年轻人趋之若骛的中国海军陆战队员。这期间,我也曾在解放军的报刊上发现有他写的文章和新闻报道,不管文章长短我都看。记得有一次他寄给我一本“海军文艺”,我从中读到了一篇他写的近万字的小说,使我认识和了解了大海和军人的生活。服兵役期满,哪里来哪里去,转业后他仍然是回乡当农民。但他这次回来后不久就去了广东,大广州那潮水般的南下打工仔中,他是一个幸运儿,在一家报社打工。因为他有中国一流的军队服兵役的特殊经历,又多次立功受奖者和黄石市作家协会会员证,有爱好文学的特长,就这样他了一名一线记者。后来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社又主办了《南方都市报》,急需招聘一批编外记者,自在是临时工了。石野去应聘被录取了。由于他有写文学作品的功底,加之他对社会生活的洞察言观色力;不怕辛苦,日以继夜地工作着。白天下去跑,晚上回来写,甚至双休日也不体息。有时我从报纸上看出,他写的报道不但有一定的份量,而且很短小,但信息量却很大,都是民众日常所关心的事,甚至是身边微而甚微的细小事,报道出来却又成了大新闻。当然他也写了不少长文章,整版整版地刊出,往往引发读者的兴趣与共鸣。紧接着是追踪报道随之而来,有时还配上自己拍摄的照片,来个立此存照,一浪掀起一浪,高潮迭起。一些被曝光的单位和个人以及那些弄虚作假者和歹徒,为此恨之入骨。有的闯入报社无理取闹,有的派人“追踪”记者,企图寻衅闹事。当记者不但要有锋利的文笔,还要有牺牲精神。石野恐怕也就具备了这种精神,对待歹徒的恐吓和报复他无所畏惧,他从海军里锻炼出一身正气,像海石一样能经受海浪的冲刷和洗礼。就拿治安员打人一事来说,文章刊出后,各地读者向报社打去千余次的热线电话,传达室真和信件就有数百封,港澳媒体、海外各地华人办的报纸都纷纷转载和报道,还有华要捐款成立以石野为主的广东新闻记者见义勇为基金会。最近据石野来信告诉我,他的任务是负责公检法司一线,每天都要收到不少读者来信,成为读者最热爱的记者。一位记者能受到民众信赖和热爱,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我衰心祝愿他能在新闻战线上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每当我重读起这些发自肺腑的真诚文字,我都会油然想起已驾鹤西归的殷显扬老师,我的耳畔会响起他那爽朗的笑声,我的思绪总会缭绕着他对我的循循善诱的教诲;我的眼前总会呈现他清瘦而又颇有仙风道骨的的形像……我的另一位文学老师胡燕怀,当时因在北京赶写一个电视连续剧剧本,没能赶至家乡为老友送行,后来他怀着悲痛的心情于1999年4月末,在《黄石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情真意切的,题为《老殷,好走!》的悼念文章,称他是“……一个能给人带来快乐的人,黄石文坛应该铭记着一个永远的老殷!……”表达了对这位文坛老友的深切缅怀之情。
现在,我怀着极为沉痛的心情写下上面这段文字,又一次回忆起老人昔日对我无私帮助的情景,时间正好已过去了整整四年!
此时,随着窗外的阵阵寒风,天空下起了深秋的第一场雨。一场秋雨一场寒。朦胧的秋雨,打得外面院落里的树叶沙沙直响,使缩在狭窄的低廉平房中的我,不由打了几个寒战。
面对苍茫的北方朦胧的雨帘,面对窗外那一片片随风而飘落的枯叶,我的思绪不由又飞回了遥远的鄂东南,回到了我的故乡大冶。我又陷入了对这位慈祥的老人深切的回忆中。
老师,此时身在天堂的您,是否已看到了我的这段文字?作为您的学生,我怎么能忘记您昔日在小雷山笔会上每一天为我多买份菜的慈善呢?那不仅仅是一份菜,是一份发自肺腑的老一辈对晚辈的殷殷关爱啊。作为曾受到过您热心帮助的小字辈,我又怎能忘记您昔日热心地为我改稿,字斟句酌,为我寄稿纸的拳拳真诚呢?
呵,老师,我看见您又在家乡的案前笑容可掬地教导我做文为人的道理;我又看见您此时正在听我用心灵与您说话……
《南方日报》总编辑的批示
时间很快过去几个月了,然而那篇有关我们在王圣堂暗访的有关报道,《南方都市报》一直没有刊发。等候了这么长时间,我明白稿子是发不出来了,但是,我想了解个中原由的心情却是越来越迫切。邓世祥也和我一样,多次去任天阳及编辑部等处打听我们王圣堂的稿件什么时候才能发出来,但每次的消息都不理想。在以后好长的一段时间中,他全心全意为此事奔忙着。
一天,我再一次出现在任天阳的办公室提及有关稿子一事,他挺为难地挠着头皮说:“平时别的稿子我还能作主,但你们这篇稿子由于影响太大了,我真的无权作主,”末了,他又轻声对我说,“这事邓世祥问过好几次了,这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独家新闻,作为策划人,我怎么不希望这篇稿子早日发出来呢?但你们暗访王圣堂历险之事,早在内部传开了,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上面有关领导早已向《南方日报》打了招呼,我们目前不可能发篇稿子了,只能等机会,等风头过去后,我们再找个合适的时机发出来——石野,我也很为难呀……”
任天阳最后向我俩摊着双手说,“这样吧,你最好去找一找老关或程益中,催他们一下,看看他们怎么说吧……”
眼见自己的报纸发稿无望了,邓世祥又特意拿着稿件几次找到《南方日报》的内参部,希望作为省委党报的《南方日报》能够将这篇文稿以内参的形式刊登出来,好让省委及省政府的有关主要领导能看到,并对此作出批示,以便广州有关主管部门能更加大力度打击那伙作恶多端的黑恶团伙,彻底铲除这个长期限盘据羊城的大毒瘤,为民除害。
稿子递上去后,又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还是音讯全无。邓世祥不由急了,接连几次跑去问有关负责同志,最后对方无奈地答道:像这样重大问题的内参一定得报呈报社最高领导审批,这个稿子早已递交给报社高层领导了,只能耐心地等候消息。
这篇稿子《南方日报》的内参到底也没能发出来。直到后来8月上旬,我们才得到了这个姗姗来迟的消息。由于这件事影响太大,也或许是为了对我们这两个为了报社的利益,几乎丢了性命的员工表示安慰吧,《南方日报》在将这篇尚未能发出的稿子递还给邓世祥时,还特意附上领导的亲笔批示。尽管这不是我们的希望所在,但这个迟到的慰问也是聊胜于无的。
我看到,在这篇不到两百字的批示中,时任《南方日报》总编辑的范以锦同志,不但充分肯定了我们的敬业精神,而且郑重地指出“此次采访太冒险了!我看了这段材料我心惊肉跳了好几次……”
直至现在,范总的这份情真意切的亲笔批示还小心地保存在我手中。两年后,我因为在忍无可忍之余救助了一名来自河南光山农村的弱女子陈良琴和她的儿子邓珂向那个长期玩弄和欺骗她们母子俩的花心男人邓世祥讨公道时,曾遭受到对方将此事加以编造和歪曲事实对我进行恶意的的诽谤与诬陷时,我还特意将报社老领导的这份批示作为有力的证据提供给有关部门。
现在,请让我将这份原《南方日报》社总编辑、现任《南方日报》社社长的范以锦同志亲笔批示的全文摘录如下吧——
石野,邓世祥同志精神可嘉,多次不怕艰险采写有价值的新闻。不过,我觉得此次采访太冒险了。这些场所不是不能采访,但深入虎穴,在发现有人跟踪的情况下继续冒进,太危险了。而且万一给扫黄专业队抓住,也无法说清楚。尽管你可以辩解经领导同意,但人家还会反过来怀疑领导当保护伞。我们的优秀记者差点成了刀下鬼,看了这份材料令我心惊肉跳了好久。
这份材料内参也不能发,上级领导看了之后反而会指责我们的采访方法不对。可考虑直接向公安机关报警。
范以锦
1998年8月8日
直到大半年后,也就是1999年1月份,广州公安部门在位于广州火车站附近的华南影都和三元里、王圣堂一举捣毁了一个有黑社会性质的色情抢劫团伙,并于广州白云区的新市镇及芳村区、荔湾区的有关出租屋里抓获了近二十名团伙成员。因为这是警方的主动出击,是他们战斗的成绩,当然要向全社会公布。接着,广州公安局特意邀请了广州地区的主要媒体,如《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广东省电视台等新闻单位参加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这一情况,并向所有新闻媒体提供了一篇通稿。但是令我感到不解的是,此次新闻发布会惟独没有通知最早有记者就此参与采访追踪、曝光内幕而迫使省市区三级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侦破此案的《南方都市报》……随后,广东主要媒体纷纷在各自的显著位置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下面就是《广州日报》对此案的有关报道:
床下抢匪专候嫖客入瓮
广州市公安局捣破一女色引诱抢劫团伙
本报讯广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经过一个多月的缜密侦查,前天捣毁一个专门以女色引诱嫖客进行抢劫的犯罪团伙,抓获6男5女共11名犯罪嫌疑人。现初步查明,该团伙仅今年3月便作案13宗,劫得价值数万元的赃款赃物。11名犯罪嫌疑人昨天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今年2月,市公安局机关刑警支队反车扒大队接到群众反映:广园西路环市西路口一带色情抢劫活动猖獗。刑警立即着手进行侦查。由于事主是因嫖娼被抢,大多羞于报案,侦查十分困难。刑警通过对犯罪嫌疑人连续进行跟踪守候,逐步查明了他们的活动规律。该团伙一般在上午9时许“开工”,到广园西路环市西路口一带,用女色引诱嫖客至王圣堂,瑶台的出租屋实施抢劫,下午5时左右“收工”,作案时均有同伙在屋外望风,而且每次都分成数伙作案。
刑警继续跟踪,又发现该团伙经常聚居在白云区新市镇棠下西街的出租屋,遂于25日上午7日时果断出击,将正在蒙头大睡的五男五女抓获。但是,该团伙头目“老王”却不在其中。刑警正在焦急之时,“老王”自己送上门来。原来,“老王”因女友流产,过来取钱,结果被刑警候个正着。
落网的11名犯罪嫌疑人,除两名女子来自江苏省外,其余均是从湖南窜到广州的,男女之间均以“夫妻”相称。
作案时以女色引诱嫖客到王圣堂、瑶台的出租屋,事先由两名男子预伏在床底,数名男子则在屋外望风。当嫖客嫖宿时,床底的男子钻出来,屋外的男子也冲进屋,对嫖客进行恐吓、抢劫财物。在把嫖客放走后,他们派人尾随,如嫖客报客则立即转移作案地点,如没有报案则继续利用原来的出租屋作案。(张翼华、谭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