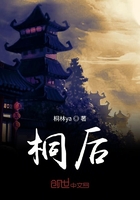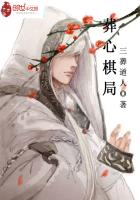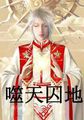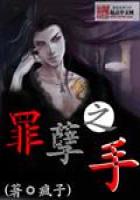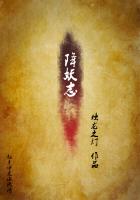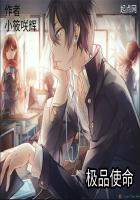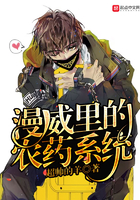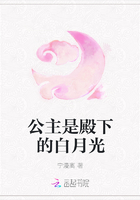左右为难,李渊渐失主见
尹张二妃,卷入玄武之变
公元626年,中原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对李氏家族来说,十分不幸,对大唐来说,却是幸事。
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这一年,李世民发动政变,杀死太子建成、齐王元吉,随即成为太子。不久,唐高祖李渊让位,李世民登基。
表面看,这就是一场权力之争,历朝历代,并不少见。其实,没这么简单。
李世民杀死了亲哥哥、亲弟弟,似乎心狠手辣,问题也没这么简单。
在玄武门之变背后,始终有一个幕后黑手,缠绕着,弯曲着,扼住了李氏家族的喉咙。
1.三子大闹舌头宴
李渊有意挽狂澜
阅读第一眼
玄武门之变:一场舌头宴?
玄武门之变,本质是李世民夺权,表面却像一场“舌头盛宴”:你嚼我的舌头,我嚼你的舌头;你泼我脏水,我扣你帽子,最终酿成武装政变。
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在尹德妃、张婕妤面前嚼舌头,目的是煽动后宫,疏远李世民。
尹张二妃在李渊面前嚼舌头,目的是诋毁李世民。
李世民奋起反击,也在李渊面前嚼舌头,称太子、齐王和尹张二妃“淫乱后宫”,目的是引蛇出洞、一网打尽。
好一场舌头宴!
主要人物关系谱
621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李世民提高了警惕。他发现,女人,以及舌头的能量,不可小觑。
舌头能杀人,女人能杀人;女人的舌头,自然更能杀人。
这一年,李世民灭掉王世充,占领东都洛阳。对唐朝来说,一个标志性时刻,已经到来。
庆贺,必须的,论功行赏。
偏偏这时候,不知哪个妃子怂恿李渊:“陛下啊,洛阳可是隋朝东都,仅次于长安,什么宝贝、珍玩啊,还有隋炀帝多如牛毛的美女,都在洛阳藏着呢!让秦王一人独占,您冤不冤哪?那些宝贝,也弄点给我们分分。要不派我去吧,我不仅给您带回宝贝,还能给您捎一大批美女回来!”
老色鬼李渊,禁不住她们的软磨硬泡,便让一批妃嫔,来到洛阳,搜罗美女珍宝。
老子的命令,儿子不敢不听。李世民虽然反感别人“抢夺胜利果实”,也没办法。只是有一条:进贡老爹可以,但要严格登记,不准私藏。
那些妃嫔,辛辛苦苦来到洛阳,哪能没点私心?想“贪污”点珍玩宝物,却无一不被冷脸拒绝。李世民,也就很不讨后妈们喜欢了。
恰在这时,被李渊从晋阳宫带到长安的尹张二妃,又出头闹事了。
从地方大员,摇身一变,成了皇帝。正所谓位置决定气度,屁股决定脑袋,李渊的本性,逐渐暴露。小老婆无数,倒也名正言顺,皇帝嘛,历朝历代,除了隋文帝,就没几个对老婆忠诚的了。
虽如此,李渊对当年“晋阳宫一夜”念念不忘,依然十分宠爱尹张二妃。
说她胖她就喘,给根鸡毛当了令箭。这俩妃子,还真以功臣自居,宫中无皇后,猴子称大王,两人侍宠卖乖,气焰嚣张。
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不擅打仗,讨好美女的功夫却是一流。两人使劲浑身解数,小恩小惠不断,甜言蜜语绵绵,几个人的关系,甚至超越了“零距离”。
“零距离”的通俗说法,叫出轨。
玄武门之变的导火索,正是李世民找李渊哭诉,指责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到底指后宫中哪位,有人确信,就是尹张二妃。
玄武门之变发生在626年,距“晋阳宫一夜”过去近10年,相比于后宫新美女而言,这两个和李渊已有“十年之痒”的妃子,显得老了。李渊对她们的宠爱,更多体现在心理和感情上。
老爹冷落尹张二妃,建成元吉才有机会。
尹张二妃和太子集团关系甚密,对李世民则很反感,一有机会就吹耳边风,蛊惑李渊,甚至说:“皇太子仁孝,陛下把妾母子托付太子,我们才能安心啊!”
因此,李世民“告密”,很可能就是针对尹张二妃。当然,也有种说法,认为李世民纯粹无中生有、玩政治阴谋,目的是激怒李渊,引蛇出洞,让建成元吉前来对质,趁机灭之。
不管怎么说,李世民在这些妃嫔间,都不大受待见。而621年,因为洛阳一块地皮,父子又险些翻脸。
补充点背景。唐建国之初,律令还不规范,一些森严的等级制度,尚未形成。典型的表现是:李建成发的“太子令”,李世民发的“秦王令”,李元吉发的“齐王令”,和老爹李渊发的皇帝诏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不分彼此。
此时的李渊,似乎有点无为而治,并不在乎三个嫡子的指令和自己平起平坐,任其自由竞争。
这样一来,问题就不可避免:有关部门接到了太子、秦王、齐王的不同指令,该听谁的?
没办法,只好折中:谁下得早,就听谁的。
621年的“地皮事件”,和唐政府“三令并行,等同诏书”的混乱状况,不无关系。
这一年,唐军攻下洛阳。论功行赏,李世民把一块土地赏给了淮安王李神通。
偏偏张婕妤的父亲,也看上了这块地。老办法,走“美女路线”。让闺女给皇上汇报一声,要块地,还不是囊中取物?
李渊不知道这块地已经赏给李神通,一打哈哈,同意了。张婕妤的老爹,大大咧咧,“奉旨要地”。李神通是堂堂淮安王、皇亲国戚,哪管什么妃子她爹?何况,这块地是自己冒生命危险、用战功换来的,岂能拱手送人?
再者,从法律上讲,咱收到了“秦王令”,和皇帝诏书,效力等同。
李神通冷冰冰地说,秦王有令,这块地赏给本人,对不住,您自己再找地儿去吧。
张老爹很生气:你瞧不起我,不就是瞧不起我女儿吗?瞧不起我女儿,不就是瞧不起皇上吗?可又不敢顶撞淮安王,回到家,火没处撒,只能再找女儿想办法。
张婕妤故伎重施,找李渊哭鼻子,添油加醋,添枝加叶:皇上把地赏给了俺爹,可秦王又故意把地给了李神通,什么意思啊?
李渊气不打一处来,把李世民提溜来,呵斥一番:“堂堂皇帝的口谕,难道还不如你的秦王令吗?”
“太子令”、“秦王令”等同诏书,或许是李渊一时心血来潮说的,此时,他自我否定,李世民哪敢争辩?含糊其词,谢罪了事。
世民退下,李渊就犯嘀咕:唉,这孩子,掌握兵权时间长了,越来越独断专行,不听话了,将来怎么办?
张婕妤闹了这一出,尹德妃也没闲着。
尹德妃的老爹,史料上记载,叫“尹阿鼠”。这到底是不是真名字,令人怀疑。因为唐朝有给人改名改姓的习惯,尤其是武则天,她看这人不顺眼,毙了不说,还赐给人家一个很龌龊的姓或名。
有了这样的传统,唐朝的史官,很可能上行下效,给不受唐太宗待见的尹德妃之父改名。权且就叫尹阿鼠吧。
尹阿鼠仗着闺女受宠,作威作福。有一天,秦王府幕僚杜如晦——后来成了著名宰相,骑着马,从尹府门前经过。
马蹄子刚过一半,尹府家奴突然冲将上来,把杜如晦拖下马,二话不说,挥拳便打。杜如晦一介书生,哪有反抗的力气?指头被打折,就差叫救护车了。
家奴边打还边喊:“你算什么鸟人?路过尹府,敢不下马?”
杜如晦挨了顿“暴揍”,鼻青脸肿、跌跌撞撞回到秦王府,找李世民喊冤。世民连忙劝慰,让他安心养伤。还没等他考虑好如何处置,皇上来命令了:马上进宫!
李世民连忙拜见老爹。老爹脸色铁青,劈头盖脸一顿痛骂:
“你看看你,啊?堂堂王爷,居然欺负一个妃子家?老子是皇帝,妃子的老爹,论起来也该叫丈人了,你属下连他都敢欺负?”
李世民这个窝囊啊,自己的人被打,对方还来个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只好根据杜如晦的说法,如实奏明情况。
这个说他欺负人,那个说自己被欺负,都说很冤枉,李渊大脑有点短路,糊涂了。
糊涂,但不迷惘。他依然坚持“信美女不信亲人”的原则,骂了李世民一顿,将其轰走。
两件事情下来,尹张二妃更加有恃无恐:现在的皇上,是咱的老公;未来的皇上(太子),是咱的情人(可能性50%),怕从何来?
有一次,李渊召集五颜六色妃嫔和七拼八凑的儿子们,设宴欢聚。老爹左拥右抱,欢乐无限,建成元吉前后谄媚,龙颜大悦。李世民遭到冷落,不由想起母亲窦氏。
如果母亲还在,三兄弟会如此反目吗?如果玄霸还在——玄霸向来最听二哥的,自己也不至如此孤独啊!
在外,李世民可谓势力强大,可在他最原始的“一家六口”中,两个和他最亲近的(窦氏、玄霸),早已死去;活着的三个最亲的亲人,两个(建成、元吉)几乎反目、离心离德,一个(李渊)对他冷言冷语、如养子一般。
眼前的祥和,眼前的歌舞升平,刺痛了世民。他悄悄躲在一边,念着母亲、玄霸,暗自垂泪。
尹张二妃,把这一幕看在眼里,事后对李渊说:“您设宴款待,大家都挺高兴的,可秦王世民偏偏落泪,什么意思啊?肯定是憎恶我们几个,等您百年之后,必然对我们不利。您说咋办?您可要把我们安顿好啊!”
在她们的蛊惑下,李渊更加倾向于太子集团,疏远李世民。
然而,庆州发生的一起叛乱,却让事情急转直下。
唐高祖武德七年,也就是公元624年,天下基本平定。李渊在打仗上不如李世民,在治国上,却有些手段。经历战乱的国家百废待兴,李渊忙了,替几个儿子担忧的精力也少了,过一天算一天吧。不料应了那句话: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他没工夫忧虑,忧虑居然还是来了。庆州都督杨文干,率众造反。
国家初定,政局未安,几个蟊贼造反,也算不得什么奇事。可这个杨文干造反,有两大特点:
第一,和太子李建成关系密切。
第二,属于“人不聪明,还学人家秃顶”类型的,一时冲动造了反。
这场“特色鲜明”的叛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一叛乱,幕后操纵者还是李建成集团,其最初目标,是灭掉李世民,而非造反。
杨文干曾在太子府打工。太子府,一般叫做东宫。东宫的一把手,当然就是太子了。
杨文干果然能干,充分发挥“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领导”的优良传统,和太子打得火热。他知道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仇视李世民,建成也把他视为心腹,三人多次密谋。
齐王元吉较为“生猛”,顾前不顾后,拿现在的话来说,属于“大脑进水、小脑养鱼”型的。他对哥哥说:“不就杀个人吗,何必这么啰嗦!老子一声令下,上几个猛士,不就得了?”
杨文干随声附和:“就是就是,当今杀个人,跟碾死蚂蚁一样,有什么难处!”
只是建成有些担心——李世民机警,单枪匹马面对敌阵尚无惧色,何况几个禁卫军?
即便如此,李世民功高盖主、势力太大,不灭掉必成心腹大患。因此,太子集团的各项措施,紧锣密鼓。
第一步,私下招募2000壮汉,作为东宫卫士,随时备用。
第二步,从幽州部队调来了300“特种兵”,个个彪悍如虎,体型虽不如施瓦辛格,比《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却毫不逊色。
第三步,派出心腹杨文干,让他当庆州总管。
哪位说了,杨文干既然是他的心腹,留在身边岂不更好,干吗调出去?
建成有自己的想法。派杨文干外出任职,有两个考虑:一是那300特种兵还不大够用,杨文干到庆州的任务之一,是继续物色一批“许三多”,输送给太子;二是万一有什么特殊情况,杨可以在外围动手,里应外合。
别说,太子有点远见,杨文干还真就用上了。
一天,李渊要去仁智宫,让建成看家,世民和元吉跟着。
建成一听,嘿嘿,天赐良机,不容错过。机会好在什么地方呢?
一是自己看家,没跟着去,万一警察问起来,那也好答复啊——可以很无辜地告诉警察叔叔:没有作案时间,不在案发现场。
二是愣头青元吉跟着,自己可以“遥控指挥”,万一东窗事发,还能把他当成替罪羊,多好的事儿啊。
想罢,建成找来元吉,说:“老二(李世民)这次跟老爹去,我看麻烦。老爹的妃子那么多,老二能不趁这个机会巴结、贿赂她们?这些娘们儿收了贿赂,必定抬举老二、贬低我们,对我们大大地不利。该下决心了!”
元吉嘴角似笑非笑:“哼哼嘿哈,你若听我的,老二早就是刀下之鬼了。”
两人秘密安排一番,决定里应外合,胁迫李渊,除掉秦王。
计议已罢,建成迅速安排两个心腹,一个叫尔朱焕,一个叫桥公山,运了一批武器,前往庆州送信给杨文干,让杨迅速起兵,响应元吉。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李建成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准“天下大势”。经历多年战乱,从普通百姓,到将领士兵,人心思稳,不欲再战。
一方面是这种心理作怪,另一方面是预测到李建成不是李世民的对手,杨文干的实力和大唐更不在一个档次。结果,李建成百密一疏,满盘皆输——派去通知杨文干的两名心腹,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