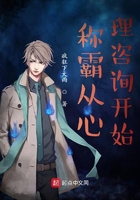最早的舍利容器当属在比波拉瓦及瓦沙里的古塔遗址中发现。这两处古塔遗址,有人认为应该是八分舍利时建立的八塔中的佛舍利塔,是仍然保留其可能性的塔址。无论哪种情况,舍利容器都是圆形盒,而且以在盖顶上伴有钮为特征。
特别是英国人威廉姆佩普从1898年发掘的比波拉瓦大塔遗址,加上1972年印度考古局发掘的两件舍利容器,从其遗址的上、中、下三处发现了包括1件鱼形钮水晶制容器在内的总共8个舍利容器。遗址中部的大石棺中并置5个容器,其中1件上刻记“释迦族的佛世尊的遗骨”波罗弗米文字,对考察研究当初舍利容器具有深远意义。
从阿育王造塔可知,公元前二、三世纪时,佛塔达到惊人的数字,因而,发现的舍利容器遗物也达到相当数量。引人注目的是尽管那些容器是同一时代的,未必沿袭一定的形式,却展示了极富变化的造型。虽说佛舍利就是死者的遗骨,而舍利容器的形制则是建造佛塔的各地风俗习惯、传统形式的根本反映。从仿盒形、瓶形、罐形、塔形等多样器形,能够了解其原因。
关于舍利容器,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容器内、外都多多少少附属有供养品。当然,舍利容器本来是供奉佛舍利的,如桑奇第二塔、索纳里第二塔、萨特达拉第二塔、案达罗第三塔等。无论哪一处在两重容器内都只有骨烬,没有任何附属品,这些确属例外。多数塔使人想到佛典说的七宝供养那样,以金银箔折叠制成花形、星形,金、银、铜指环等环类,各种宝玉类、玻璃、珍珠、珊瑚片,更有金、银、铜钱等供品,附属多种多样的供养品是惯例。
最值得一提的是供品总计达1080件的比波拉瓦塔,而巴提普罗尔塔、米尔哈斯塔、娑婆罗塔等,在多重容器中也装藏着数百件供养品。
舍利容器随着时代的变化出现越来越精美的倾向,公元后的遗物是代表佛像起源的犍陀罗比马兰第二塔发现的豪华嵌玉黄金制舍利容器(2~3世纪大英博物馆藏);表现佛像着名的迦尼色伽王大塔发现的铜制舍利容器(二世纪白沙瓦考古博物馆藏)等精美遗物,至今庄严着往日的佛舍利。
(二)印度舍利容器的形制
与舍利容器造型富于变化一样,容器的质地材料、供奉的方式也丰富多彩。有用单件容器供奉佛舍利,安置于塔内的情形,但多数情况下,佛舍利直接存放于琉璃(玻璃)、水晶、黄金制成的瓶、罐及筒形容器内,以其为核心进而以银、铜、铁、石、陶,偶尔用象牙、木制作外层容器,三重、四重或者六重容器来保护,从内到外依次变大的多层套装容器,即所谓的子母状套装容器是其特色。
发现二重容器的有水晶、金铜制容器的迦尼色迦大塔;水晶与石制容器的巴提普罗尔第二塔;金与石制容器的达摩拉吉卡B2、R4、S8塔及比马兰第二塔;金、银制容器的那揭罗笈第六塔;金、铜制容器的孟加拉大塔A、8室。
三重容器的有大、小三合陶制容器的萨特达拉第七塔;以水晶容器为中心,二重陶制容器保护的波普尔第二塔、第四塔;水晶与二重石质容器的巴提普罗尔塔第一室;金与二重石制容器的卡拉奇A1塔;金、银、石制容器的达摩拉吉卡G5堂、J2塔以及卡拉奇A13塔;金、象牙、石制的达摩拉吉卡G4堂。
四重容器有金、银、水晶、石制的米尔浦尔哈斯塔;以水晶罐形容器为核心,装于滑石制容器之上,置于二重砂岩箱供奉的索纳利第一塔等。另发现的一例六重容器是从娑婆罗塔出土的金、水晶、铜、石质等组成的舍利容器。
采用这样的多重容器表达了对神圣佛舍利的敬重之意,而且释迦涅盘前后的事迹在《大般涅盘经》、《摩诃摩耶经》等经典中均有详细记载,与释迦宝棺也是金、银、铜、铁四重棺椁相联系,可引起大家的浓厚兴趣。
事实上,从波陀第十塔发现的金、银、金铜、铜容器,从拘尸那迦涅盘地出土金、银、铜、铁金属的四重容器,如经典的记述浮现在我们眼前。
在这些印度古塔发现的舍利容器形式,如前所述,虽形制不尽相同,却表现了同一类型的特色,其中如比波拉瓦塔发现的舍利容器那样,圆形容器顶部具有独特的钮形。此类容器腹部为盖、身两部分,盖子的半圆形上部使人想到最上端为安置佛舍利、附之伞盖的覆钵形塔,由此推测舍利器形的变化,其原因在于佛塔造型发生了变化。
伴随着佛塔信仰的盛行,佛塔形状得以进一步展示,而且促使将佛塔原样微型化的塔形舍利容器流行起来。
加仁迦目调查报告中的波普尔第二塔出土的舍利容器,是在铃铛形陶器的外容器中,覆钵上藏有伞盖形水晶制典型的舍利容器,类似的水晶制舍利容器在柏林亚洲博物馆藏品中也能找到,推测为二、三世纪前后的卡拉瓦佛塔出土的滑石制塔形舍利容器。作为犍陀罗物品引人注目的还有神奈川个人收藏的石质塔形舍利容器,虽出土地不明确,但它们如实反映了当时的塔制形式。
因此我认为,这种仿照印度覆钵式佛塔制作的舍利容器,对东方佛教国家的舍利容器也产生了影响。
德国的东方文化学者鲁考克,在西域吐鲁番附近的吐略沟千佛洞发现的被认为是7~8世纪左右的作品一晕橺彩色美丽莲花纹木制舍利容器,覆体状盖顶上备有相轮,明显地沿袭印度古代塔形舍利容器的传统,朝鲜半岛新罗时代的舍利容器也被认为是响铜制的同一类型遗物。另外,作为舍利容器的确切遗物没有传承下来,但正仓院宝物、法隆寺献纳宝物中存在的通俗所称塔碗的相轮钮盒,作为这种塔形舍利容器形式的标准器,按道理是明确的。
迄今为止,虽没有中国方面的事例,但从吐略沟千佛洞发掘的经典、佛教绘画等,有相当的遗物阐述着与唐王朝的关系,加上表现形式上完成中国化的完美器形,使人们充分猜想在唐代早期存在同一形状的舍利容器。
不仅如此,由于时间、地点在形式上略有差异,无论哪一个信仰佛教的国家都会依据本国的塔形制造出相应的舍利容器,追根溯源,这也归功于印度的塔形舍利容器。
二、中国六朝时代的舍利庄严
构筑佛塔之际,佛舍利作为不可欠缺的要素来供奉,也被佛教传来的六朝时代的中国佛塔所继承。但是,与中国产生独特的塔形相同,佛舍利的供奉方法也变为中国式。
这种情形虽然只能依据文献,但根据正史记载最可靠的是《南史》扶南传收录的关于梁武帝改造阿育王塔的记载。梁武帝在其大同年间(535~545)为了改造阿育王塔,从慧达建造的三层塔址中发现了传为东晋时代的舍利器具,在改造这座慧达塔而新建长干寺塔时,沿袭以前塔的舍利供养方式,仍将佛舍利深埋于塔下。从这个记载可知,六朝时代的梁朝也是把佛舍利埋入塔下的土层。
无论是木塔、砖塔、石塔,都如法将舍利埋入塔下的方式本身,是不同于印度的中国式舍利瘗埋制度的最大特色,而且此制度被后世一直继承下来。六朝时代的佛舍利与木塔的构造没有直接关系,被埋藏在塔基中央的地下,上面建立柱,以柱子为中心构筑多层楼阁,屋盖上装饰覆钵、相轮组成的模拟印度佛塔的塔形,似乎是通用制式。
根据上述同一文献记载,舍利器具在东晋慧达建造的木塔里,以装藏佛指舍利的金镂罂为核心,其次为银函、铁罐、石函共四重容器,即使在梁武帝所造的砖塔,象金罂、玉罂、七宝塔、石函那样,部分因材质不同也有象宝塔一样的形式而同样置有四重容器。这样的子母状容器与同时埋入的金银环、钏、钗、错等供养珍宝类一起,依据印度旧制,最外容器为石函,函上刻记明确的缘由,在棺上刻墓志铭的惯例,被认为是沿袭中国古有的埋藏方法。
(一)隋代仁寿舍利塔及其舍利容器
中国佛舍利信仰达到最高潮,是在隋文帝时的仁寿年间(601604)学习印度阿育王造V万四千塔的故事,俗称仁寿舍利塔的多数塔就是由隋文帝建造的。
当时建塔盛行的情景,在《广弘明集》卷十七收录的仁寿元年建青州胜福寺塔、《续高僧传》仁寿二年造本乡弘博寺塔以及仁寿四年造蕲州福田寺塔的记载等文献中可以了解到。近年的发掘成果中,证明此结论的遗物也屡有发现。
1969年,河北省定县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塔基(五号塔基)发现了仁寿三年的金铜函,因屡次重修,内部容器丢失,但展示了佛舍利容器的外层,而寺名并不明确。陕西省耀县塔基于同年出土的舍利容器也推定为仁寿年间所安置。前者发现的北宋时期大量的附属品,虽然展示了数次复兴的情形,却无法详细了解当初的供养情况。后者以琉璃制舍利瓶为核心,用金、金铜制成的箱形容器加以保护,形成三重,若加上石函总共为四重容器,由此可知隋代完全继承了六朝时代的舍利容器形制。两例箱形容器上部均是圆盒形盖,这也是当时箱形容器的特色。
(二)唐代的棺形舍利容器唐代的舍利容器与前代一样,也为子母状套装容器,埋藏于塔基内成为通用方式。核心容器为琉璃制瓶、最外容器为石函外,大概制作的棺形容器是其特征。但供奉的佛舍利像仁寿舍利塔那样,以前建造又荒废的佛塔改造之际,从塔基取出、调换新的容器再次瘗埋。石函上所刻的铭文基本都是明确的事例,如实反映了当时随着佛教隆盛佛塔复兴的情况。
唐代典型的遗物是泾州大云寺(甘肃省泾川县)塔基发现的一套舍利器具由白琉璃瓶、金棺、银棺、金铜函、石函组成的五重容器,石函盖内壁刻有大周国名及泾州大云寺舍利、侧面刻有供奉舍利的由来及延载元年(694)年号、施主姓名。延载元年是武则天建周、敕命在诸州造大云寺五年之后的时间。
同一类型的舍利容器有I960年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发现的长干寺舍利容器,在同一塔基下还瘗藏有禅众寺舍利容器都保存完好。两者根据石函所刻的铭文可知如旧塔所在、移动的年份等,其由来是清楚的。至于长干寺阿育王塔的舍利,根据铭文可确认是唐穆宗长庆四年(824)移人甘露寺,翌年建塔,金棺、银棺、石函组成的舍利容器也是当时新制作的。后者由金棺、银椁(箱形容器)、石函器构成的三重容器,也明确是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安置在甘露寺东塔下的。
棺形容器除此之外,有大阪个人藏的银制容器、波士顿美术馆的石质容器、金铜制二重棺及山东省济阳县出土的京都泉屋注7博古馆收藏的石柜一套,均是着名的舍利容器。虽都失去了核心容器,前者在后壁铸出佛足,后两者都是这种棺形容器,规模宏大,而且在侧面配有守护佛舍利的天部、比丘雕像和线刻像,对研究佛舍利瘗埋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注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图录》朝日新闻社昭和48年。
朱捷元、秦波:《陕西长安和耀县发现的波斯萨珊银币》,《考古》1974年第2期。
甘肃省文物工作所:《甘肃省泾川县出土的唐代舍利石函》,《考古》1966年第3期。
江州省文物工作所镇江分所镇江市博物馆:《江州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发掘记》,(考古)1961年第六期。
《波士顿美术馆东洋美术名品展》,京都国立博物馆昭和47年3月。
《删订泉屋清赏》,泉屋博古馆昭和9年8月。
关于印度和中国的佛舍利庄严63参考资料:
1.高田修:《印度的佛塔及舍利安置法》,《佛教艺术》11昭和26年(髙田修《佛教美术史论考》中央公论美术出版昭和44年所收)。
2.中村元编着:《佛陀的世界》,学习研究社昭和41年。
3.肥塚隆、田枝干宏:《在美术中看释尊的生涯》,平凡社昭和44年。
(王竞香,女,法门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译自奈良博物馆编《关于印度、中国、朝鲜的佛舍利庄严》图录,同朋舍,1983年)略论武则天时期的舍利瘗埋冉万里“舍利者,西域梵语,此云身骨。恐泛滥夫死人之骨,故存梵本之名。舍利有其三种:一是骨舍利,其色白也。二是法舍利,其色黑也。三是肉舍利,其色赤也。菩萨罗汉等亦有三种。若是佛舍利,椎打不碎。若是弟子舍利,椎击便破矣”。佛像未出现之前,人们主要通过对佛足、佛发等的崇拜来表达自己的佛教信仰,舍利也是人们表达崇佛意愿的重要对象之一。在佛教传入我国之初,来华的西域或印度僧人,常利用佛舍利的神奇作为其传播佛教的重要辅助手段,而且这一手段对于佛教传播确实起到了作用。如三国时来华的康僧会通过对孙权展示舍利的神奇,取得孙权的信任,并为之建立了瓦官寺。从发现的舍利塔基地宫来看,舍利瘗埋在中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发生在武则天时期,其典型标志就是舍利容器中首次出现了中国式的棺椁。关于这一点,已有学者进行过探讨本文主要借助于武则天时期舍利瘗埋的一个片断,探讨唐代舍利瘗埋制度的变化。
一、武则天的佛教信仰
唐高宗、武则天都对佛教比较推崇。唐高宗对佛教的推崇表现在为孝经皇帝李弘修建西明寺、支持玄奘修建慈恩寺和慈恩寺塔等方面。武则天本人对于佛教的推崇,为学者们所关注并多有探讨。陈寅恪认为,武则天的母亲出自隋朝宗室,是佛教的忠实信徒,热衷于造像写经,而武则天本人在幼年时代,似乎一度成为沙弥尼,武则天时期的造像写经或许与此有关。更值得注意的是,据《雍录》卷十《感业寺》条云:“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太宗上仙,其年即以安业坊济度尼寺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唐太宗死后,武则天出家感业寺为尼,这是她一生中的又一次与佛教有关的重要经历,这件事情对于她本人有深刻影响,也可能使她对佛教的理解不同于他人,甚至可能促使她认识到佛教是可以为之利用和服务的宗教,对于她以后推崇佛教至关重要。武则天本人对于佛教的推崇表现在很多方面,从下面一些例子中可以得到反映。
在武则天时期,每当有新的佛经翻译出来,她都亲自为其写序,先后写有《方光大庄严经序》、《大周新译大方光广佛华严经序》、《新译大乘入楞伽经序》等,还写有《大福先寺浮图碑》、《三藏圣教序》等。
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摩崖石窟卢舍那佛座束腰部位的左侧,有唐玄宗开元十年(122)补刻的《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佛龛记》,其内容为:“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之所建也,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二菩萨七十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五十尺。粤以咸亨三年壬申之岁四月一日,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奉敕检校僧西京实际寺善道禅师、法海寺主惠陈法师、大使司农寺卿韦机、副使东面监上柱国樊元则、支料匠李君瓒、成仁威、姚师积等,至上元二年乙亥十二月三十日毕功,调露元年自己卯八月十五日,奉敕于大像南置大奉先寺。”大佛的修建过程中武则天以皇后身份“助脂粉钱两万贯”,可知她本人对佛教的信仰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