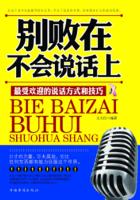整座黎宫,鹅毛大雪飘落,第一片雪落在琉璃瓦上迅速融化,紧接第二片,第三片,越积越多,最后朱红的瓦砾尽被白雪覆盖。
雪落在何处都是银装素裹,美不胜收,唯独落入萧条的冷宫,少了一抹灵动,多了一分萧瑟。
破风的窗户失修已久,冷宫内,衣着朴素的妇人坐于中央,脚下布机不停响动,身上裹着厚厚裘衣,身上衣服缝缝补补数遍,可这却是她能找到的唯一御寒的衣服。
冷风卷着雪花呜咽着从破洞的窗户吹入,妇人依旧不为所动,织着手里的布,她的手已被勒出血痕,没人知道她在这坐了多久,只看出她面容呆滞,一双甚是好看的眸子,如一汪死水泛不起一丝涟漪。
忽然,冷宫大门被人推开,妇人这才抬眼,手脚上的动作仍未停止。
门外宦官扯着尖嗓通报:“皇上驾到!”
妇人罕见地做出表情,却是一声讽笑,她无视来人身份的尊贵,又自顾地低头织起布来。
门外的黎明帝推开身旁撑伞的宦官。
“滚开!朕要自己进去。”。
脚下虚浮,两颊绯红,看来喝了不少酒,黎明帝晃着身子抽出一旁侍卫腰上别的剑,脚下雪被他踩得嘎嘣直响,他就这样跌跌撞撞进了屋子。
‘哗,’一股强风吹入,吹起妇人散落的鬓发,她别过脸,不让冰冷的雪花打在脸上,黎明帝嗤笑一声,转身将门关上。
一身宽大白袍未着外衬,身上披着的裘衣显然也是下人执意为他披上的,如此着急来此,不说妇人也知道为何,可她却不挑明话,或者说她根本不愿与他说话,甚至连看他一眼也不愿意。
“你可知朕为何来此?”
黎明帝用剑指着妇人,脚下不停晃悠。
妇人没有理他。
似有火在眸中燃起,黎明帝挥下手中剑,将眼前织布机一通乱砍,妇人原地不动,任由他发疯,线被搅作一团,架子也被砍的四分五裂。
见妇人依旧一脸的淡然,黎明帝彻底怒了,为什么!为什么到头来只有他一人烧心,一人愤怒。
他将剑扔下,几步上前将妇人衣领揪住,几乎是咬牙切齿。
“情人死了,你难道就一点不难过吗?你不是说你喜欢他吗?还是你从来就没在乎过他。”
‘呸!’妇人朝他脸上啐了一口。
“无耻!”,眼底是冷漠,是嘲弄,是讽刺。
脆亮的巴掌落在妇人脸上,妇人被抽翻在地,白皙脸颊立刻印上五指印,她捂住脸,笑了,笑得那样放肆,那样心酸,泪从眼角滑落。
“黎天明,你就是个混蛋!”
话出,却畅快不已。
黎明帝将剑捡起,抵向她,“放肆!你是什么货色,竟敢侮辱朕。”
高媛站起,将腰板挺直了,她握住剑尖抵上胸口,“杀了我啊!反正被你折磨这么久,我早就不想活了,不过临死之前有件事我得告诉你。”
黎明帝眼中闪过一丝错乱。
高媛哼笑一声:“原来你早就猜想到了,一直不承认,不过是想找借口麻痹自己。”
“闭嘴!”剑朝前抵了一分,高媛身子一顿,低头瞧去,剑尖没进身子,殷红的血顺着剑身滴落。
她苦笑抬头,“可怜文昌痴心一片,终究错付了真心,竟爱慕你这般人渣。”
黎明帝错愕,“你如何...”,他想问她又如何得知,这份情藏得深刻,任谁也不能察觉。
高媛冷笑道:“一人若装满你整个心,那他的一言一行,甚至于一个眼神都会装进你的心里,我是爱他,所以我懂他,相反,我恨你入骨,却也将你那可怜的心看的一清二楚。”
她将剑拔出,绕过身体,手从剑上划过,皮开肉绽,血顺着剑的纹路流向另一端,早已死的心又怎会觉得疼痛。
她走进黎明帝,仰头看他,一字一句便如利针刺入他心里。
“你爱他,可你却不敢承认,因为你是天子,你恨他,恨徐家权利在握,如日中天,因为你是天子,你恨他娶妻生子,恨他原来心里不止有你,所以你抄他满门,这些!只因为你自私自利,我骗你与他情投意合,骗你羽儿是他的孩子,这样直白的骗术,你竟然也相信。”
话到这,她眼梢上翘,讪笑道,“忘了,其实你也不相信,你不过是为了你的自私自利找寻借口。”
“黎天明你知道吗?”
她忽然压低声音,笑容变得诡异,“你害死了唯一对你真心的人,如今他死了,世上再没人在乎你,再没了,在这人间炼狱里,永远只有你一人。”
“闭嘴!”
黎明帝怒红双眼,掐住高媛的脖子将她抵在房柱上,此时的他,面目狰狞如厉鬼,“你不是想死吗?朕成全你!”
手下力道收紧,高媛依旧面容平静,甚至从她脸上寻不到一丝痛苦的表情,她闭上双眼,垂下双臂,只等死亡的到临,良久,脖子上的束缚慢慢减轻,死亡没有如期而至。
黎明帝松了手,‘若是不爱,便死在他手里,那样你爱的人无论如何也会记你一辈子。’
他忽然想起自己曾经对小昌说过的话,可若爱呢?
灵魂似被抽离,黎明帝眼中一片空洞,身子向后退去,剑尖在地上拉出一条血印,他盯着青石板地默然回头,僵硬地走到门边,门开,刺骨的寒风吹散最后的酒意。
高媛望着远去的背影,颓然地蹲在地上,捂住嘴放声大哭。
海棠花下,再无白衣少年。
往生岁月,只剩回忆。
徐将军走后,徐南依便躲了起来,直至临走前朗月都未再见过他,库尔汗王以黎人葬俗将其厚葬,一代枭雄,自此陨灭。
汗王本想让他们将徐将军的遗骨带回中土,奈何徐将军遗训立得死后绝不入黎地,话语如此决绝,可见他心中仇恨有多深。
五公主得了父皇的命令放他们走,红绸入手,取绸者却已不再,自那日后公主再未寻过黎羽,倔强如她,自是放不下那份身段,也低不下眼。
二人回到凉军大帐,分道各走一边,朗月先回京都,黎羽和随从则是先回黎军大帐与部队一道回来。
驾马重回原路,途径沣河镇偶遇一位老友,珠儿姐姐,沣河镇地处大凉与黎国交接处,地理偏远,镇中鱼龙混杂,难怪靖王寻她这么久没有寻到,竟躲到这里清闲。
故友重逢,春儿很是惊讶,却不过惊喜大于惊讶。
二人找了个清净之地,坐下闲聊,其间朗月有意无意提到靖王殿下,她却总是含笑糊弄过去,直到后来她直接开口追问,并将涵洞内靖王说与她的话全部告诉她。
她才松了口,只笑言自己与他绝无可能,叫她带话与他莫要再做无用功,更不要满世界找她,不然她可真的没地方躲了。
朗月问她心中可有靖王,她笑而不答,半晌道;“有时喜欢并不一定非要在一起,二人道不同不相为谋,没有谁愿意为对方舍弃一切,做不到这些,那便将感情珍藏于心中,过各自人生。”
话到这,她再没追问下去,其后又闲聊几分,待天醒时分,又相互道别。
在路上折腾五日,终于回到京都,大雪将整座城覆盖,围城之内,千家万户屋顶上都堆了厚厚一层积雪,个别院中,有人堆起模样各异的雪人,使得厚雪带来的压抑感减轻,更添一份趣味,过冬的麻雀早早屯上一身膘,扭着臃肿的身子在空地上啄遗落的残羹剩饭。
气氛本是如此安详,直到另个消息的出现,打破了这份祥静,事发突然,以至于她听到这一消息时,第一反应竟是狠狠地拧自己一下。
梁成死了!
刚回到家,师兄便板着脸对他说,“梁成死了,是昨夜死的,消息是他派去监视的人告诉他的。”
朗月还处于震惊当中,她问师兄,“他可是亲眼见到?”
师兄答:“我派去的人二十四小时昼夜更替监视,昨夜有人瞧见南絮将浑身是血的梁成从侧门带出,依他口中描述,梁成脑袋耷拉着,胸口有个很大的血口子,身子似已僵软,完全由南絮扛着走。”
朗月又问:“他可跟了上去?”
“自是跟了,可南絮的道行,岂是他们能比得上的,很快就更丢了,不过,”
沈安年话语一转:“今早我回暗门查询了一番,梁成生蛊确实已没了声息。”
朗月还是不相信,毕竟这种事还是能造假的。
沈安年却道:“我一直派人守着生蛊的动静,让他每跳一辰便向我汇报情况,如今五个时辰已过,生蛊依旧毫无动静。”
此时朗月又注意到另个问题,自她进屋便一直未见清风和香兰的身影。“清风和香兰呢?”
沈安年顿了顿道:“他们去了王府。”
“王府?那里不是被封了吗?”
“黎羽回来了,并且皇上恢复了他的爵位。”
朗月惊喜,“真的!”
沈安年则是面色凝重,将朗月拽到石椅上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