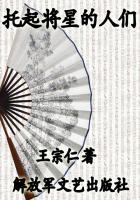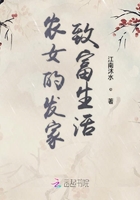周昙《咏史诗》的传世,不似胡曾《咏史诗》的幸运,可谓命运多舛,不绝如缕。今传有宋刻单行本,已属海内孤本;有丛书本,收入明人编辑的《唐百家诗》,亦仅嘉靖年间一刻;有丛编本,即编入《唐音统签》、《唐诗》稿本及《全唐诗》者,幸而有三;还有两个删节本,见《唐诗类苑》卷六八、《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卷四一七史学部艺文二。案《诗源辩体》卷三一《 晚唐》云:“晚唐七言绝,周昙有《咏史》一百四十六首”。可知明时已有周昙《咏史诗》删节本,惟不知是指单行本,抑或《唐诗类苑》本?清人编《古今图书集成》收录周昙《咏史诗》恰为一百四十六首,不详是否由此而从出?这几个本子的题名、卷秩、编次、分门等,详参下节所列之表。
在以上数本当中,以自吟之诗、自注之文、自评之语集于一本而刻印的宋本最为重要,其他则为删落注评而单存诗作的白文本。宋本于一九八〇年由天津古籍书店影印出版,书名题为《周昙咏史诗》。尽管这次影印,正如周叔先生在《跋》文中所说:“使人间孤本,化身千万”,但迄未得到学界的关注与利用。如有论者谓周昙《咏史诗》的“单行本已佚”。(《论晚唐的咏史组诗》)还有论者则谓:“胡、周《咏史诗》传本虽有注或讲解,却并不是原作者所撰说白”。(《传统诗体的文化透析》)案胡诗如此,而周诗乃自注。又《增订注释全唐诗》卷七二二周昙《鲁仲连》:“昔迸烧牛发战机,夜奔惊火走燕师。今来跃马怀骄,十万如无一撮时。”注曰:“‘今来’二句:田单攻聊城,岁余不下,士卒多死。鲁仲连射书城中,燕将见书自杀,遂克聊城。”案此注显然不合诗意。而据宋本自注:“田单将攻狄,往见鲁仲连。仲连曰:‘将军攻狄,必不能下。’单曰:‘我以(三)[五]里之城,(五)[七]里之郭,败亡余卒,破万乘之燕,复齐邦。今以十万精兵,攻狄不下也?’遂上车不辞而去。攻狄三月,不克。惧而问仲连,仲连曰:‘将军之困于即墨也,坐则织蒉,立则(杖)[杖](捶)[插],为士卒唱,人皆欲战,此所以破燕也。今将军东有(剧)[夜]邑之俸,西有淄上之(娱)[虞],金玉满堂,绮罗满室,有生之乐,无死之心,以此不胜也。’[单曰]:‘单有心,先生志之矣。’单厉气(修)[循]城,立于矢石之所,援鼓之,狄人乃下。”(案底本文字讹误颇多,此据《战国策》卷一三《齐策六》略作校订。)又同书同卷《武公》:“猛兽来兵只为文,岂宜凉德拟图尊。君看豹彩蒙糜质,人取无难必不存。”注曰:“武公:春秋战国时,诸侯国前后有九位君主号武公,此未详孰是。”据宋本自注:“顷襄王欲图周,周(被)[赧]王使武公谓楚相昭子曰:‘夫杀其主,(距二十)[臣世]君,则大国不亲,以众胁寡,则小国不附。大国不亲,小国不附,不可以致名实。今周之地不过百里,名为天下共(之)[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国,得其众不足以(致)[劲]兵。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发号用兵,以周为意者,见祭器在焉。今若以器传之于楚,臣恐天下以器仇楚。臣请譬之。(人)[夫]虎(右)[由][肉]不堪食而爪牙甚利,人(由)[犹]攻之。若使泽间之麋(象)[蒙]虎之皮,人攻必甚矣。’于是楚计不行。”(案底本文字讹误颇多,此据《史记》卷四〇《楚世家》略作校订。)知“武公”为东周赧王之臣,并非不明所指。此均为时贤不曾参考影印宋本之明证。故以此影印宋本为据,结合有关文献,对宋本的刊刻板式、时地及收藏、流传等情况作一介绍。
宋刻本半叶十二行,正文大字单行,行二十字,注文小字双行,行三十字,行有界栏,四周双栏,外粗内细。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板心上鱼尾的下方各题“周诗上”、“周诗中”、“周诗下”,下鱼尾的下方各记叶数。上卷首行顶格题“经进周昙咏史诗卷之上”,“经”与“进”之间空一格。中卷、下卷亦然,仅换“中”、“下”字样。又各卷的末叶亦如是题。次行低七字题“守国子直讲臣周昙撰进”,且“周昙”二字之间及上下均空一格,中卷、下卷亦然。第三行顶格为黑盖子系以墨圈,下题“唐虞门”,又低六格为黑盖子系以墨圈,下题“吟叙”。全书所有诗题均加有黑盖子系以墨圈,且后一首诗的题目均在前一首诗的注文之下。
全书收诗一百九十五首,均为七言绝句,除过前面两首叙诗,皆以历史人物为题,始于《唐尧》,终于《贺若弼》。每诗或单吟一人,或合吟二人、三人。同一人之第二首题《再吟》,第三首题《又吟》。分十门,为唐虞、三代、春秋战国、秦、前汉、后汉、三国、晋、六朝、隋。诗题之下用几个字简说大意,诗后注出史事,注后为评论,多以“臣昙曰”标示。
论者谓此本为“宋福建刻本”,甚是。兹以四点证之。一、宋代刻书有三大中心,各具风格特点。在文字校勘上,最精审者为浙本,其次为川本,粗劣者即建本。谛审此本文字,讹误衍脱,屡见不鲜。如《夷齐》诗:“让国由哀义亦乖”,案“哀”显然为“衷”之形讹。又如《晏婴》诗:“车何必用奔驰”,案“”显然为“驱”之形讹。再如《百里奚》诗:“只击用之能不能”,案“击”显然为“”之形讹。复如《高祖》诗:“安和强啜不含悲”,案“和”显然为“知”之形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注中文字讹误致有不可句读者,以至清人彭元瑞叹曰:“多不可通,奈何奈何”。二、建本书多为书贾所刻,喜用俗体字,这个现象在此本中至为明显:“无”作“无”,“礼”作“礼”,“虽”作“虽”,“与”作“与”,“万”作“万”,“尽”作“尽”,如此等等,俯拾皆是。三、在避宋讳方面,以浙本为最严,川本次之,而建本又次之。细观此本,避讳不甚严。“弘”、“殷”、“敬”等不缺末笔,“”或缺或不缺,“匡”缺末笔,“桓”或缺或不缺,“”不缺末笔,“慎”缺末笔。虽然讳及嫌名“贞”、“侦”、“真”、“徵”等,也是或缺或不缺。四、在刻书字体上,浙本多为欧体,川本多为柳体,建本多为颜体,而此本正是颜体。合此四者综观,影印宋本之底本当为建阳所刻。不过,此本在板刻上却颇精致,疏朗悦目,不啻为建本书之佼佼者,即使与其他宋刻佳本较之,亦堪称上品。
论者又谓此本为“南宋刊本”,甚是。案此本避宋讳不甚严,前已论及。但是,书中凡遇“慎”字即缺末笔,且不为光宗以下诸帝避讳,可见此本当刻于南宋孝宗时。
此宋刻三卷本在宋元时的流传情况不详。前引明高儒《百川书志》卷一四集志三唐诗类著录《经进周昙咏史诗》之解题颇详,然而未说明是否有注评。其他各家之著录,更是语焉不详。故此本在明代流传的情况亦不详。
至清代,收藏及流传情况则较明朗。就现在所见书目文献记载,最先收藏宋刻本周昙《咏史诗》的是清初著名藏书家季振宜。观今影印本,上卷、中卷、下卷的首叶首行下方各钤一枚“季振宜藏书”印章,且下卷未叶有“泰兴季振宜沧苇氏珍藏”墨书一行,可见据以影印之底本即为季振宜所藏宋本。
再观全书首页和尾页的空白纸上各钤三枚同文印章,由上至下为:“五福五代堂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下卷末叶无字处钤有“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二枚印章。至为有趣者,上卷首叶书眉紧贴边栏处有二枚各为半方的印章,印文仅存“天继”、“乾御之”,而全幅印文应是“天禄继鉴”、“乾隆御览之宝”。这大概是因印章较大,怕加盖后,印文下半部会将书上的文字掩盖,于是用纸遮住下半部,不使印文全部钤上。看来,这位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还颇惜古书。而据上引《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六《宋版集部》著录:“《经进周昙咏史诗》……册尾墨书‘泰兴季振宜沧苇氏珍藏’。‘季振宜藏书’,朱文,卷上、卷中、卷下。‘唐古夫氏’,白文,卷上。”与今影印宋本同,可见宋本于乾隆时即已入存内府,成为秘籍,难得窥豹。案乾隆皇帝于嘉庆元年至四年正月为“太上皇帝”,而《后编》撰成于嘉庆三年,则此本进入清内府是在嘉庆三年之前。又案《四库全书》编成于乾隆四十七年,而《四库总目》既未著录此书,亦未存目,则此本之入内府,似又在乾隆四十七年之后。
一九三三年编撰的《故宫善本书目》不著录此宋本,可知此前已流出宫外了。又据傅增湘先生的记述,早在一九一七年即散出内府,流入厂肆。其云:“《青山集》、《周昙咏史诗》、《纂图互注扬子法言》、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博物志》、《山谷老人刀笔》、《佩》、《国语解》八书久闻流出厂市,探询半月,苦不得耗。嗣晤蒋孟及周叔,两君皆得寓目。继而闻经手者为宝华堂张秋山,因往访之,密不肯示。继而孟还价不谐而去。闻之怅往而已。昨夜亥刻,宝瑞臣前辈以电见告,谓八书皆在渠处,遣急足往取,夜分乃至。《青山集》古雅绝伦,恐为海内孤本,《咏史诗》及《昌黎外集》、《扬子法言》均属宋刊,余皆明本,而《佩》乃以张氏泽存堂本冒充,独为可诧。因连夜将《周昙咏史诗》校勘一遍,余皆略记行格印记如右,翌日亲赍还之。”案所记行格印章均与今影印本同。《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二集部“经进周昙咏史诗三卷”条。惟“卷之上”误为“卷之一”,又第三行顶格有黑盖子,下题“唐虞门”,而误为“三行低二格题‘唐虞门’”。又释“唐古夫氏”为“吉夫氏”,略异。另据周叔先生回忆说:“《经进周昙咏史诗》三卷(案此下略引《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语)。五十年前,北京琉璃厂书友曾携此书及宋本《寒山子诗》来天津求售。当时为财力所限,只收《寒山子诗》,而此书交臂失之。久之消息杳然,时时形之梦寐。解放后,从友人处得悉此书现存天津某家。此书除《天禄琳琅》(案指《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外,明清两朝未见传本。此书毁,则是书绝迹于天壤矣。前年余阅书于天津古籍书店,张振铎同志出示此书,为之惊喜过望。五十年前,初见此书光景如在目前。询之从何处得来,则云收于废纸堆中。死者复生,断者复续。冥冥中若有神物护持。偶然之事,良有不可思议者。今者古籍书店拟付之影印,使人间孤本,化身千万,甚盛事也。”时为一九八〇年。影印宋本附《跋》文。可知此本先是于民国初年在书商手里转售,至三十年代由北京流入天津而为私人收藏,然后就下落不明,到八十年代前后却从废纸堆中捡回而重见天日,真可谓“不可思议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