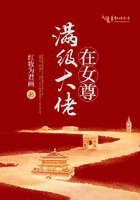你在找什么呢?那个女人躺在床上,看着锦一在房间里翻开所有的箱子和抽屉,问他。
锦一说,我在找你。
那个女人哈哈地笑,然后不理会锦一了,继续看手上的书。
那是一本《三玄》,锦一很喜欢看,三玄,分别是《易经》,《南华经》和《道德经》,全是高深莫测的东西。锦一买的是一本白话文版的,有时候锦一觉得,这几本书是诗,他画不出东西的时候,看一下《易经》的部分,就会感觉身体里有了欲望,准确的说,不是欲望,是灵感,是有了热量,或者磁场。
他甚至还想过画一组由六十四幅小画共同组成的大画呢,他是这样想的,每一幅小画都独立可以成为优美的个体,但如果把这六十四幅画按照着天干地支的方位摆放好,又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大画。
他只是这样设想而已,他找不到第一幅画的内容,他没有起点。
锦一看着所有被打开的抽屉和柜子的门,发呆。他没有找到他给邵娅画的画。锦一很纳闷,他记得很清楚,画了两幅,第一幅画坏了,只有邵娅的身子,后面的墙没有画出来,只有一只表,那表上的时间是锦一和邵娅在一起做爱的时间。另一幅完整的,被邵娅拿走了。
锦一陷入记忆的纠缠里,他经常害怕自己的记忆乱了,他需要自己的记忆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或者重要程度,排列整齐地存放在一个文件夹里,等着自己随时检阅。
那个女人突然问,你有黄色的体恤衫吗。
锦一回过头看她一眼,觉得有些莫名,但还是摇摇头。
那个女人说,我这就出去给你买。
说完,女人穿好外套,然后转身出门了。只是,她刚出门,就回来了,她又问锦一,你喜欢喝黑豆浆吗?锦一点点头,朝她笑了一下。
女人消失了,一上午也没有回来。
锦一觉得,她一定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但是,昨天自己干什么了,昨天晚上呢,自己是如何和她在一起的呢。我录的节目呢,音乐盒带找齐了吗。
锦一突然觉得自己的记忆有一段被删除了。
他不记得昨天了,他只记得好多天以前,他和卡车和苗瑜琍和潘玉凉等一大帮人在城市的街道上唱歌。
他只记得这些。
锦一觉得问题有些严重,他觉得自己真的丢了昨天。
他开车到办公室,问正嬉笑的同事们昨天他做了什么。配音组办公室只有蓝若玉在,她在接电话,锦一静静地听她的说话内容:嗯,嗯,可能是吧。是的,好,我,我知道,我,我知道,我明天,不知道,我知道了,是吗,不会吧,我不信,鬼,你是,你是,就是,好吧,嗯,嗯,好了好了,办公室里有人,嗯,不重复了,拜。
锦一差不多能猜测到对方那个人在说什么,他甚至想起自己和其他女人通电话的情形,他会说:在办公室里吗?今天天气好不好?我这一会儿忽然很想你,一定是你先想我了对不对?我猜你今天穿了那件绿裙子对不对?下午帮我买一贴药膏好不好?你的牙齿还痛不痛,要吃牙痛安。那个药片在盒子里。嗯,对了,你什么时候来给我送温度适合的乳房……
蓝若玉指着锦一桌子上的一本杂志说,拆开看了,没有秘密。是有一次在卡车画廊里遇到的一个女孩子寄给他的。
锦一看到了那本杂志。是本地的一份DM杂志。杂志的封面上是一个穿着毛绒绒衣服的女孩,手上戴着广告品牌的腕表,笑容是电脑鼠标处理过的,一点暧昧也没有,那眼睛里的黑像极了他自己画画时没有化开的一点墨汁。
锦一长时间地盯着那女孩的眼睛看,仿佛要从她的眼睛里看到这个世界的微型景观,结果,一无所获。
锦一摇摇头。看了看那个杂志封面上的目录:
蝙蝠并不自己搭窝。
越南湄公河和奥地利萨尔斯堡和爱情。
三个诗人,分别叫做小明小青和小平。
封面标题很趣味,像极了蓝若玉的那条裙子,竖条条的装饰线,到了裙子的下面变化成了柳树的枝条,显得妩媚极了。
他问蓝若玉,昨天台里有什么事情。
蓝若玉一边用纸巾擦手,一边用鼻音说:昨天下午不是政治学习吗,我们大家都各自散了。全台只有新闻部在那里搞形式主义。
锦一把目光放在蓝若玉的裙子上,很久,蓝若玉的裙子没有了,蓝若玉出去约会了。
锦一给卡车打电话,问他正在做什么?
卡车说,正在和一个推销药的女孩喝咖啡。卡车忽然咳嗽了一声,声音变小了一些,说,这个女孩的眼睛很好看,你知道吗,这种女孩子做爱的时候眼睛一定是半睁半闭的,特别好看,我在努力发展中。
锦一嗯嗯地挂断了电话。
他很着急自己找不到记忆里的任何线索,那个女人的模样非常陌生,她怎么可能是邵娅呢。
打扫卫生的清洁工突然到锦一的办公室里擦玻璃,那是一个中年女人,她干活很卖力。她穿着一件蓝色的工装,还戴着物业公司的帽子,她的牙齿有些灰暗,像这个城市的天空。
前几天看电影,锦一看到电影中的女主角的父亲对男主角说,你的牙齿很好,所以,我断定你有好的前途。女主角的父亲是个牙医,所以,他有这样的人生视点。
那么,如果女主角的父亲是一个清洁工呢。
锦一陷入了另外的思考陷阱中,只是一会儿,他就感觉到了自己的无聊。
他把车子开进常去的咖啡厅里,竟然看到卡车。
他仍然在那里发表他的观点,锦一坐在卡车的身后,听他在一个陌生女人面前高谈阔论。他听到卡车对夜晚发表看法:黑夜是一个视觉游戏。我们的祖先要是在白天睡觉,让太阳晒晒屁股,而在晚上抹黑干活,那么,现在的世界一定是另外一个样子。
那个女人安静地看着她,笑容像自来水里的水一样,大股大股的流出来。从侧面看,这个女人有些像陈小艺。
锦一这样看着她们。锦一还看着窗外停车场里的那个保安在指挥车子,手势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像做广播体操一样。如果把停车场的车辆和其他人都一一从画面里删除,可以看到他的一天在不停地做向左向右的广播体操。
锦一这样想的时候,突然看到那个那个保安蹲在地上,把鞋子脱掉了,像是要磕掉鞋里的沙子。
卡车的声音没有停:在黑夜里,把灯关掉,我发现,捂上眼睛和睁开眼睛是一样的。但是,睁开眼睛,就可以慢慢地把黑暗中的事物分成不同的层次,你试过没有,我试过好多次呢,在房间里,我看过一个女人的身体是如何一点点进入视线的,最先进入我的视线里的是她的胸部,是浅黑色的。还有她的呼吸,是她呼吸时起伏的胸部,你小朵的波浪一样,稍有些复杂,但也是一种黑。还有窗帘,是花纹一样复杂的黑。以及没有来得关掉的电脑音箱开关的指示灯,那是夹杂着执着的白颜色的黑。当然,还有纯粹的黑,那是我趴在了女人的身上。
锦一在一旁插话说:伙计,你大概是想说,黑暗是时间和我们玩的一种突发性的游戏。
卡车转过头,说,你这家伙,怎么鬼崇鬼崇的。偷听我和我的网友聊天。这要是在网上,你这就属于盗窃我的QQ号码偷看我的聊天纪录知道吗,这是不道德的。
锦一就哈哈地笑,他看到了卡车的对面端坐的女孩子,鼻子很好看,眼睛眯着,很细小。
是鲁亭亭。
鲁亭亭。锦一站了起来,叫出了名字。
那个女人也认出了锦一,说,你还好吧。
当年在学校里有皮肤病的鲁亭亭,没想到变成了医药销售代理商。
锦一心里想,皮肤病一定是治好了。
锦一说,你们刚才说得这么热烈,说什么呢?
卡车说,说小时候的事情呢。
锦一说,小时候的事情,我最拿手了,我小时候练习过尿尿,白天在院子里的一片空地上画一个小圈圈,然后在夜里起床尿尿,要尿到那个圈子里。练了好多天,终于在夜里看到了我划好的那个圈圈,感到无比的骄傲。
卡车说,你说的是哪跟哪儿啊。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黑颜色的层次。我是在说,对于黑颜色,小时候判断得很清楚,分成很多种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统统地叫做黑色。
锦一问鲁亭亭,怎么和他认识了,你现在做医药推销吗,你过得如何?
锦一的问题是三个,这让鲁亭亭挑选了好一会儿,她一直笑着看着锦一,停顿了很久,才说,我也是无意中做医药推销的,这一行来钱快一些,但意思不大。
锦一在大学里是喜欢鲁亭亭的,但是那些具体的细节却已经想不起,譬如有没有在上课的时候给她写过情书啊,譬如有没有在一起看电影的时候把手伸向她的身体啊,等等,锦一均一片空白,他只是记住了鲁亭亭的样子。
锦一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脑子里做怪,就连昨天做过什么他都记不清了。
前天他还很清晰,他在前天的时候去洗车,然后跑到一家湘菜馆吃剁椒鱼头,还给新闻中心的一则给狗寻保姆的新闻做了配音。下午的时候给邻居家的孩子辅导绘画,还帮助把小区里一个吃安眠药自杀的女孩送到了中医院里。
可是偏偏昨天的记忆一片模糊,锦一发呆的样子被鲁亭亭看到眼里,她笑着说,你还是老样子。没有变化。
锦一一下子被这句话击中,他像是在一个黑暗的洞穴里突然看到灯火一样,他看到自己在记忆的邃道里来回奔跑,他看到自己的影子很快地消失,他看到一个女孩子在昨天上午的公园里讲故事。
他甚至看到有一片叶子,慢悠悠地飘下来。
锦一愣在了那里,心里的那一些记忆有些轻飘,若有若现。
卡车去卫生间回来后,接电话,哈哈地笑,露出得意的表情。
鲁亭亭说,我结婚了。
锦一看着她的胸部,那是一个结婚的女人应该有的胸部。锦一和其他所有男人一样,他喜欢看女人的胸部来判断女人的心事、年龄、爱好,包括是否结婚。
鲁亭亭说,他有皮肤病。
锦一笑了,没有发出声音来。却是很会心地笑。他看着鲁亭亭,觉得,男人和女人除了爱情和暧昧的关系,真的有一种淡淡的友谊。这种感觉来自于爱过之后的疏远。
卡车把电话挂断了,说,要不要吃这里的牛排。
锦一说,你们吃吧,我还要找一些东西。
锦一说完就起身往门外跑,他忘记和鲁亭亭说再见了。
很早以前也是一样的,他抓起衣服就往教室外跑,然后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直到大学毕业各奔东西。
卡车对鲁亭亭说,这家伙就是这样子,有时候很无耻,有时候会害羞。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歪着头对鲁亭亭说,你们早就认识是吧。
鲁亭亭说,大学同学,同班的。
卡车说,是这样啊。他又一次说起黑颜色来,他说,锦一是我们画廊里著名的画家了,你大概不知道,不仅你不知道,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其实,他的画之所以能卖出高价,是因为他舍得用墨水,浓得也好,淡得也好,他泼墨很舍得,是很放肆的舍得。他在画里面隐藏了很多东西,包括爱。很多人都从他的画里看到了另外的意思。
鲁亭亭说,你说他的画像感冒药一样,还能帮助睡眠。
卡车说,是的,像牛排一样,还能帮助锻炼牙齿。
两个人就笑。
夜来了,黑颜色的层次渐渐均匀,整个城市成了锦一的画,那画,叫做《被遮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