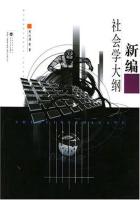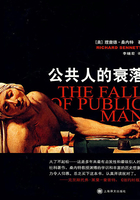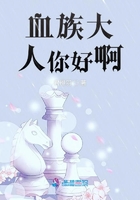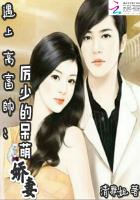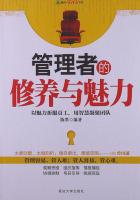一
有人说:“七老八十的人还在那里爬格子爬个不停。”言下之意,不问可知。其实,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在想;去年我还写过这样一首小诗:
盆里的丝瓜
爬满了整个窗台,
头还在向着天。
爬吧,爬吧,
我们都有这个缺点。
就人的本性而言,积极向上本无可厚非,但也要视年龄而定。且看树木,一到秋天就把叶子一片片卸下来,紧缩开支,准备过冬;而不是一味地疯长,好像有使不完的劲似的。人老了也应该检束自己,把世事看得淡一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借此驱散内心的空虚与寂寞。宋词云:“乃翁依旧管些儿:管竹,管山,管水。”城里人无山水竹木可管,所以就借种花、养鱼等等作为消遣。我因为不善于养鱼种花,所以就挑了“爬格子”这门行当,而不是说我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赋。
二
远在“文革”后期,我因为闲着无聊,就摘抄书画家的轶事,同时还记录了不少越中方言,如今还保存着一个小册子,题曰《越语备检》,署名思衡,就是眼下这本《越中乡音漫录》的前身。最初我用“随语记录”法,就是从人们的嘴上(也包括自己的)把方言记录下来。这个方法的好处是“新鲜”,有如黄瓜刚从藤上摘下来;缺点是耗时费力太多,就像“守株待兔”,要是兔子不出现可怎么办?所以我就改用“附舟还乡”法,就是从鲁迅、周作人等越人的著作中找出例子来。这有三个好处,一是这些人的著作早已存在,所以找起来就比较有把握;二是他们已做过一番筛选的工作;三是对某些难懂的方言往往有所诠释。这些越人之中,特别是鲁迅和周作人,他俩不仅是写文章的能手,也是运用方言的积极分子。我将他俩的著作(不包括翻译作品)重新看了一遍,发现那里的方言竟比我原先想象的还要多。
当然,越中方言浩如烟海,单靠“二周”等几个越人的著作是不够的,所以我就又把注意力转而致他,譬如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和张南庄的《何典》就是我首先想到的。古代的吴越是两个国家,虽然战争不断,但毕竟是山水相连的邻邦,所以在民俗语言诸方面都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同时,这两部小说不仅是吴语文学中的佼佼者,还大量运用方言,其中有好多就是越人也一直在使用的。《海上花列传》好版本难找,我这一本还是该书的整理者典耀先生特地从北京寄来送我的,其中多含勉励之意。
三
有一次,我随一位师长去看望一位绍兴籍的老作家,我对他说起绍兴的方言。他说:“别看这区区的方言,要解释它还真不是一桩容易事。”他突然问我:“绍兴人说东西差叫‘息’,你知道这个字应该如何写?”我说“‘皮革’的‘革’字旁加一个‘以及’的‘及’字,据《西湖游览志余》说是‘讳低物为靸’,读若‘歇’”。但是他却说:“据鲁迅的朋友陶望潮说,这是有人把‘好歹’的‘歹’字错认为‘一朝一夕’的‘夕’字所致,开始大家都当作笑话流传,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竟成了一句方言了。”他还说,方言的成分很复杂,有的是方言,也就是“土语”,有的却是“外来语”,读音就不同。譬如“跑来跑去”说的是土音,独有“跑马灯”的“跑”字读若“抛”,据说这是由绍兴在北京做官的人带回来的。关于方言的读音“有例外”,我还曾见周作人在一篇《方言与官音》的文章中说过:“大概学方言难处不在发音别扭,读音有例外最是麻烦事,例如‘大’字读‘陀’(去声),用于读书时的官音则仍为‘大’,地名如‘大路大坊口’读土音,‘大云桥大善寺’却又用官音。‘水’字土音读若“史”,地名大抵一律如此,但人名如鲁迅小说中的运土本名运水,又仍读作绥(上声)而不叫作‘运史’。又如‘猪’土音读‘支’,‘桃子’读‘桃执’,‘人’读‘银’,但‘鸡子、鸭子、杏仁、朱红柿’,都还是照普通读法,不曾改变。”
四
方言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一词语(包括语音、语法),二名物,三风俗(包括各种传说),都是最贴近老百姓生活的东西。我们习惯把故乡的一条干流叫作“母亲河”,因为它不仅哺育我们长大,还是我们“游于斯,钓于斯”的好伙伴。方言不及河流具体,却也与我们有着“知痛着肉”的关系,所以也不妨称之为“母亲语”。一个人别的都可能忘记,包括后学的多种语言,只有“母亲语”是不会忘记的;不仅不会忘记,越到老年印象就越深刻。朱舜水是明末遗民,明亡后起兵反清,后来失败,就流寓日本,能操倭语,但一有机会就与身边的人说余姚话,讲浙东的民间故事,也不管别人听得懂听不懂。
从传情达意的功能来说,方言比不上大众语,即普通话。但就文学的创作而言,它也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一个文学家不管他的活动空间有多大,归根到底还是属于某一地区的。譬如鲁迅像一颗流星似的划过大半个中国,但是说到底还是绍兴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会稽山下之平民”。绍兴话是他最熟悉的语言,绍兴事是他最爱听的故事。他的小说散文无人说是乡土文学,但是却包含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绍兴的事不必说,绍兴的话也随处可见。他在《写在〈坟〉后面》中说:“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这博采口语之中,也就包括方言在内。周作人的看法也一样,他在《歌谣与方言调查》中说:“我觉得现在中国语体文的缺点在于语汇之太贫弱,而文法之不密还在其次,这个救济的方法当然有采用古文及外来语这两件事,但采用方言也是同样重要的事情。”
五
上面我说了许多关于越中方言的话,仿佛要对它作一番研究似的,其实不然;我写这本小书,主要是受了“思乡的蛊惑”。所谓“野人怀土,小草恋山”,人是没有不爱他的故乡的。但是爱也有一定的内容,大概环境、人物、饮食、语言就是载体。人到老年,故乡也不可能不变,尽管高楼林立,风景如画,“但要找我的故乡只在梦里”。人物更不足恃,所谓物是人非,几十年间不仅老一辈都已作古,就是当年“排排坐,吃果果”的小伙伴也已经为数不多。饮食的变化也许少一点,但是许多食品也都在优胜劣败中消失,即使存在,也往往没福消受,不是齿牙零落,就是胃纳欠佳,孔子“三臭而不作”,实在也只能如此。只有语言好像变化不大,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年过八旬,村里的小孩子自然不会认识他,他就拿出一张“金名片”来:一口地道的萧山话。我没有朱、贺两位前辈的遭遇,但与故乡也总是处在若即若离中,从前住在富春江边,现在定居杭州城里,虽然与故乡都只有一江之隔,但是醒里梦里想的却还是以故乡的事情为多。鲁迅曾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说:“虽于所见事状,时不惬意,然兴会最佳者,乃在将到未到时也。”我现在一边记录着乡音,一边就像是走在回乡的路上:
蓝天里白云绵绵,
白墙黑瓦——
映衬出青山一片。
流水绕过村庄,
好地方还在那边。
2014年5月5日写于杭州古砖街巷寓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