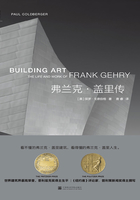第十六章 (1)
割掉知情人的舌头
割舌
云奇是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来救他的师弟如悟的。他俩和朱元璋是一同托钵游食四方的师兄弟,如今朱元璋要处死如悟,云奇好歹央求马秀英,算是求下情来了,如悟可以活命了,但云奇却高兴不起来。
朱元璋说:“可恶的如悟口无遮拦,舌头惹祸,谁能保住他今后不会背地胡说八道?”他答应网开一面,但却是有条件的,“他不是管不住他的舌头吗?那就把舌头割了去。”
宫里派人来割如悟舌头这天,云奇早早来到刑部大牢前等着,几个太监见了云奇,一齐向他施礼。
云奇看着他们手上的刀子,皱眉头问:“治红伤的药备了吗?”
一个小太监说:“回大人,备了。”
云奇挥了挥手,让他们进去了,自己仍在门外走来走去,他不忍心看那血淋淋的场面。一阵叮叮当当开锁开门声把蜷缩在草堆上睡觉的如悟惊醒过来,他打了个哈欠,问:“又是馊饭吗?我不吃!”
牢头阴阳怪气地说:“你等着吧,有肉吃呢,等着咬自己舌头吧。”几个跟在后面的小太监不怀好意地笑,如悟显然什么也没听出来。几个太监不由分说扑上去,七手八脚把如悟按倒在地,用绳子捆他。如悟挣扎着大嚷大叫:“干什么?你们敢杀我?我要见云奇!”
这时云奇从外面跑了进来,说了声:“慢。”
几个太监只好松开手,站在一边。
如悟从地上爬起来,眼里充满恐惧地问:“云奇,这是怎么回事?皇上要杀我吗?”
云奇默默地摇摇头,叹口气,说:“不,不杀你,你能活命了。”他告诉如悟,他求了皇后,皇后在皇上面前磨破了嘴,才算求下情来。
如悟不满地目视几个动手绑他的小太监,问:“那他们几个不男不女的混蛋绑我干什么?”
云奇好难张口,为难了好一会儿,他说:“师弟,是这么回事,皇上不是怕你嘴上没把门的吗?你呀,惹祸都惹在舌头上了,所以……”
如悟看见了小太监手里闪着寒光的刀子,明白了,吓得向后躲:“不,不!是不是想把我的舌头割掉?那我怎么说话!”
云奇叹口气,道:“这是没办法的事。没了舌头总比没了脑袋要幸运。你别怪师哥,师哥就这么大本事了。”他不敢再看如悟的眼睛,低下头往铁栅栏外走。这等于是无声的命令,几个小太监又一次扑上去捆绑如悟,如悟便杀猪一样地号叫,但寡不敌众,很快被制服,牢牢地绑在了铁栅栏上。如悟撕裂人心地喊了一声:“师兄!云奇——”
云奇不忍,又回过头来,心如刀绞,眼中有泪。
“先别让他们割。”如悟哀求着,“让我再说几句,成了哑巴,话就只能憋在肚子里了。”
云奇心酸得不行,用眼神制止了急于要下手的小太监们,走到如悟跟前说:“师弟,有话说吧,你说上一个时辰我也等你。再不说,就永远也说不成了。”说到此处,他不禁呜咽出声了。这一说,如悟反而安静了,他沉默了好一会儿,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云奇说:“说呀,你怎么又不说了?”
“多说一句两句,又有什么用,不说了!”
“你别难过。我向皇上请准了,过几天送你回濠州皇觉寺去,如今修得可好了,回那里是根本,不愁吃不愁穿的,别再惹是生非了,人怎么还不是过一辈子呢!”如悟近乎绝望地说:“行了,动手吧。”
“你不是要说话吗?”云奇问。
他摇摇头道:“不说了。”
云奇闭了一下眼睛,几个小太监便走上去,其中一个说:“别让我们费事,把舌头伸出来,我给你多留一截,说不定你还是个半语子。”
如悟顺从地伸出了舌头,当小太监伸手扯住舌头要动刀时,他又突然缩了回去,吼叫起来:“朱元璋,你这个贼和尚!我早晚宰了你!你割我舌头,我割你秃头!”所有的人都吓坏了,上去踢他、打他。由于他反抗,刀子扎偏了,把腮帮子都扎漏了,鲜血淋漓。云奇说:“他快疯了,说的都是疯话,你们都当没听见。”说罢快步走了出去。
云奇快走到走廊尽头了,忽然惨绝人寰的惨叫声传了过来,云奇打了个哆嗦,靠在石墙上,无力地闭上了眼睛。牢中又陷入了死寂。
几个割完舌头的小太监鱼贯而来,有一个用一根麻绳拴着割下的少半个舌头,血淋淋的。
两天以后,如悟被放了出来,云奇在狱门口等着他,还备了一匹马,马鞍上挂的皮囊里装了些吃的、用的,云奇告诉他,这都是马秀英娘娘为他准备的。如悟绝处逢生,好不感动。云奇送如悟出了城门,把马缰绳递到他手中,说:“若不是皇后慈悲为怀,你小命早没了。”
如悟点点头,双目含泪,向着皇城的方向鞠了一躬。
装疯卖傻保性命
廖永忠得“怪病”的消息在南京城里早已不胫而走,有奇怪的,有嗟叹的,有可惜的,有好多人目睹了廖永忠的傻相。
但在深宅大院里,他就是一个正常的人了。
这天午后,管家慌慌张张地进来说:“皇上驾到!”
这消息来得好不突兀!廖永忠吓了一跳,冷静下来,他意识到凶多吉少,装疯前,自己一直请求陛见皇上,朱元璋始终不给他机会,似乎有意冷漠他。那今天为什么一反常态,反倒屈尊移驾上门?
除了“刺探虚实”,不会有别的解释,廖永忠吓出了一身冷汗。
当朱元璋走进廖永忠的卧房,还没等迈门槛,便皱眉了,一股臭烘烘的味道,令他喘气都不匀了。
廖永忠正在吃饭,朱元璋进来时,他正把手伸进粥盆里抓粥吃,也不怕烫,手烫得红了,稀饭糊了满脸,下人忙去制止:“我用勺喂老爷吧,看手都烫坏了。”
朱元璋站在门口,显得很忧伤地说:“几天不见,病到这地步了吗?”廖永忠不认识似地望着朱元璋傻笑,不下跪也不说话,只顾去抓粥吃。朱元璋抓过廖永忠的手看看,烫起了水泡。
朱元璋坐在廖永忠对面,手指着自己的鼻子问:“我是谁?”
廖永忠嘻嘻地笑着说:“认识,你不是玉皇大帝吗?我给你的金童玉女梳过头。”
朱元璋叹了口气,说:“他们兄弟俩,投奔我也十几年了,立下过汗马功劳,廖永安已逝数年,廖永忠今天落得这样惨,朕心里很难过。”朱元璋面谕胡惟庸,“让户部支出银子来,在他们安徽老家修房,给他置办一千亩地,让他回去颐养天年。”
胡惟庸说:“这样也好,干净。”朱元璋不满地瞪了他一眼。
这正是朱元璋的心里话,出于胡惟庸之口,又令他不舒服。廖永忠一疯,谋杀龙凤皇帝的无头案将真的永远无头了,让火眼金睛的太史们去望洋兴叹吧。朱元璋心底其实在为廖永忠庆幸,他这一疯,成功地躲过了一劫。不然,尽管朱元璋不忍心,也不会留下这个活口在人间,就如同廖永忠没有让那两个凿沉了小明王座船的水贼存下活口一样。
当众杀谏臣
无独有偶。不是为孟子遭贬而有吞金死谏的山东道御史吗?今天又来了一个抬着棺材冒死上疏的刑部尚书钱唐。
上朝时分,他把一口黑漆闪亮的棺材摆在了奉天门外,这令朝臣们人人侧目。侍卫们全都围过来,不准抬棺者再往前走。钱唐一脸正气,毫无惧色,见皇宫侍卫们想把棺材弄走,他大吼了一声:“住手!”
侍卫们又惶惑又无奈,钱唐说:“老夫是刑部尚书钱唐,今天来冒死上谏,一死而已,这是老夫的棺材,你们谁敢拦挡?”
这一说,没人上前了。一宫门使迅速跑入殿中。钱唐迈着方步徐步上殿。朱元璋正与群臣议事,宫门使上殿来报:“刑部尚书钱唐抬着一口黑棺材摆在了奉天门外。”
朱元璋大惊,众臣更是惊得转身向殿外张望,这时钱唐已大义凛然上了殿,朗声说道:“陛下,臣钱唐有大事谏奏。”
朱元璋沉静下来,满脸怒气地问:“你抬着棺材是来死谏?你把朕当成昏君了吗?”
钱唐立于阶下,说:“抬棺自随,自不怕死。臣岂愿意死!但如陛下不纳臣谏,臣愿一死以谢先贤。”
朱元璋一下子明白了:“你是为孟子而来?”
钱唐道:“正是。”接着他慷慨陈词,“孔孟是千百年来读书人心目中的圣贤,其书是志士欲救世弊所必读,儒学大师朱熹将其编入《四书》以来,在读书人心目中神圣无比,今吾皇将其删得体无完肤,且将孟子赶出享庙,这是对先贤的冒犯,臣叩请皇上三思,收回成命。”
朱元璋大怒,怒的不唯是他为孟子说话,更在于他胆敢藐视自己,此时如果低了头,今后将无法收拾,即使他所谏是对的,也不可容忍。
朱元璋冷冷道:“你不是抬了棺材来死谏的吗?朕今天就成全了你。”他这一说,全殿大臣们大惊,个个面无人色,钱唐可是个为官清廉,口碑极佳的重臣啊!
钱唐面不改色,大声道:“臣能够为孟子而死,死有余荣。”说罢哈哈大笑下殿。
朱元璋先时下令将他斩首,由于受不了他的大笑,又改令用乱箭把他射死。当钱唐走到台阶中央时,乱箭齐发,顷刻间他犹如一个刺猬。
大殿上目睹的大臣们个个垂下了头。只有一个没低头的是刘基,双目平视,脸上是冰凉和麻木的表情。
杀了钱唐,朱元璋偏偏不准用他自备的棺材下葬,别出心裁地赐了一张芦席,令他家人卷了去埋了,朝中没人敢谏阻。
朱元璋认为这已是宽大了,否则应当剥皮实草,让他的干皮囊永远耻辱地立于人前,这已是他网开一面了。
杀了钱唐,果然没有人再谈孟子的是非曲直了。说来也怪,朱元璋杀钱唐,不怕百官心生怨艾,当年却独独忧虑过江南女才子苏坦妹会给自己带来坏名声。如今时过境迁了,也不知胡惟庸办了那件事没有,朱元璋有理由相信,他在办,而且一定办得漂亮,人不知,鬼不觉。
他没有猜错,这一天,胡惟庸重金役使的几个人正在婺水河畔大行其事。月色朦胧,坐落在婺水河畔的一块石碑在静穆中披着月色闪着青幽幽的光。落款处有朱元璋的名字,墓碑上可见“苏坦妹之墓”字样。
几个黑影走来。他们来到碑前,四下看看,先后抡起大铁锤,顷刻间把青石碑砸得七零八碎。随后,他们拾起碎碑石,叮叮咚咚地投到了婺水河中。坟前只剩了一块墓碑。几个黑影已经消失了,朱元璋的心病也从此消失了。当胡惟庸把这消息带给朱元璋时,朱元璋还装腔作势地说:“你不要胡来,别陷朕于不仁不义!”
胡惟庸笑道:“天下有这样遂人愿的巧事!昨天婺州知府来报,说不知什么人把苏妲妹坟前的御碑给偷走了,我已限令他们破案呢!”
朱元璋一怔,喜上眉梢,却马上一本正经地说:“好!浙江府县要通力合作,一定抓获元凶。这事要大张旗鼓地办,刘基他们知道不知道这件事?当年朕就是立了这块碑,他们四贤才肯应诏而来。”
“臣已经告诉了刘基和宋濂。”
“他们说什么?有何反应啊?”
“没说什么。刘基只是说,这事蹊跷。”
朱元璋便没再言语,胡惟庸又道:“今天有一个画师来,给圣上画像。”朱元璋说:“别又像上两个似的,画功太差,根本不像。”
胡惟庸说这个是岭南有名的画像师,但是不是名副其实,他也不得而知。朱元璋说:“你不是认识那个给达兰画像的人吗?那才是个圣手,达兰的眉毛、头发丝都画得一丝不苟,太传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