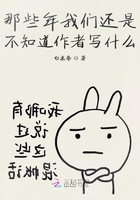没办法,实在想不了什么。
我闭着眼睛,头低垂着,摸着床铺又静静躺下了。
还是睡不着。
我又坐起身,缓缓睁开眼睛,一如既往的黑暗。
我随着记忆,触摸到帘布,而后轻轻拂开,来到自己房间。我想了想,决定先走出这里。
在屋子外面,走了几步,决定坐下来。
凉风自然不必说,只是看不到月亮。
这屋子中和这外面大概都是一样的,只是多了些空旷,少了些倦乏。
天空中的昏明在缥缈的乌霭下,如散去的烟缕,如黑色的薄纱。逶迤的云幔轮廓在远处逐渐模糊,难以分辨的天际与眼中力所能及的大地边埏相接,黑色的粘稠融没在远方。
从此处往右方看,那里理应有一条蜿蜒的河流,事实上,肉眼很难分辨得清,它已经变得狭长,没有光芒映照的它,同周边一样黯然。
眼前的坡在向上延伸,成了矮矮的一座山,像绵延起伏的一座不起眼的小丘,在其顶,仍可依稀辨明一团更加幽暗起伏的存在,那是之前我们走出的林子。
更加遐远的一端,微微左前方,还有另一片林子,我想,那大概就是之前坐公交车穿过的其中一个林子吧。(坐公交车途经了好几个林子)
地上有个石头,我捡了把它扔出去。
之后又捡了几块,无一例外都扔出去了。
然后起身走了。
(我哪知道我屁股底下怎么这么多石头)
我感觉有点脏,就拍了拍手。
之前看到的那个烧着火的石柱不见了。火好像已经灭了,所以我看不到。
我想了想大概的位置,就走了几步,绕了几个圈子,成功发现了石柱。
我抚摸着它,感受着上面的质感,虽然很粗糙,但触感出奇的舒服,我渐渐倚靠在上面,是侧着靠的,左臂拥抱着它,感受着其硬度和粗大。
我感觉有个人,抱住了我。
我睁开眼睛。
那个人抱的更紧了。
我松开石柱,两臂垂下。
由于那个人是从我胳膊下面搂过去的,所以双臂一松,内侧就会接触到。
由于我穿的是短袖,肉就碰到了。
这冰凉柔软的肤质,跟我们班一个男的很像啊!
于是我就说:
“你是男的吗?”
“不,我是女的。”一道柔和温润的声音从我后侧递到我耳边。
“阿姨,我们认识吗?”
“不用认识,凌晨半夜能够相见,本身就是一种缘分,不是吗?”
低头瞅了瞅她放在自己胸腹上的手,因为环境比较暗,所以我也不知道那手何样,我个人比较喜欢包子手。
因为她很使劲,似乎一直想将将我留在她的怀中,所以我感觉到因过分按压自己心脏传出的扑通声。
这种声音想必已传入她的掌心,以她的手臂为媒介,直达其人意识当中了。
想到这里,我就感觉怪怪的,很不是滋味,自己的心跳被她人深深体会,这本身就很微妙,何况在这样静籁淡泊的风下,四下又无人,我俩这久久伫立的人影前后贴合,似乎连月亮都避其嫌,不肯探出头来,在这样黯然无言的天地间,我们的心灵彼此融合,于荒漠中长相厮守……
但我觉得这样的长相厮守也应该是个头了。
我微微侧首,眼角余光可以看到她的肩膀:
“那你现在可以松开我了吗?”我的声音比较平静,但略显压抑。
“这么快就对人家感到不耐烦了?不过有这样一个柔软的女人从身后抱住你,怎么着都不应该这么快拒绝吧?”她没有丝毫放开的意思,口舌之欲裹狭热气布满张力。
我细细体会背后,确实有够柔软的。
我就没啥可说的,先是沉默一会儿,然后眼珠子左撇右撇,有时候想观察她的容貌,但又不想被她发现,故作不经意。然而就在这份所谓的不经意之间,我看到一个人影朝着我妹妹睡的那个房屋掠去。
“现在可以放开我了吗?”我说。
“不,不,再抱一会儿,再抱一会儿。”她似乎在撒娇。
“OK,别怪我。”我猛地往后倒,我不采取掰她手的方式,是因为这的确太耗时间了。然后她可就惨了,身体就跌在上面,我一个翻身撑地,身体有那么一瞬间俯在她上面,在靠得最近的时候,我看到她蹙起的眉头,心中升起那么一丝愧疚。我脚蹬地,站稳了,直往我妹睡的房间跑。
推开房门冲进去的时候,一下子撞到一个人,那人哎呀一声,听声音居然也是女的(不用问我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多女的),我感觉她要栽跟头,手往大概的方位一搂,竟然成功了,然后四周瞬间静默,只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和心跳。
不知道为什么,灯突然亮了,虽说烛光微微,但依旧不妨碍我看到她那惊世的容颜,那一抹似酒韵中酝酿开来的嫣红,宛如春花的羞涩,在朦胧中含苞欲放。
我有点小小尴尬,但是不能妨碍我面无表情,虽说如此,眼珠子还是尽可能的往旁边看去。
手也随着她身体的稳定而逐渐松懈。
往旁边看去的时候我看到一双腿,另一双,目光微微抬起,白灰色的格子短裤,皙嫩大腿,这种波转的轮廓,是我妹妹没错了。
她站在烛灯下,左手拿着打火机,轻轻放在靠窗的桌沿上,另一只手放在下巴那里,用懵而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俩。
她没说话,我也没说话,我面前的这个,大姐?却想趁此机会从我旁侧偷偷溜出去,猫腰而鬼祟,步无声而匿于黑暗,很快就要得逞了。
然而我的手就像长了眼睛一样,明明头看着妹妹,手臂却像独立的个体一般朝左边一抓,一下子就把内衬下摆抓到了,任凭她怎么使劲都挣脱不了。
“跑什么?”我扭过头。
只见她一脸沮丧的神情,身体缩到门后的墙旮旯里,一脸孱弱不经寒风的模样。
这女的一身黑,就内衬是灰色的,有着漂亮的短裙和丝袜,眼睛大而不真实的看着我,仿佛还是个童贞小女孩儿。
“哥,大哥!”然而她一开口就是个土匪小流氓,声音大而粗,将我拉入似真非幻的世界,“可求你放过我!我真的啥都没做!我就在这儿落(lao)个圈儿的!”我真不信这声音是从她嘴里传出来的。
“落个圈儿?”我不明所以。
“就,就蹦跶瞎晃的意思!真的,你不信你问问你女朋友!”
“女朋友?”我啥时候有女朋友?
“就她!她不是吗?”
“呃,她……”正当我要说出妹妹的实际身份时,妹妹却突然抢先回答:
“我是他女朋友。”
??
我看向我妹,她浅浅笑着,面庞安详而柔婉。
好吧好吧,这样也行。我把目光移开,又重新盯视着这名黑裙少女,她腿有些弯,逐渐趋向于内八,眼珠子朝上抬了抬,但是眼皮张开的幅度很小,头也没动,她这一瞟,竟是让我感到一股桀骜冰霜般的敌意,但她眼眸很快闪动,睫毛伴瞳中微光扑朔,像是在整理思绪,调整状态,又不时与我的目光交错,不敢直视,似乎愧疚而心虚,在这几秒钟的眼波流转间,她终于鼓起勇气再看我。
她眼神中有种难以掩饰的闪避,像不清澈的膜覆盖在上面,还透着假意。
我眼神我当然不知,但应该有变化,我开始看她时属于不经意,不在意,眼神很平常,她就能展现外表的那种真稚,好像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似的。但是后来我盯着她看了,她就不能保持,眼下她身体僵硬,眼珠轻微颤栗,我估计她不想装下去了。
她呼吸急促起来,胸口愈加不稳,裙下内八宛如风中枝杈,她突然大叫起来:
“我知道你不会信的,我就知道!”
“……”我心里想的是,然后呢?
她那双昏黑的眼珠随着脑袋的扭动愈加压抑,狭迫的双眼皮将那股浓重突显,好像有人将她逼仄入一个无法跳出的死巷中。
我感到一股强烈的戾气。
“你先放开我。”她眼珠终于有个固定的位置,一动不动地朝左边看(她的右边)。像是在转移注意力,嘴一边儿歪着,讲话的时候有点儿泄气,但含着内劲。
我放开了她。
她手扯了一下刚才我抓的那个地方,像是在把脏东西捋走,然后她眼珠子又偏了一下。
“我进去只是为了种一个东西。”她气压的很重,加上她的声音本就很粗,就给人一种毋庸置疑的感觉。
“种东西?”我不得其解。
“呐,很随便的一件事情,我就把话说这儿了,多的就不能告诉你。你可以放我走了吧?!”
我看了看,本来不想合她意的,正打算问清楚了,外面突然一道声音传来。
是就靠在门外侧的声音。
“虽然我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再等一会儿也行,但是我觉得,都到这个时候了,也应该放过她了吧。”
我想问她们是什么关系,但觉得还是算了,就说:“我怀疑你们对我妹妹动了手脚,所以对于这件事情,我绝对要问清楚。”
“这种事情问不清楚的,”门外的女人说,“何况到了这个地步,也不可能再告诉你更多了,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你难道连一个男人的基本准则都不知道吗?”
“什么基本准则?”
“不要把女人逼得太紧。”
“……”我没啥可说的,虽然她语言平平淡淡,波澜不起,但我觉察到了一股愠怒。
不过我向来就不在乎这个,正当我要继续逼问这个黑衣女孩时,我妹妹突然发话了。
“哥,没什么事的,也不要再这样了,她们没对我做什么,我很好。”
“……”
听到这句话后,我内心几乎没怎么挣扎,但是很剧烈,不过被妹妹这个更加能够摇撼我的存在所折服,我没看妹妹,只是感受着妹妹声音所传递的信息。在近乎死寂的沉默后,我说: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