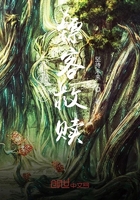理解犹太人引人注目的崛起,有助于理解社会的总体进步。犹太人在美国是白手起家的,开始时并没有诸如金钱或知识这样一些似乎是必备的条件(他们比其他移民更加贫困和无知),也不精于政治。周围社会也没有特别地“接受”他们,或给他们提供经济方面的机会。然而犹太人内在的价值观念和传统精神,让他们在美国的经济环境里恰似如鱼得水,成功自不待言。他们不仅带来了特别的技术,也带来了千百年养成的那种适合于城市工商业活动的生活方式。有时,犹太裔的工人看起来和别的工人没有什么两样,实则不然,他们不少是商人和学者的子孙。他们家庭过去的生计虽被俄国反犹太主义的政策破坏了,但他们仍保持着昔日成功所培植起来的经验、信心和主动精神。犹太人就是住在贫民窟时,他们的贫民窟也与众不同--酗酒、凶杀和意外死亡的比例,普遍低于别的贫民窟,甚至低于所在城市的总体比例。和其他种族相比,犹太人子弟的逃学率和少年犯罪率都偏低,但(到20世纪30年代)智商得分却高出一筹。与其他别的低收入种族相比,犹太人的婴儿死亡率较低,组织和社团却很多。选举国会议员时,低收入犹太人参加投票的比例,也超出高收入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一句话,即使身居贫民窟,犹太人也具备中产阶级的社会模式和价值观念。尽管宣称贫民窟会改变人们价值观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犹太人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价值观,他们把这种价值观带进了贫民窟,后来又带出贫民窟。
简而言之,不管是从犹太人来看,还是从其他种族来看,或志得意满,或步履艰难,皆不单纯是美国的国情可以说得清楚的。成功或受挫的许多原因,都可以追溯到他们很久以前的历史。
社会状况
格外重视家庭,向来是美国犹太人的一大特点,尽管和其他美国人比起来,他们家庭的规模一直在更加急剧地缩小。和其他人有所不同的是,犹太人在其生命的某一时刻总会结婚的,离婚的却不常见。在20世纪30年代,犹太人和异族通婚的比例为5%~9%。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犹太人和异族通婚的比例因地而异,在纽约市大致为8%,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马林县为37%,在艾奥瓦州则超过50%。虽然犹太人和异族通婚的比例在上升,但仍远远落在其他种族的后面。一般来说,凡在犹太社区很小而又靠近大量非犹太居民的地方,他们和异族通婚的比例就往往偏高。但亦不尽然,纽约的犹太社区算是够大了,但和异族通婚的比例也在上升。无论如何,和其他欧洲来的种族相比,犹太人和异族通婚的比例仍然不算高。
犹太人家庭的规模,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年里,犹太人家庭的人口一般比其他多数种族的家庭人口要多。但到20世纪中期,犹太人的家庭就进入规模最小者的行列。在1910年,30多岁和40多岁的犹太妇女,平均每人有5.3个孩子,而相比之下,全美同年龄段的妇女平均每人却只有3.4个孩子。比起黑人、爱尔兰人或意大利人来,犹太人家的孩子多,而与长期处于高生育率状态的墨西哥人持平。到1969年,犹太妇女平均每个人生育的子女减少了一半多,即2.4个,低于此时全美的平均数3.4个。这样一来,犹太人口就出现了年长者众而年青者寡的局面,因而与其他任何一个少数种族相比,犹太老年人所占的比例都偏高。现在美???犹太人的平均年龄是46岁,比黑人、印第安人、波多黎各人或墨西哥人的平均年龄要高出一倍以上。这使得在高层次行业中就业的犹太人显得特别的多,因为这些行业需要丰富的经验和知识。
尽管犹太人和异族通婚的比例较低,却向来与其他种族群体保持着和睦甚至是合作的关系。这种睦邻传统当然也是从欧洲带来的,在欧洲,不必要的敌意将危及犹太人自身的生存。在美国,犹太人和德国人及意大利人历来就相处得很融洽,参与并部分地资助过黑人民权组织。爱尔兰人和各种族都斗过,当然也和犹太人发生过冲突,但当别人不愿雇用爱尔兰裔工人时,犹太老板仍然雇用他们,尽管爱尔兰老板并不以对等的做法来回敬犹太人的好意。当黑人迁入他们的地段时,犹太人向来并不怎么加以抵制,哈莱姆一带在20世纪初曾经是犹太人的地盘。
在政治上,犹太人历来倾向于接受或至少是附和“弱者”的观点,尽管他们自身在经济上早已不是弱者了。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构成了美国犹太人的两大政治主流。早期犹太移民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观点,由于他们摆脱了工人阶级身份而上升到中产阶级地位,也已让位于广义上的自由主义观念,尽管犹太人当中的偏激分子仍然特别多。早在19世纪,当共和党被认为比民主党更加开明时,犹太人属共和党,例如他们曾是林肯的支持者。他们到20世纪20年代都一直投共和党的票,伍德罗·威尔逊在1916年曾把他们拉到民主党一边。在1920年,有11位国会议员是犹太人,10位是共和党,1位是社会主义党。但在1922年,以民主党身份当选国会议员的犹太人超过了以共和党身份当选的犹太人,这在20世纪尚属首次。1940年,90%的美国犹太人投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票,1944年还是如此,1948年杜鲁门竞选时仍是如此。此后20年,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票的犹太人,比例最低的1956年也占60%。犹太选民党派所属的变换,与两党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取舍恰好相吻合。对纽约犹太人的一项调查发现,75%的人是登记在册的民主党人,半数人自称属“开明派”,只有不到25%的人才自称属“稳健派”。和犹太人属于相同收入档次的美国人,则大多倾向于保守观点,拥护共和党。这一点,完全凭犹太人在美国的经历--尤其是他们的经济地位已有显著的提高--为依据,是难以理解的。但是,假如把视野投向犹太人千百年来着意照顾同族穷人的宗教传统,投向他们在欧洲各地作为备受迫害的少数种族这样一个历史背景,问题就很容易得到解答。
犹太裔候选人时常能取悦于犹太选民,但因双方都是自由派人士,所以非犹太裔候选人也能取悦于犹太选民。赫伯特·汉弗莱在1968年就曾比亚瑟·戈德堡争取到更多的犹太人选票。在1962年,共和党人雅各布·贾维茨在犹太选民当中的得票数也输给了一位爱尔兰裔的民主党候选人。
与犹太人的品行十分不相称的现象之一,就是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犹太帮歹徒。自公元70年之后的大规模疏散以来,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对犹太人来说都是可憎的,尽管古代以色列也曾有过自己伟大的勇士。拳击运动在英国兴起时,犹太人甚至不准本族的拳击手死后葬在该族神圣的墓地里。大体上说来,纽约东南端的犹太社区算是太平的,坐班房或被监禁的犹太人很少。犹太人一般多是犯罪案件的受害者而非害人者。但在第二代犹太人当中正如在其他移民种族之中一样--出现了一批死心塌地的恶棍。在1909年,有3000名犹太裔不肖子弟被押赴纽约的青少年法庭受审,其后,犹太裔成年歹徒就成了臭名昭著的犯罪团伙,卖淫的事也出现了,这使纽约曼哈顿东南端的犹太人社区大惊失色,因为他们不管是在欧洲或在美国都看不惯这种丑恶现象。但在曼哈顿东南端的第二代犹太人当中,冒出了一批拉皮条的、小偷以及流氓和犯罪团伙的头目。到20世纪20年代,阿诺德·罗斯坦是“纽约黑社会的独尊首领”。臭名昭著的“谋杀公司”是一个专门杀手组织,其头目们都是犹太恶少。在基本上由犹太人把持的纽约成衣制造业部门,在遇有罢工时,劳资双方都借用流氓的力量,而这些流氓甚至摇身一变当上了公司和工会双方的官员。
与犹太人子弟操守不相称的另外一个行业是拳击。在20世纪初期,本尼·伦纳德和巴尼·罗斯是两个家喻户晓的犹太裔拳击运动员。他们很多人在拳击场上使用爱尔兰人的姓名,因为后者已在拳击运动方面建立起巨大的声望。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犹太裔拳击运动员也和犹太裔歹徒一样,逐渐销声匿迹。这两种都是玩命的行当,但凡有其他出路的人,皆不愿混迹其间。
对后代的美国犹太人来说,最惨不忍闻的事件发生在美国境外,这就是纳粹在德国的兴起和其后那场有600万犹太人惨遭不测的大屠杀。这场亘古未有的大屠戮,不仅手段之残忍及受害者数量之众实在骇人听闻,而且格外令人惊诧的是,它竟然发生在德国这个先进的现代国家。犹太人此前在德国的处境,向来比在欧洲其他地方要好些。也就是在一代人之前,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犹太人出版物一直帮德国讲话,以致遭到美国政府的调查,并以在战时为敌国张目的罪名而被提起公诉。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提出的“明确而现存的危险”定罪原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审理涉及犹太裔作者的案--阿伯拉姆诉美国案和申克诉美国案--时提出来的。
既然连德国都会翻脸,向犹太人下此毒手,想赶尽杀绝,那犹太人怎能放松警觉而悄悄地与其他民众融为一体呢?做个犹太人已经不是人生一个偶尔触及的特点了。持同化论观点的犹太人士曾劝说同族人变为“具有希伯来信仰的德国人”,这种简单化的尝试已经沦为可悲而又可怕的笑柄,使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痛切地认识到,当务之急是加强犹太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虽说是亘古未有的,却也向世人强烈展现了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即对犹太人是时而和解、时而排斥、时而庇护、时而驱赶。犹太人时而昌盛发达,时而惨遭屠杀。犹太人在西班牙、波兰和俄国,历史上都有过这种变幻莫测的遭遇。
一桩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件--也发生在美国境外--使美国犹太人大大加强了种族认同意识,并深感欣慰,这就是现代以色列国家的创立。作为世世代代散居异国的民族,长期仰别人的鼻息过日子,犹太人终于再次有了自己的祖国。创立和捍卫新的以色列国家的勇武精神,有力地改变了犹太民族在“集居”区和篱笆墙内偷生时给世人造成的那副绝望而胆怯的可怜相。曾在美国支持过许多本族市民组织和全美犹太组织活动的犹太慈善机构,也向新的以色列国家伸出了援助之手。不少美国犹太人甚至到以色列去大显身手。从密尔沃基去的果尔达·梅厄夫人就是其中一个。
今天美国犹太人的认同感并非昔日旧世界那种犹太宗教意义上的认同感。大多数美国犹太人今天并不尊奉传统的犹太安息日,参与犹太教会的活动也不算热心。他们的认同感带有种族的性质,尽管这种认同感从历史上来看脱胎于一种特定的宗教。
今天的美籍犹太人
犹太人的家庭收入高出全美平均水平的72%,在美国种族当中算是最高的。没错,犹太人平均年龄和受教育的程度都偏高,但仅仅这两个因素还不足以造成如此之大的差别。即便不具备这两个因素的犹太人,平均所得也比别人要多。由受过4年或4年以上的高等教育且年龄在35~44岁之间的男子充当家长的犹太家庭,其收入高出全美平均水平达75%。这里部分的原因是,犹太人不仅受到更多的教育,而且受到更好的教育,读的是高质量的大学,选的专业也多在博大精深的领域,比如法学、医学和科学等。由受过不满9年的教育且年龄在35~44岁的男子充当家长的犹太家庭,其收入仍然高出其他处于同样状况的人。简而言之,这里存在着统计数据无法涵盖的素质和文化上的差别,这些差别也明显地影响犹太裔人士的发展。第一代犹太移民家庭曾让妇女和孩子工作以增加收入,现在这种情形已不复存在于犹太人家庭。今天,不止一个人挣钱的犹太家庭,在比例上低于全美的一般家庭。甚至无人工作的犹太家庭,在收入上也高出其他无人工作的家庭。正如在其他方面积累起来的有利条件一样,犹太人从这种或那种投资中获得的收入显然要高。
在某种意义上说,犹太人是美国成功故事的典型之作:在逆境中从一无所有到腰缠万贯。此外,一如那些在美国找到了自己祖籍国反而被剥夺机会的其他种族一样,犹太人是自豪而爱国的美国人。但是犹太人的历史远比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要久,内容也更加丰富。在其他的时代和其他的地方,犹太人也曾登上财富和权势的顶峰,但皆被不可捉摸的反犹太主义狂潮所毁灭。故此犹太人难以成为既存权力体制的安闲成员,不管他们拥有多少该权力体制的显赫标志。尽管很富有,但犹太人在政治上一般都偏左。激进派人士当中,犹太人特别多,??然多数犹太人并非激进分子。正如一位杰出的学者观察到的,“100个犹太人当中,可能有5人是激进分子。而在10个激进分子当中,则可能有5个犹太人”。
犹太人在支持自由派候选人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不管这些候选者本人是不是犹太人。甚至当乔治·麦戈文在1972年的大选中被广大选民所唾弃,只获得38%的民众选票时,他却赢得了65%的犹太人选票。作为罗马天主教的自由派人士,德里南神甫在1970年竞选国会议员时,获得了64%的犹太人选票。相比之下,只有2%的犹太选民在1972年的大选中支持总统候选人乔治·华莱士,华莱士甚至在不是白人的选民当中赢得的选票(3%)也高出这个比例。
“肯定性行动”计划在20世纪70年代的实施,导致某些犹太团体与他们传统的激进派和自由派盟友--包括黑人民权运动组织--分道扬镳。该计划就就业、升级或大学招生在数量上规定了要达到的“目标和进度时间表”,使犹太人回想起过去美国为了限制他们的机会所实行过的配额制度,这种制度亦曾在欧洲更为严格地实施过。况且,经过几代人的奋斗,犹太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了,现在在高校教授队伍当中,在政府高层领导岗位上,在各行各业及工会领导层,犹太人所占比例都是格外地高。以人口多寡来“分摊”的原则,不管其动机如何,都必然会损害到他们目前的利益。
犹太人到现在的成功是罕见的,但绝对不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圣公会教派的信徒在收入上就比犹太人要高。正是美国犹太人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弥补了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巨大差距,才使得他们的发展史是如此的光耀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