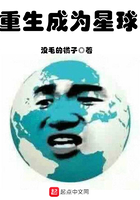王大炮这个人,说来绝对是一个传奇人物。不过,说到王大炮,怕又要重提我们王家的祖上了。
据村中老人讲,一百年前,三十里外大财主袁家,之所以最终选中我们王家祖上来看坟,除了我们王家祖上对他们袁家忠诚,一个很大原因,就是我们王家祖上会武功。据说,一旦动起手来,十个二十个年轻小伙子根本就到不了他的跟前。
这还是其一。
其二,我们祖上还会一种顺风耳的功夫。当然,这种功夫,后来我知道,跟狗趴到地上听动静的功夫差不多,也跟猛兽几里外都能闻出人的味道也差不多。不过,我们袁家坟村老人也一致认为,这种功夫,并不是天生的,也是我们祖上长年累月练出来的。
当然,还据我们袁家坟村老人讲,祖上练就的这套功夫,规定只传王家老大不传小,只传男不传女。王大炮祖上这一支,也恰是我们王姓族人老大这一支,一百年后,功夫自然而然传到王大炮身上,也是理所当然。
可是,王大炮十八岁当兵——当然,从我们袁家坟村出去的当兵人也不在少数。可个个还是最终回来了。只有王大炮,四十年过去,却再没有回到过袁家坟。不过,具体到这四十年,王大炮在外边都做些什么,村里人无人知道。他身上的功夫,也自是再没有传给我们袁家坟村人。
不过,四十年后,王大炮还是最终回来了,还是用一辆吉普车送回来的。不但来了一帮陌生人,县上、公社里的头头脑脑也都跟来了,并在跟来的那些人的强烈要求下,王大炮还直接被安置到了我们袁家坟村房子建得最好的地方——袁家坟村大队部——一间最好的房间里。
这时候,村里人也才清楚,原来这个王大炮,这些年其实跑得也不远,竟一直生活在北京,并已在北京娶妻生子。孩子有男有女,当然也都很大了。
也就在王大炮五十八岁这一年,不知犯下了什么错误,妻子和儿女都跟他划清了界线,决定生死再不往来。这让王大炮精神上很受剌激,也从此开始胡言乱语。
不过,送他来的那帮陌生人,临走时,可是再三叮嘱县上和公社里的头头脑脑,要他们一定照看好王大炮,保证他不能有任何闪失,县上和公社里的头头脑脑都满口应下。
王大炮,很后来我才知道,并不叫王大炮,大名叫王智慧。因为回村后,到处说他曾跟***问过好,跟周总理握过手,还曾保护着***到过苏联……总之,在当时,这些我们袁家坟村民想都不敢想的大人物,王智慧却敢拿他们吹牛皮。大炮吗,我们袁家坟村人,对这些人的称呼一向这样。
当然,关于王大炮的武功,许多村民还是亲眼见识过。那还是王大炮回到我们袁家坟村的第一个冬天,人们都在大田里收割大白菜,突然一只野兔儿从大家眼前蹿过。兴奋中,许多年轻人开始狂叫着围追堵截。但无论他们如何围追堵截,就是捉拿不住。王大炮见了,只猛地挥出了手中镰刀,那只奔跑的野兔就当即趴在了那里,一动不动了。人们捡回一看,锋利的刃早已深深镶进野兔的肚子里。
王大炮站在我家院门口,高声喊叫我母亲。母亲隔着窗上那方小玻璃,应该看到了。母亲没有理他,因为我又听到了母亲和大姐的悄悄说话声。
“王家大嫂子,我知道你在屋里,还是赶紧出来吧,要不,你们家怕是要有大灾祸了。”王大炮站在院门口仍在高喊大叫,却又决不踏进我家院子半步。
应当说,王大炮如此喊叫,我们是不必担心邻居会听到的。我曾说过,我们居住在村子的最南端,往西往南都是大田。眼下,我家院墙外的大田里种得都是玉米,棵了都长成两人多高了,已给人一种很封闭的感觉。
还有就是,现在正是上工时间,村里除了跑着玩的孩子,就是耳聋眼花走不动的老人。就连母亲也是听说大姐回来,才临时向生产队长请了假,从很远的一块大田里赶回来。
“栓柱,去看看,快让你这位神经爷爷走开,别让他在门口乱喊乱叫了。”母亲透过里屋和堂屋的布门帘,很是不耐烦地对我说。
同样是在堂屋,母亲不喊二姐,而喊我,这也让我第一次有了我是我们王家唯一男人的感觉。
我答应一声,来到门口。这时候,王大炮还想喊,我却在他喊出声音之前,先喊了他一声“爷爷”。
实事求是地讲,王大炮年轻时,应该是一个长相极为帅气的人。就是现在,在我七岁孩子的眼睛里,除了皮肤黑一些——其实,在我们农村参加过一段时间劳动的人,再白的皮肤也会让它黑下去的。当然了,赵利英这样的老师除外——王大炮浓眉大眼的,尤其那副身板,尽管五十多岁的人了,仍是那么高条笔挺,处处都透着已与我们农村人不同的一面。
果然,王大炮听到有人喊他爷爷,急躁的情绪马上不再急躁了。
“你妈呢,她不是在屋里吗。”王大炮满眼看着我,说,“快叫你妈出来,我可是有句要紧话要告诉她的。”
“爷爷,我妈说了,她不想听,你还是快走吧。”我怯怯地,却又满是勇气地对王大炮说。
“怎么能够不听呢,刚才在大队部,我是亲耳听到他们说了,他们开了一辆吉普车,马上就要过来了。”
这话吓了我一跳,我想,也一定吓到母亲了。在我刚想喊母亲出来,母亲已经快速走下台阶,来到了王大炮面前,后面还紧跟着我的大姐和二姐。
“他爷爷,你说说,谁开了吉普车要过来了?”就听母亲急切问道。
“县上的和公社的那帮人!”
“他们要来我家做啥?”母亲仍有些似明白又不明白地问道。
“他们说要抓你家大姑娘到县上。”
王大炮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看出,完全一副清醒的样子。
可母亲刚想问什么,大姐却很响地笑了。
大姐:“不用说,定是安主任派车来接我了!”
“接你?”王大炮很是疑惑地看着大姐,说“怕是要接你进火坑吧。”
大姐便一扭屁股,几乎连看都不愿看王大炮一眼,一转身又朝屋里走去,且边走边很是得意地说:“即便是进火坑,也是用吉普车接进去的。”
说完,又说:“我可没时间在这儿与你费话了,我得赶紧收拾去了。”
边说边扭着她十七岁的屁股,进屋去了。
母亲便越来越有些不知所措起来。那样子,她既想多问王大炮两句,又想着还是快些把这个神经病人轰离自家门口为好。
可也正在这个时候,一辆绿颜色的吉普车很洒脱地拐过西边那个急转弯儿,紧接着,便“呼”一下停在了我家门口。随着车门一开,也从车上跳下来三个人来。
其中一个,我自然认识,就是经常来我家的王有发。另一个,看上去,比王还要小着几岁的年纪,比王有发也白净的多,穿着也体面的多。还有一个,年纪又大肥胖的身体,尤其长着一个大脑袋,略显秃顶。一说话瓮声瓮气,样子又总是一副要做报告的架势。
随后,我知道,这人不是别人,正是王有发三姨父,公社革委会主任胡来。
就见他们极其坦然地从车上走下来,然后由王有发带路,紧接着,就要朝我家院子里走。
这时候,王大炮仍堵在院门口。
王有发:“大炮,你在这干啥?”
王大炮:“阻止你们抢人!”
“胡说,谁抢人了?”王有发一听,有些恼怒说,“怕是你的神经毛病又犯了!”
“我没犯,”王大炮也是满脸怒气道,“我脑子清醒的很。”
“那就快闪开!”仍是王有发在说,“快让胡主任进院子里去。”
王有发的姨父胡来和那个穿着体面的年轻人,只是站在一旁看,并不说话。
这时候,母亲见胡来来了,竟进不了院子,也有些尴尬,也再次劝王大炮。
“他爷爷,这里没有你啥事,”母亲说,“你还是回大队部歇着去吧。”
王大炮:“怎么没什么事,他们来抢你们家闺女,既然我见了,就不能让他们抢!”
母亲:“就是他们来抢,也是抢着让我闺女享福去了。”
王大炮便“呸”了一声,说“社会主义社会,任何人都不能享福,只是勤勤恳恳劳动。”
母亲:“他们接我闺女,就是让她去劳动的。”
王大炮点了点头,似乎真得糊涂了一下,说:“对,劳动。”
但刚想离开,又突然清醒过来说:“他们接你闺女,不是来接你闺女劳动的,是要去祸害你闺女的。”
这时候,就见站在一旁的胡来不禁皱了皱眉头。王有发见了,不由恼怒地掉头就走。
就见不大功夫,王有发就带来七八个民兵骨干,后面还跟了我们村的妇会主任兼赤脚医生王小脚。
这七八个民兵骨干,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都是从部队复员回来的。在村里,也是从不下田劳动的。他们每天除了在村里,就是在大田里转,用我们袁家坟人的话说,是专门守护我们袁家坟村人平安的。
就见王有发来到近前,把手一挥,猛喊一声:“把这个老神经给我捆了!”
带了几个民兵便一拥而上。我说过,王大炮别的可以吹,但身上的功夫又绝对不是吹出来的。
也就在几个民兵一拥而上的同时,王大炮也同时把背着的粪筐和手中的镰刀同时放到了地上,手臂张开,双脚也分开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随着七八个民兵一拥而上,只刹那间,在我的感觉里,王大炮也象变了一个人一样。或说刚才的王大炮刹那间不存在了,站在我面前的完全是一个孔武有力的年轻人。瞬间,双方就交了手。
虽然,几个民兵要想捆住王大炮,怕是有些困难。但话又说回来,王大炮毕竟又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武功虽在,但体力怕也不似年轻时候了。当然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我们王家祖上的真传功夫,也不一定如我们袁家坟村民所传,十个二十个年轻小伙子到不了近前。
说话间,就见一个民兵猛扑到地,紧紧抱住了王大炮刚要抬起的一条右腿。紧接着,左侧一个民兵又顺势抱住了王大炮的那条左胳膊。一条右腿一条左胳膊被民兵死狗一样抱住,王大炮想踢腿踢不了,想挥拳挥不动,只听“咕咚”一声,被一拥而上的其他民兵用力按趴到了地上。
这时候,还没等民兵掏出绳子捆,又只见妇会主任兼赤脚医生王小脚先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带着很长针头的注射器,用手举着奔向前去,就见他连王大炮的裤子都没脱,便直接把注射液注射进了王大炮的身体里。
应该说,王小脚给王大炮所用剂量怕是太大了,就见王大炮只挣扎了一下,就沉沉地象死狗一样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