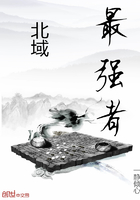予澈走的甚急,漓裳紧紧拽着他的衣袖,撩起裙裾小跑着依然跟不上他的步伐,直被他拖拽踉踉跄跄的。
“王爷,您、您走慢点……阿漓走不动了……”全福小心翼翼地提醒。
予澈住了步子,骨节分明的手指探向漓裳沁着细密汗珠的额头,“傻丫头,走不动了怎么不说一声?”他弯下腰,在她面前蹲下。
漓裳默默地爬上他的脊背。
幽蓝的苍穹,流云随风如扯开的棉絮铺展在天空中,月儿娟娟,从云从中娇怯地探出头来。
漓裳低垂下眼睑,轻轻地问:“予澈,八王会相信你的话吗?他会不会就此忌恨上咱们?”
予澈的瞳孔里泊着星星点点的月光的影子,显得格外的幽深,“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他即是存了疑忌,我便是此刻瞒了他,我们之间也不可能回到最初的融洽和和谐了。”
隐约看见一条罅隙在他们之间不可避免的裂开了,他叹了口气,又道:“总有真相大白的那一日,与其来日相对无言,不如此刻说分明了。况且我如今身份尴尬,多一个人记挂,少一个人记挂原也没有什么分别。”
漓裳无力地将头倚在予澈的肩膀上,予澈的侧脸美好,却如初秋的夜晚,玉露澄清,银河泻影,终难掩露干霜落掩杀而来的萧索和寂寥。
她难掩凄切之意,不敢再看他的脸,只是仰头看那素月分辉,银河共影,错落交叠的花草树木如同笼罩在烟水中一般,通透的清光洒下,凛冽出崔嵬的剪影,层层叠叠从背后扑来。
回到静水庵时,在禅房内焦灼不安地踱步的容若一把抓住了予澈的胳膊,眸中隐忧闪现,“澈儿……”
她抬头望了望门外,唏嘘着,转过脸去,无言滚下眼泪。
“臣年扶风叩见王爷!”年扶风踏着强而有力的步伐在门外行礼。
予澈淡淡地应了一声,并不回头,他扳过容若脸,屈起手指开去她乌青的眼睑上挂着饿泪花,“姑姑又做噩梦了?”
“我……”容若平抑的声调隐约带了些颤音,“我又梦见……”
“姑姑!”予澈打断了她的话,“我已经和八弟坦白了。”
容若听说,似给谁暗地里扎了一针似地,惊呼出声,“你、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实诚啊?”
予澈良久无语,飘渺的目光随着晚风飞上落寞的枝头,留下一声若有若无的轻呓,“姑姑,我们走了。您多保重!”
年扶风侧身立在一旁,“王爷,请!”
予澈微微颔首,携了漓裳的手出了门,淡淡地扫了一眼木格窗子下予泠略显萧索的身影,径直下了台阶。
山下早有宝马香车在此久候,予澈抱着漓裳上了马车,车驭赶车即行。
漓裳悄悄挑起帘子的一角,苍茫的夜色下,年扶风一身莹白色的盔甲昂藏跨于马上,按辔徐行,前前后后,更有千余羽林卫环伺围绕。
“一夜长着呢,睡会儿吧。”予澈将她揽在胸前,掖上了毯子。
漓裳的嗓子干涩的几乎说不出话来,“予澈,我怕。”
她很害怕,害怕睁开眼睛时再也看不到他。
可她已经不敢看他言笑自若后的哀戚和荒凉。
予澈修长的食指拂过她蝶翼般扑扇着的长睫,在她的耳边低语,“阿漓不怕。乖了,闭上眼睛。相信我,不会有事的。”
漓裳听话地闭上眼睛,吱吱咯咯的车轮碾过地面的声响伴着咴咴马蹄声迤逦一路,终于不曾入梦。
抵达冶城时,已是平明时分。
年扶风将他们送进了睿王府,只说皇上御驾隔日会来睿王府,便匆匆告辞了。
年扶风昂藏的背影隐如交叠错落的花影深处,漓裳这才转过头来,呐呐地问:“皇上来睿王府?他为什么要来睿王府?”
“皇上御驾亲临,那可是莫大的殊荣!”
予澈笑着吩咐月婵准备来日迎驾的事宜,又命小丫头煮了药膳并早点过来。
无双和妙常已经备好了沐浴的香汤,漓裳一夜未眠,给她们舒舒服服地伺候着,不觉已是眼饧神色,朦朦胧胧中竟睡了过去。
隔日,予涵并没有来。
倒是容若派人传了信过来,说予泠和她谈了一夜,一大清早便回了济阳去了,再不知他心底是怎样的想法。
第三日、第四日……第十日……第十五日……
恍然月余过去了,予涵依然没有来。
漓裳朦胧着双眼倚在予澈的腿上,有一下每一下地绣着手里的荷包,左思右想,再不知予涵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予澈放下手里的书卷,初秋散淡的阳光透过扶疏竹影洒落在窗棂上,是悠悠荡荡的金色光圈。
予澈淡淡地目光掠过立在屏风外的两个窈窕的身影,笑得云淡风轻,温润的唇瓣摩挲着漓裳的耳垂,“左不过是寻个借口拉着咱们回来,放在眼皮底下看着,放心些罢了。怎么还惦记着这个事儿?”
他的手探向她日益瘦削的下巴,柔声道:“日日补着,反倒是越发的瘦了?到底是宫里的御医技艺精良些。明儿八月十五,顺带让御医给瞧瞧吧。”
一枚黄叶掠过苍翠的竹叶梢头,扑落在雕花锁窗上,叶片卷曲,微黑的茎脉历历可见。
漓裳的眉心残留下一丝凄清,“我……我不去……”
予澈犹豫了一下,着力掩去所有的情绪,换上坦然无波的神色,“倘或太后专门下了懿旨来请你,你去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