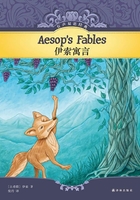Mallory grunted. De Lesseps' face, instead of expressing appreciation of the compliment, blanched suddenly, and his hands closed tightly. Again he recovered himself and smiled.
"The beauty of this picture lies not only in its faithfulness to the original, " the scientist went on, "but also in the fact that it was painted under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For instance, I don' t know if you know, Mr. Mallory, that it is possible so to combine glue and putty and a few other commonplace things into a paste which would effectually blot out an oil painting, and offer at the same time an excellent surface for water color work."
"This water color—this copy of Whistler, " continued the scientist evenly—"is painted on such a paste as I have described. That paste in turn covers the original Rubens picture. It can be removed with water without damage to the picture, which is in oil, so that instead of a copy of the Whistler painting, we have an original by Rubens, worth fifty thousand dollars. That is true; isn' t it, M. de Lesseps? "
There was no reply to the question—none was needed. It was an hour later, after de Lesseps was safely in his cell, that Hatch called up The Thinking Machine on the telephone and asked one question.
"How did you know that the water color was painted over the Rubens? "
"Because it was the only absolutely safe way in which the Rubens could be hopelessly lost to those who were looking for it, and at the same time perfectly preserved, " was the answer. The Thinking Machine"I told you de Lesseps was a clever man, and a little logic did the rest. Two and two always make four, Mr. Hatch, not sometimes, but all the time."
马修·科尔在车轴润滑油生意上足足赚了五千万,随后他便开始四处收购名画。原因很简单,他有钱,而欧洲也不缺大师级名作。不过,他收购名画只是为了填满府邸中占地大约五千平方米的艺术厅,所以他总共买了总面积大约五千平方米的画。画的品质参差不齐,大多数都是次品,不过,他也买到了不少好的作品,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他在罗马花了五万美元买下的鲁本斯的名作。
收购完成之后,科尔打算对这间宽敞的大厅作些许变动。于是,他让人把画全部摘下来,存放在同样宽敞的宴会厅里,并让所有的画都面朝墙壁。同时,科尔和家人则暂住在一家小旅馆内。
就是在这家小旅馆里,科尔和吉尔斯·德·勒赛普斯相遇了。德·勒赛普斯是那种典型的说话细声细气的法国人,神经兮兮的但是又聪明伶俐。他告诉科尔,自己不但是个画家,而且是个高级艺术鉴赏家。一向为自己的藏品感到自豪的科尔想在这位“专家”面前炫耀一下,于是便带着他在宴会厅内费力地翻看自己的收藏。德·勒赛普斯时而眼中闪现出惊叹的神情,时而只是礼貌地笑一笑,看不出任何感情色彩。
随后,科尔把鲁本斯的名作《圣母子》拿到这个法国人的面前。虽然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但是这幅画依然色彩鲜艳、栩栩如生。可令科尔有点儿失望的是,德·勒赛普斯好像并没有对它另眼相看。
“看到了吗?鲁本斯的名作!”他大喊。
“看到了。”德·勒赛普斯回答说。
“我花了五万美元买下的。”
“可能不值这些。”德·勒赛普斯耸了耸肩,移开了目光。
科尔有点儿懊恼地看着他。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是鲁本斯的名作,不知道鲁本斯是个大画家吗?还是没听到这是自己花五万美元买来的?以前他每次提到五万美元的价格的时候,听众们总是目瞪口呆。
“喜欢吗?”科尔问。
“当然,”德·勒赛普斯回答道,“但是我以前见过这幅画,就在罗马,就在你买下它的一周前,我已经看过了。”
他们继续翻看着其他画,突然,一幅惠斯勒的画映入眼帘,这是著名的泰晤士水彩画系列中的一幅。德·勒赛普斯两眼放光地盯着它,还不时地瞟瞟鲁本斯的画,似乎在比较现代作品中的细腻与古老画派的豪放。
科尔却误解了德·勒赛普斯的沉默,他说道:“我也不怎么喜欢这幅画。”他的语气中略带歉意,“只是惠斯勒的一幅风景画而已,我花五千美元买下了它,不过,我自己却不怎么喜欢。你觉得呢?”
“我觉得太棒了,”法国人兴奋地说,“我觉得这是现代作品中的精华,是最完美的一幅。请问,我可不可以临摹一幅?”他转向科尔,“我自认为绘画水平还不错,我肯定可以画得以假乱真。”
科尔被夸得有点儿飘飘然了,渐渐地,他也觉得这幅画确实很不错。“当然可以,”他答道,“我可以把它送到你的旅馆里,然后你可以……”
“不不不,”德·勒赛普斯马上打断他,“旅馆里随时都可能发生火灾,万一出了问题我可负不起责任。如果可以的话,我能不能到这里来?这里宽敞明亮、通风好,而且还很安静……”
“我只是觉得旅馆对你而言更方便一些,”科尔很大度地说,“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在这儿画吧。”
德·勒赛普斯走到科尔的身边,挽着这个百万富翁的胳膊,诚恳地说:“我的朋友,如果这些画是我的,我不会让任何人在这里多作停留。我敢说这些画肯定花了你……”
“六十八万七千美元。”科尔骄傲地说道。
“想必你不在家的时候一定是派人严加看管?”
“有二十个用人负责装修时家里的安全,”科尔答道,“其中有三个人专门负责看管这些画。我们进来的门是这个房间唯一的入口,其他入口都已经用铁棍封住了。只有得到我的允许或者拿着我的书面许可,才能够进来。所以说,没人能偷走这里的任何东西。”
“不错,不错,”德·勒赛普斯微笑着,充满敬佩地说,“我觉得我看待事情可没有你这么强的预见性。”他回过身来漫不经心地看了一下,试探道:“可是,一个聪明的窃贼完全可以把画从画框里割下来,然后卷起来藏在衣服里面带出去。”
科尔笑着摇了摇头。
几天之后,德·勒赛普斯买齐了临摹惠斯勒的画所需的全部物品。科尔则亲自把他送到了宴会厅门口,德·勒赛普斯自然千恩万谢。他们俩站在宴会厅的门口。
“简宁斯,”科尔对一个仆人说道,“这是德·勒赛普斯先生。他要到宴会厅内画几幅画,他可以在这里自由出入。记住,不要让任何人打扰他。”
德·勒赛普斯看到鲁本斯的名作被随意地丢在其他画旁边,画中的圣母正好面对着他们。“科尔先生,”他抗议道,“这幅如此名贵的画这样放着不大好吧,万一有老鼠呢?请您让仆人拿一块帆布来,我会把它包起来,然后放到这边的桌子上。”
科尔表示感谢,让仆人照办,随后他们把画包起来放在了安全的地方。德·勒赛普斯开始布置作画的物品,纸张、画架、凳子等等,科尔看了一会儿便离开了。
三天之后,当科尔进来的时候,德·勒赛普斯仍然在画板前忙碌着。
“我只是路过,”科尔解释道,“来看看这儿装修得怎么样了。还有一周就完工了。我没打搅你吧?”
“当然没有,”德·勒赛普斯赶忙说,“我也快完成了。看看我画得怎么样?”说着,他把画架转向科尔。
这位富豪看了一眼仿作,又转头看了一下原作,眼中流露出敬佩的神色。“哇,太棒了!”他大声说,“简直和真的一样。五千美元,你肯定不卖吧?”
他们就聊了这几句。随后,科尔出去转悠了大约一个小时,查看了装修情况,然后又回到了宴会厅。他看见德·勒赛普斯在收拾画画的工具,于是便和他一起回到了旅店。德·勒赛普斯腋下夹着卷起来的惠斯勒水彩画的临摹本。
一周之后,艺术厅装修完毕,施工人员也离开了。德·勒赛普斯主动要求帮科尔把所有的画挂回去,科尔当然开心地答应了。那天下午,他一边挂画,一边和科尔开心地聊天,但是,当他打开包有鲁本斯名画的帆布时,突然目瞪口呆——画不见了!空空的画框上残余的帆布碎片留下了刀子割画的痕迹。
科尔报案一天之后,被称为“思想机器”的奥古斯都S.F.X.范杜森开始关注这件事。画被偷后,科尔焦急地跑到警察局马洛里警官的办公室报案,将生气的双拳砸在马洛里的桌子上,气冲冲地说:“我花了五万美元啊。你怎么不去调查?你坐在这里盯着我干吗?”
“冷静点儿,科尔先生。”警官说,“我马上派人去找你丢的那个……对了,那个鲁本斯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是一幅画!”科尔大叫道,“是一块上面画着东西的画布。我花了五万美元,你一定要给我找回来。”
警察们马上开始着手调查。与此同时,哈金森·海奇记者也开始关注这个案子。他了解到画被偷之前的情况,然后便去拜访德·勒赛普斯。门开了,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这位艺术家那近乎暴怒的眼神。记者的到访令原本就很激动的德·勒赛普斯变得更加神经质,他大声说道:
“老天,太不可思议了!叫我怎么说?除了我之外,那几天没人到过宴会厅;而我也是唯一一个愿意不怕麻烦,去保护这幅画的人!现在画被偷了,损失这么大,我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海奇不知道此时该说些什么,索性让他继续说下去。最后,海奇打断了他:“德·勒赛普斯先生,据我所知,在这段时间内,除了科尔先生之外,没有其他人去过宴会厅,对吗?”
“没有,谁也没去过。”
“科尔先生说你在临摹一幅著名的水彩画,是吗?”
“是的,是惠斯勒的,泰晤士风景画之一。”他回答说,“看,就是那幅挂在壁炉上面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