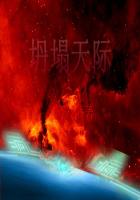海风吹着我的头发和衣衫,黄昏里踽踽而立,追忆往昔之人,总会显出几分寂寥。正自嘲间,往生海走出一个身影,一身玄衣,身姿英挺,不是白泽又是谁。他见了我,略一行礼,并无多言,转身便走。
“站住!”我唤他。
他徐徐转身,恭声问道:“胧音大人有何吩咐?”
“没有。”
“那白泽便告辞了。”
“不许走。”
“更染大人尚有要事交代在下去办,若耽搁了,更染大人怪罪下来,白泽担待不起。还请胧音大人莫要胡搅蛮缠,难为在下。”
“我偏要胡搅蛮缠耽搁你,为难你,你又能如何?”
“胧音大人……”他叹了口气,定定地看着我,我也凝视着他。
“你我之间,似乎变得很陌生。你并非当真厌烦我,不愿搭理我。而是在故意躲我。”我说,“究竟为何?”
“白泽如今已是更染大人的仆从,绝不该再和往日的主子走得过近,这是对更染大人的不敬。”他一板一眼,我嗤之以鼻:“你以为更染会在乎这个?”
他不说话,我穷追猛打:“她分明不在乎,可你却偏要做给她看,希望她在乎。你对我姐姐,到底是个什么心思?”
他并不答我,拱手一揖道:“胧音大人,白泽告辞了!”
“六首蛟为何出现?”我厉声道。
“白泽不知。”他不为所动。
“你是当真不知呢?还是不肯告知于我。”
他沉默。
“狰兽在黄泉路食人,这你可知道?”我换了个问题。
“不知。”
“当真?”
“胧音大人既不信我,又何必多问。”
“我还有个问题。”
“?”
“更染跟你缔契了吗?”这话让他陡然失色,不过仅仅一瞬间他便平静下来,恢复了一贯的冷心冷脸的模样。
“是否缔契,都与胧音大人无关。”
“当年你在望乡台,可希望我与你缔契?”
“陈年往事,多说无益。”他冷心冷脸到底。
我沉默地凝视他,他被我看得别扭,扭过脸去走开两步,换了副语重心长的口气:“胧音大人,你放心。”
“放心什么?”我还未问出来,他已化身一道白光,飞快离开了。
我叹了口气,什么都问了,什么都没问出来。这倒也在意料之中,不过我知道,他说谎了。他曾跟在我身边三万年,脾气秉性我还是了解的,他从不说慌,一来不必要,二来也不屑。不愿多说时多半沉默以对,直到耗尽你的耐性。方才他沉默了几次,他的沉默就是他的谎言。可他跟在更染身边,即便对我有所隐瞒,也绝不敢在更染眼皮子底下放肆,六首蛟的事他不告诉我,更染也肯定知道。既然更染能容忍他,那自有她的道理。
突然觉得有些累,原想着去旸谷问问狰兽的情况,或者去枉死城看看刘嬷嬷。罢了,以后再说,回家吧。正要招朵云,一只熟悉的独脚神鸟向我飞来,稳稳地落在我身边。他蹲下身,方便我走上去。眼神还带着那种要死不活的睥睨和高冷,你一只蠢鸟,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今儿日头打哪儿出来的?竟想到来接我。”我懒洋洋地躺在毕方背上,揉他脖子上的翎羽,他没答话,倒也不避开我。我嘴角勾笑,闭眼小憩。
“大人,到家了。”是松青,我长长地伸了个懒腰,觉得清醒舒适了不少。
“肥妞呢?”我问。
“睡着了。”
“我说呢,良心发现想到来接我。”
“我去给大人准备膳食。”
“不必了!”我突然出手,扣住了右手的拇指和无名指,催动术法。她大惊失色,“大人!”
“别动,这是灵犀缔契。”我收了手,完成缔契。“看看你的左臂。”她伸出手,左臂上已经印下一个“妞”字,我左臂同样的位置也有一个相同的字。看到手臂上渐渐隐去的契印,我不禁想起了右手掌心,那里曾经……罢了,如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了。
“这便是灵犀缔契……大人……您为什么突然……?”她吞吞吐吐。
“我早该与你缔契了,以往是我大意,不曾想过这一遭。”我坐下来,“我与你结下的是两生契,契印间的感应是双向的。你催动契印,我也能感应到你。”
“可你我是主仆,该结单向契才是。”
“既然缔契,自然要缔结出诚意。还有啊,你我共处几万年,我的性子你定是了解的,若说我不信任你,那你是真的冤枉了我。”
“大人……”她羞红了脸,为之前因为缔契的事对我大呼小叫感到不好意思。
“你想知道些什么?今儿你来接我了,我心情好得很,要问什么尽管问吧。”我给自己倒了杯水,做好了和盘托出的准备。
“您的师父,寒川大人,他是个怎样的人呢?”她也坐下来,壮胆问道。
“他嘛……一言难尽。他很强大,此岸之主,女娲伏羲的独子,百万年的老妖怪。很护短。我小时候到处闯祸,都是他不厌其烦替我收拾烂摊子的。”
“大人小时候很淘气吗?”
“岂止是淘气,简直混账。”我自嘲地笑笑。“混账得推陈出新,我如今能安然无恙站在这里,着实是寒川心大,也是我自个儿运气好。”
“那他是怎么去世的?是九万年前吗?”她问这话时有些小心翼翼。
“是。九万年前,上古四大凶兽,帝鸿,梼杌,饕餮和九婴联合一群大大小小的妖怪吃人。黄泉路,枉死城,三途河岸还有奈何桥生灵涂炭,为了平息那场浩劫,寒川用自己,封印了整个战场。”
“我不明白。什么叫用自己,封印了整个战场?”
“寒川使出了魂咒大阵,以自己的魂魄为阵,元神为祭,将整片战场封印了。与其说那是一种阵法,不如说是一种诅咒。用出此招,就意味着同归于尽。”
“他们,我是说四大凶兽,为何要吃人?还有那些精怪,又为何肯以身相随?”
“他们喜欢对岸的气息,尤其是人族,他们是对岸的主宰。而很久以前,上古时期,那些妖兽精怪才是对岸的主导,后来他们不能过河了,无**回,是被对岸抛弃的族类。所以对岸的生魂死魄对他们有致命的吸引力,有些类似于乡愁。那些小喽喽也差不多,不过是群乌合之众。以往只是有贼心没贼胆,有了四大凶兽带头作乱,他们自然一呼百应。”
“为何他们无法过河?为何他们被对岸抛弃?”
“天地有规矩,是这规矩不准他们过河。”
“就这么简单?”她似懂非懂,也给自己倒了杯水。
“就这么简单,他们是神兽,还在对岸的时候生死的轮回周期就很长,导致没有经历过太多的进化和经验积累,虽然一身修为,却并没有多少智谋。行事全凭一己喜恶。就像小胖子喜欢吃你做的奶羹,不给他便鬼哭狼嚎,这是一个道理。”
“我还以为活了百万年的他们行事会更有脑子呢?想不到竟和小胖子一个级别。”
“此岸和彼岸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我也是回来后才明白的,仅凭岁月的无垠并不会累积智慧,只有切实的经验教训才会使人成长。这些恰恰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才能学到,所以对岸百年,往往抵过此岸万年。”
“原来如此。”她胆战心惊地喝了口水。
“一旦被对岸抛弃便不能过河了,孟婆汤没有用,而奈何桥不承载记忆。”我耐心地解释。
“奈何桥真的是通往彼岸唯一的路吗?”
“是,而且是单行道。”我喝了口水,一通问题解释得我口干舌燥。
“那寒川大人把那片战场封印在哪里?”
“忘川。具体在哪里,没人知道。”
“所以白泽……?”
“他修为深厚,行事一丝不苟,更染派他巡视忘川,守护封印。”想起白泽,我心里又泛起一丝不安,不禁又喝了口水。
“我还有一个问题。”她似乎很郑重。
“你问。”
“您为什么不称呼寒川大人师父,而是直呼其名?”
……
“我们一向没规矩惯了的,改不过来了。”我平静地说。我没有看她的眼睛,可我知道她在注视着我。
“是这样。”
“嗯。”我端起杯子又喝了一口,却没注意到,杯中早已空空。
“胖妞该醒了,我得去准备她的尿布了。”她轻轻地说。
“好,你去吧。”
她走出两步又回头说:“大人,你跟我讲这些,我好高兴。”
“是吗?”
“嗯,真想看看到处闯祸的大人,若那时便认识您,那便太好了。”
“哈哈,想多了,你这小身板儿可经不起我戏弄折腾。”
“其实,被你戏弄的那些人或许也是很开心的。”她转身走向长廊。
我松了一口气,这小丫头。其实她问了一个很有水准的问题,我为何不称呼寒川师父,而是直呼其名。这个问题很重要,我自然可以直呼其名,其实,只有我可以直呼其名。我也是经历了许多的艰辛才有了直呼其名的资格:
寒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