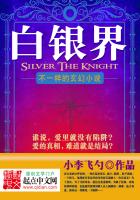如同被注射了毒剂。
白垩痛苦地按住胸口。
——糟透了,这次是个噩梦。
就像把鱼扔到油漆里一样。不,这么形容都显得浅薄。
脑袋无端发昏,突如其来的心悸感化作贯彻神经的幻痛,她下意识理解了,这是本能在悲鸣。
发生了什么?
尚未睁开双眼,亲水性的少女侧耳倾听。
——然后忍不住把按着胸口的手挪开,用来堵住耳朵。
底层是让白垩联想到世界崩坏的背景音。
超出了能用语言形容的范畴,如此宏大。倘若地脉开裂、山峦崩塌、天地颠覆,发出的声音也就如此吧。
并非具体的音波,而是某种更深刻、更抽象、更遥远的东西。使得人心神溃散、头痛欲裂,塞住耳朵都毫无作用,也是理所当然。
但这不是唯一。悲怆的鸣响中,交叠着另一种魔性的呼唤。
对此白垩再熟悉不过了——
那要从她第一次不依靠亲水的义肢,独自深潜大海时说起。
无所谓白天黑夜,天光抵达不了那么深的海渊,于是女孩索性闭上眼睛,彻底融入名为“深海”的魔窟。
但是——
如果说在她的世界,人们怀着恐惧,将那片不可知的领域描述为居住着魔女的洞窟,那么她想必就是魔女选中的使者吧。
掠过大大小小的鱼群。
搭一段巨鲸的顺风车。
再往下就是哺乳动物绝对无法企及的深度了,这是由物理上的结构和密度决定的。
白垩,只顾下潜。
那是她第一次来到这里。
倾听深海的回响。
能听到吗?
升腾的气泡声、水流的碰撞声、生命微小的激荡声……绝不止如此。
听到了——啊,该说不愧是她吗,终于听到了。
那是海洋的歌声。
绝不属于领域之外的歌喉,空灵、幽远,带着淡淡的哀愁,诠释着不可名状的意味。
彼端之音,邈邈回荡。
然而对于寻常的人类来说,其乃绝对的毒药,恐怕触之即死。
现在,浮在背景音之上的,就是这种声音。
但也有些不同。
如果说白垩熟悉的,是那种拒斥人类的歌谣;那么如今传来的,则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变化出了诱惑性的曲调。
拒斥没有改变。
诱惑也属真实。
那么只有一个答案——
白垩睁开眼睛。
依旧是灰白的建筑群,野蛮生长填充了入目可及的全部方向,仅有的缝隙都是精打细算,不过倒也算宽敞。
但这次,视线内多出了密密麻麻的人群。要知道具体的数量,可以把周围的建筑都想象成住满人的居民楼。
而且,地点是水下。
此前一直被忽略的第三种声音终于浮现,并且迅速占据了白垩的心神。
人声。
人的哭泣、喊叫,人的互相安慰、彼此迁怒,人的动荡、人的惨嚎、人的疯狂。
原来如此,今天是毁灭的七日中的哪一天?恐怕是最后一天。
以意识体的形态,她得以一览人类「种族灭亡」级别的灾难——
先是无以计数的穿着防护服的人从房门、窗口、随便什么能出来的地方,哭喊着拼命地涌向外界。有打开喷射装置的在水中乱飞,撞坏了别人或者干脆一头撞到墙上,头盔裂开将海水染红;没打开或者没携带装置的则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疯狂地想要挣开防护服。有自残的、相害的、死滞的、狂躁的、紧拥的、诀别的……老人、小孩、青年、中年,人们各自述说自己的声音,于是人类合唱诉说“绝望”二字。
人类在痛苦。
聆听世界之音也好,倾听海洋之歌也罢,如果两者同时进行,没有谁能再维持哪怕最基本的心智。不是火山崩塌、飓风、地震或者海啸,这是另一种无法理解的自然灾害。即使是能融入深海、豁免一部分伤害的白垩,实际上也是因为没有身临其境,才不至于立刻疯狂。
而这只是最开始。
下一步是物理层面的毁灭。
注意到这件事,是因为原本飘散在海水中的鲜红色,忽然变淡了。接着更多惨绝人寰的叫声响起——恐怕是在全人类的范畴内响起。
海水忽然改变了性质,从培育生命的温床,化作吞噬生命的胃袋。
血红色变淡是因为尸体被消化,叫喊声是因为活人被消化——后者本不至于波及太广,可人们正在极端的疯狂中想方设法地撕开防护服,全然不顾之后身躯一寸寸被吞没的痛楚。
啊,多么恐怖的一幕。
白垩无法克制地流下眼泪。目睹历史上真实的人类灭绝,是单个人类个体难以承受的体验。即使灭绝的是异世界里、无数年前的人类,但他们毕竟如此相似——都皮肤红润、淌着赤红的血,相比之下废墟之民反而是异常的。即使这名执行官自诩见惯了生死,但一想到眼前的事情发生在世界各处,便好像连心脏都难以跳动。
她之前所疑惑的,深海歌声拒斥人类与诱惑人类的矛盾,在一具具身体离开保护材料、暴露于海水中后,也得到了开解。
如同被污染,不知从何时起,人之躯体早已发生了异变。皮肤变得滑腻,泛着靛青色;在连续不止的剧痛中,原本的血肉溶解、蠕动,长成陌生而健壮的流线型肌体。
更关键的是——表面长出鳞片,各处钻出鳍,两臂缩短、两腿并合,末端生出蹼。究竟是退化还是进化?或者都不对……仅仅是在引诱血肉形变的歌声中,某种与深海有着更密切亲缘的怪物扭曲着撕裂人类的身体,好似破壳而出?
大部分人,当然,在这一过程完成前就已死去,被外观表现为海水的消化液溶解得不留任何痕迹。悲惨的却是只蜕变到一半的人们,新生的形态似乎能够抵御溶化,未转化的旧身体却不能,于是白垩看到这部分人扭动着畸形的手脚,肚子被腐蚀出大洞,直露出同样变形的内脏。最终只余下海兽模样的残躯,失去活性后同样免不了消失殆尽的命运。
而甚至,那极少数变形完成的孽生种,依然在痛苦。它们的脸已经是半人半鱼的样子。那眼睛在流泪吗?肌肤在紧皱吗?有发出悲鸣吗?难以辨别。它们从头到脚都丑陋而亵渎,完全有悖于童话中“人鱼”的美好。但白垩就是知道,它们在痛苦。
稀疏的身影们不顾一切地向上方游去,似乎在逃离什么,动作看上去和天生的鱼无异。然而在逃跑的途中,其中的多数又毫无预兆地死去,抛下一片片惨状难言的尸体。
说来讽刺,最后白垩的视线里空空荡荡,只剩无人的灰白建筑,和尚未溶解完的非人尸首了。
世界,无人生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