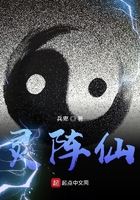玉露原本懒懒的,一听他说玉宽被救出去了,也跟着高兴起来,笑着问道:“是谁救的?”
云山拿出一张字条,递到玉露面前,玉露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宽已平安离沪,望二少爷珍重,切,切。”
玉露问道:“这是哪来的?”
云山笑道:“早起换衣服时,在衣兜里发现的,我竟不知道何时放进来的。若不是玉宽的字我认识,我还以为是谁开玩笑。总算一颗心放下来了。”
玉露轻轻咳了一声,云山忙把她刚刚放下的杯子端起来,放到唇边触了一下,茶水冰凉,他皱了皱眉:“怎么大起早的喝冷茶,一点儿也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子,若这儿使唤人不方便,一会儿我让锦屏过来。”云山觉得住在这儿越来越不方便,何笑伦对他又有成见,认为他不学好,总跟一些激进分子来往,怕惹祸上身,可是若不是玉露固执己见,不肯离开,他又何尝放着家里的大房子不住,挤到这儿。
玉露笑道:“难道烧壶茶我就能累着,只是早起嗓子有些干,想喝杯凉水。”说着拿了茶吊子要去烧水,被云山一把抢了过来,云山的手正巧握到玉露的手上,手心热烘烘的,而玉露的手却凉润润的。
两人都怔了一下,玉露见云山目不转惊地看着他,脸微微一红,低下了头,顺手抽出手。
云山见她扭头向外走去,左手提了壶,伸右手拉住她,把她往跟前拉了拉:“你刚才唱那首歌是什么意思,我倒听了似有满腑的委屈似的,你若有什么话尽可对我说,千万不要暗地里生气。”
玉露听她如此说,忽然从心底真有委屈似的,眼泪漱漱地流了下来,她抽回手回了东屋,坐到椅子上看着桌子上的琴弦发呆,听到身后轻轻的脚步声,知道胡云山跟了进来,云山走到桌子旁,手扶在琴上道:“这两天因为玉宽的关系,或许冷落了你,你不要往心里去,其实我比你更想陪在你身边。”
玉露回头啐了他一口:“玉宽生死攸关,我就是再不明白事理,也知道孰轻孰重?”
云山见她嗔怒的样子,比清冷的样子看了更让人心动,他脸上也渐渐露出笑意,蹲到玉露膝前笑道:“那是说你不是因为我而伤心,难道是想家了?”
玉露拂开他放在她膝盖上的手,被他反手握住,他满脸含笑地偎在她面前:“你若不说清楚,我就不放开你。”
玉露望了他半晌,扑闪闪着长睫毛,云山觉得玉露哪儿都美,特别这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仿佛一抹深遂的幽潭。
与他过份亲近,令玉露心跳过速,血液直冲到她的头顶,她见他眼中闪动着光泽,似要把的眼睛吸进去似的,她垂下眼帘,冷着脸问道:“你即问我,我也不跟你绕弯子,我只是想问你,你如今对我好,是因为当真喜欢我还是另有原因?”
云山笑道:“你这话我就不明白了,对你好当然是喜欢你,难道还会另有什么原因?”
玉露冷笑道:“若我不是姑母侄女,恐怕连你家大门也进不去吧。”
云山原本满脸笑容,慢慢冷了下来,他站起身向后退了一步,与玉露保持一段距离,玉露手一空,抬起清冷的眼睛望着胡云山,见云山的嘴角隐隐掠过一丝讥笑,玉露觉得心也空起来,眼泪围着眼圈直打转,听云山问道:“你这又是打哪儿道听途说,把我看成什么人了,难道我胡云山连自己的主都做不了?”说完气冲冲地向外走去。
玉露头伏在琴弦上,压得琴弦嗡嗡跳动着,她不管不顾地任眼泪流下来,半晌她抬起头,抹了一下眼睛,见琴弦上的泪水,凝结成一个水珠,落到琴身上,慢慢滚动着。她轻轻拨动着琴弦,泪珠随着琴身的振动一点一点地扩大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