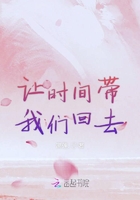从清河县到省城奉天,每天只有上午九点一班火车,还是从隔壁市路过经停的,要是没赶上,就得第二天请早。
光家里出发到县城就得将近俩小时,还不算排队买票的时间,季惟上次坐这个年代的火车还是沾了老天爷的光,她吃不准火车站买票到底是个啥情况,天没亮就出发了。
就这样紧赶慢赶到县城,火车站的售票口也已经排了不少人,有跟她一样去省里的,也有到市里或者其他区间站的,其中好几个还是季惟认识的二道贩子,但是他们这行有规矩,出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只要是同行,哪怕遇上自己亲爹妈也不带打招呼的,所以都互相装作不认识对方。
以前买动车票、火车票,季惟只知道一等座二等座,还从来没听说车票分快慢,她现在能买上的就只有慢车票,三百来公里得要六七个钟头,期间每个区间站都得停,票价三块九毛六。
如果想坐快车,就得从上一站隔壁市或者下一站市里出发,在慢车票的基础上再加“加快费”,因为中间不经停,差不多一半时间就能到。
当然,不论快车票慢车票,季惟能买到的都是硬座票。
要说六七个钟头坐硬座,那还真有些吃不消,以前她出去写生,从来都只要软卧,有一回没票了将就着要了张硬座,才三个小时整个人就酸胀得恨不得就地躺下,而且就她上次看到的情形,硬座车厢里的环境实在不太美好……
她有些犹豫。
售票员拿着她的介绍信不停催促,“你想好没,别耽误大家时间,后面排了好长队呢!”
她一催,乘客们也跟着催,“赶紧的啊,等会儿火车就该来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这乡下来的不懂,大伙儿见谅。”季惟刚要把钱递过去,从她身后伸过来一只手,连钱带介绍信全给收了回来,“小麦,咱们坐软卧。”
季惟震惊回头,就见庄呈昀裹着条白色的羊绒围巾站那儿冲她笑。
“你咋来了!”她忙把他拉出队伍,在人群里到处扫小常的踪影。
庄呈昀掰过她的脸,“我一个人来的,昨晚我跟小常临时搬回了县城,天没亮就到这儿等你来了。”
“……”可别告诉她,就是为了上这儿来等她,才特地搬回的县城,不然小常最近且不愿意回县城呢,就怕虎妞再找上门。
季惟从他手里抽回自己的介绍信,“我上省城办正事儿呢,你快点回去,等我回来给你带礼物。”
要是让小常知道她把庄呈昀一块儿带省城去了,非杀过去把她狗头拧下来不可!
“不会,我给他留了条儿了。”庄呈昀点了点手心里剩下的钱,“上省城要三块九毛六吗,小麦我没有带钱,你再给我拿点儿。”
“买不了。”季惟把他手上那点也抓了回来,“你没有介绍信。”
这介绍信得是个人户籍所在地的行政单位,譬如生产队、街道或者工作单位啥的才能出具,他庄呈昀又不是这里人,就算他有门路,瞅他那样肯定也不知道介绍信是啥,更不可能提前准备上。
庄呈昀不慌不忙从上衣前兜里一枚拇指大小,扁扁窄窄的玉状物,“你在这儿等我。”
季惟眼看着他走向售票口隔壁的办公室,又眼看着他出来,还真就给他弄回两张去往省城的软卧票。
“你这是个啥玩意儿。”她好奇的不得了,庄呈昀随手递给她,“你喜欢就给你了。”
季惟拿过一看,还真是玉,不仅是玉,还是上好的和田籽料,细腻温润,状如凝脂,连她这样的外行都能看出这块玉曾经或者以后价值不菲!
而玉的一端,红彤彤的残余印泥下,刻的是三个极其端庄的正楷反字,印下来,就是“庄呈昀”。
一早知道他的身份,她倒不以为奇,问题是她拿他私章干啥……
掏出手帕揩了揩,给他装回衣兜,“这个我不能要。”
庄呈昀又塞回她手上,“拿着吧,迟早你用得上。”
就因为他这句话,季惟后来一度小心谨慎的做人,生怕自己犯事儿得用到这玩意儿保命,直到几个月后,她才发现一切都是自己太天真……
火车还没进站,季惟就近找了俩位置安顿好自己和庄呈昀。
候车室面积不大,但层高得可观,顶上空落落的,四面白墙,绿漆刷的地脚线,候车椅看起来跟之前她在火车上见过的很像,只是更长更大一些,不少来得早的人,买好票已经开始坐那吃起了早饭,贴饼子馒头啥都有,半密封的空间里,一股味儿。
庄呈昀那么早就从家里出了门,身上又没带钱票,季惟估摸着他得是没吃,从随身斜挎小布包里掏出俩鸡蛋给他,“给,先垫巴垫巴。”
出发的时候,陈翠莲真给了她一担东西,棉衣干粮脸盆饭盒,整得她不像出门去跑业务倒像上西天取经,季惟嫌麻烦,没进火车站就全给收进了画册空间,只剩下这个小布包。
除了几个鸡蛋,里面还有俩大肉包子、一张红糖馅饼和一只装有些许麦乳精的小号玻璃罐头瓶,全是陈翠莲准备来给她路上吃的。
季惟四下看了看,终于在候车室角落的墙上看到“供应热水”四个红通通的大字,底下的长条桌上架了个带龙头的老式带盖金属储水桶,圆柱状,足足有她小半个人那么高,外面包了厚厚一层棉被,她忙拿着罐头瓶过去接了点。
热水一冲,麦香混合着奶香一下子就飘了出来,引来好些羡慕的目光。
“同志,你这喝的啥啊,可真香!”一个蓬头垢面的年轻妇女抱着个奶娃挨过来,两只眼睛骨碌碌的盯着她手里的罐头瓶。
季惟真不愿意跟陌生人搭讪,可看到她怀里那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娃,到底还是没忍心,“麦乳精。”
眼看这都八十年代了,居然还有惨成这样的,母子俩身上的补丁,都快缀成袈裟,连她们那个穷生产队里家庭条件最差的穿的都比这要体面点,年轻妇女背上还背了个破包袱,压得她本来就瘦弱的身子板更显伛偻,一个人带着个娃,也不知道要去哪儿。
年轻妇女舔了舔干裂发白的嘴皮子,小心翼翼指指罐头瓶,“能分点儿给我吗,我身子骨不好,家里又穷,娃都两岁了,连口奶都还没喝过。”
她使劲往季惟身旁凑,把奶娃的皴得发红的小脸送到她眼前。
要是认识的,给她也就给她了,这都不知道大哪儿冒出来的,季惟实在没这个胆,万一“喝出啥问题”,到时候她就是浑身长嘴都说不清。
她摇头,“不好意思,不行。”
“同志,你就行行好,可怜可怜我的娃吧……”
“真不行,要不我给你拿二两粮票,你上外面给娃买点豆浆喝喝吧……”季惟说话就要掏兜,年轻妇女却突然翻脸,凶巴巴撞过她肩膀,“不行就不行!真抠门,喝喝喝当心呛死你!”
“……”看着她扬长而去的背影,季惟无语。
林子大了果然啥鸟都有……
别说是她,就连周围的乘客都看不过,纷纷替她抱不平,一路上全是对年轻妇女指指点点的人,也不知是不是寡不敌众的缘故,刚才还挺嚣张的年轻妇女这会儿却缩着头像个鹌鹑,大伙儿越骂,她抱着娃走得越快,没一会儿就消失在了候车室的大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