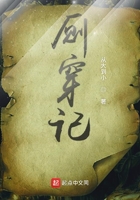天色向晚,扬子江畔,明月早悬。
三五骑士簇着一架皂色马车,朝着渡口疾奔而来。
渡口处,早已泊定了一艘客船,那船极大,长十数米,高两丈余。
船分两层,四壁施窗户,如房屋之制,上施栏楯,采绘华焕,而用帘幕增饰。
“神医,这官船我已包下了,你骑不得马,怕旱路颠簸,且走上一段水路再说!”
浪子燕青翻身下马,凑到马车前,躬身从车上引了一人,先把着上船去了。
那人四十岁上下,生的七尺长短身材,三牙掩口髭须,穿一领靛青绣花素袍,踩一双皂线抹绿软靴,正是江南第一神医安道全。
身后处,自有庄客们算还了车钱,引着马匹,背着药囊跟上。
安道全在建康府颇有善名,又是个恋家的,闻听要到大名府医人,本是不愿的。
可一来被那二百两蒜苗金晃花了眼,二来燕青会说,哄的他心动。
如此众人苦劝了一日,这才开口允了。
眼见的收拾妥当,船身一荡,正待要开。
那厢里,忽听得有人在岸上叫喊。
众人抬眼看时,只见到一个黑凛凛的汉子,带着一人,自岸上慌慌张张赶来。
“休要开船,休要开船,燕小乙哥,等俺铁牛一等!”
船上有眼尖的庄客惊道:
“哎呀,那不是庙里的李大哥么。怎得跑到了这里?”
浪子燕青也认出来人是李逵,心中诧异,忙叫停了船。
黑旋风李逵脚快,到了近前也不见停,熊罴的身躯直直跳将上来。
只听得“哐”的一声,把十几米的大船震个晃动不停。
身后那人动作也不慢,只见对方到得近前,身子稍一停滞,右腿在前,左腿上步,上身下腰后仰,一个鹞子翻身,轻飘飘的落了上来。
船板兀自在晃动不止,那人的身子竟纹丝不动。
“好俊的身手!”
燕青见了,忍不住喝一声彩!正待要问对方名姓,边上的李逵又叫嚷起来:
“小乙哥,你等走的这般急,直叫俺一通好赶,险险错过了!”
燕青看着这才分别不久的黑汉子,诧异地问道:
“铁牛,不是叫你先往大名府了么?怎得又跑到这里?莫不是走错了路?”
“俺铁牛又不是傻的,怎会走错了路?是你那员外主人有难,俺是来报信儿嘞!”
燕青吃他一惊,忙扯住了李逵追问,黑旋风这才道出了原委。
原来,那一日别了燕青等人,李逵独自闷闷不乐,朝着大名府方向走去。
行得半日,看到一处酒肆,他走的正渴,身上又得了燕青给的银钱,便进去要了酒肉来吃。
正自吃着,听到身后的阁子中有人说话,隐约间听不清楚,只依稀听到“这趟定要准备万全,好歹把那卢俊义的武魂弄到手”之类的话。
李逵是个性急的,才听得燕青道了一夜他那员外主人的好,此时听到似有人要害他,如何忍耐的了。
当下大喝一声,提了两把板斧冲撞了进去,挥舞着便砍。
哪成想,阁子里的几人很是了得,见他进来,也不惊慌,随手取了身旁的兵器来挡。
不过才八九个回合,李逵便遮拦不住,吓得仓皇逃了,连两把板斧都没顾上。
好在阁子里的几人急着要走,追赶了他一路便散了,这才逃的性命。
李逵本想着要独个去报信儿,可一则担心大名府没人识得他,二则怕再撞到那拨人,吃他们害了。
这才索性朝着建康府一路追赶燕青他们下来,想着遇到后先把此事说了,再一同去大名府报信儿。
“铁牛可记得那几人相貌?”
燕青听李逵细说了,心中松一口气,又继续问道。
“俺当时性子起了,只顾着进去杀人,那个耐得去看那撮鸟儿长得甚样,只记得当中有一个高的,一个胖的!”
李逵瞪个牛眼,半天也没记起个高低,不耐的说道。
燕青懒得与这粗人计较,看向那与他同来的后生,拱手道:
“这位兄弟,在下浪子燕青,不知如何称呼?”
那后生听了,上前一步拜道:
“小人姓王,排行第六,唤作王定六,是这建康府人氏。因为走跳得快,乡人给个异名作活闪婆。
平生只好赴水使棒,多曾投师,不得传受。见今随老父在江边整治个酒店,权且卖酒度日。”
李逵这时也在一旁接话:“这个兄弟是条好汉,俺追赶到这里时,便是同他家打探得你们消息。
俺看他使得一路好棒,又是个讲义气的,便邀了他一同去救你那员外主人,到时也多个帮手!”
燕青没想到这黑汉子还有这般心思,哈哈大笑。又躬身对着王定六谢了,这才邀两个一同到船内吃酒。
安道全见的进来个黑凛凛的大汉,生的面相凶恶,慌忙起身见礼。
好在这黑厮知道安道全是燕青请去大名府救人的,也敛了性子,一路腆着脸神医哥哥长,神医哥哥短的奉承个不断。
让安道全直以为自己看走了眼,敢情这黑汉子就是生的凶恶,内里却是个乖巧的。
却说这燕青听得这消息为何不急,一是知道自家主人手段,二是那大名府非比寻常府县,卢家也不是甚小门小户,以此并不如何担心。
此时,扬子江边的败苇丛里,两个人正站在船头张望,直到那官船远去,才叹一口气,回了船篷底下。
进入里边,一个火盆烧的正旺,火上烫着半瓮浊酒,边上堆放了几碟碎鱼烂虾。
两个人无心吃酒,各卷了半条棉被,裹着下身,就着盆向火。
半晌后,其中一个叹口气道:
“这河北来的富商凭地阔气,不过是请个郎中,就舍得撒几十贯包那官船,我兄弟两个几月也挣不到那许多。
可惜这等人瞧不上私渡,若不然赶着发回利市,却不快活?”
说话这人二十八九年级,作艄公打扮,身长七尺,黑红脸膛。头上一蓬赤红发,腮边几许焦黄髯。一对三角眼中泛着血丝,满是懊恼!
“哥哥只想想便好!那客人是大名府来的,听闻是河北玉麒麟的心腹。这般奢遮人物出了事,我们弟兄两个安能得脱?
到时亡命天涯不怕,只苦了家中老娘,谁来看顾?”
那人听了,正待和兄弟强辩,又觉得无味,叹一口气,仰身斜躺下去。
他兄弟两个,自幼在小孤山长大,水上练就十分本事,只可惜无人赏识,如今只落得在江边作私渡过活。
平日里若是赌钱输了,他两个也在江上做些黑心买卖。
先由他驾一只船,渡在江边静处做私渡。
有那一等客人,贫省贯百钱的,又要快,便来下我船。等船里都坐满了,却教自家兄弟,也扮做单身客人,背着一个大包,来趁这船。
待他摇到半江里,歇了橹,抛了锚,插一把板刀,却讨船钱。本合五百足钱一个人,他便定要三贯。
却先问自家兄弟讨起,教兄弟假意不肯还他。他便把兄弟来起手,一手揪住头,一手提定腰胯,扑通地撺下江里,排头儿定要三贯。
旁的一个个都惊得呆了,把出来不迭。都得足了,却送客人到僻静处上岸。他那兄弟自从水底下走过对岸,等没了人,却与兄弟分了再去赌。
只这等生意,不是常有不说,惹到了人被找将上来,也少不得受上一顿好打。
且做的久了,兄弟两个的名声也坏了,连带着这正经私渡买卖都冷清了,常常十天半月捞不到一个客人,日子愈发艰难。
如今兄弟两个都到了年纪,却连个上门说亲的也无,直让老娘也跟着遭罪。
兄弟两个都有心事,相对半晌无言,忽听得棚外有人喊:
“张家昆仲可在?快些回家去,你家老娘似是背疾犯了,倒在地上直喊疼,吓死个人!”
兄弟两个大惊,出外看时,见是邻人王二。
央着这人帮忙看了船,两人不敢停歇,火急火燎的朝家中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