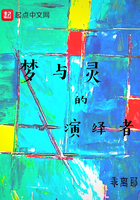小说创作的实与虚(四) 文\刘庆邦
我所说的小说创作的三个层面,是步步登高的三个层面。但三个层面并不是孤立的,截然分开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紧密联系在一起,最后通过完成的小说,浑然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
从实再到虚,是一个比较高的层面,要达到这个层面是有一定难度的。有的作家点灯熬油,苦苦追求,都很难说达到了这个层面。在我的有限的阅读经历中,能让我记起的达到“太虚”境界的小说不是很多。如果让我推荐的话,外国作家的小说,我愿意推荐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契诃夫的《草原》。中国现代作家的小说,我愿意推荐鲁迅的《阿Q正传》和沈从文的《边城》。而我国当代作家的小说呢,我觉得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刘恒的《虚证》、还有阎连科的《年月日》等,在虚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特别是沈从文的《边城》,我看了不知多少遍。每看一遍,都能激起新的想象,并得到灵魂放飞般的高级艺术享受。《边城》是经典性的诗意化小说,可以说整部小说都是用诗的语言写成的,堪称一部不分行的诗。朋友们可能注意到了,我所推荐的以上几篇小说,之所以达到了小说创作的高境界,是它们都具备了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小说是道法自然的,与大自然的结合非常紧密,都从大自然中汲取和借喻了不少东西,从而使小说得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雨雪之润泽,实现了和谐的自然之美。第二,小说从大面积的生活中抽象,抽出一个新的、深刻的理念,然后再回到生活中去,集中诠释这个理念,完成了对生活的高度概括。第三,这些小说的情节都很简单,细节都很丰富。它们不是靠情节的复杂多变取胜,而是靠细节的韵味引人入胜。沈从文在自我评价《边城》时就曾经说过:用料少,占地少,经济而又不缺少空气和阳光。第四,这些小说都在刻画人物上下足了工夫,人物不但情感饱满,而且有人性深度。
我自己的小说,不敢与上面的小说相提并论。但当我逐步确定了虚写的意识之后,在虚写方面也下了一番工夫,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如果让我举例的话,我愿意举一些自己的短篇小说,如《梅妞放羊》《响器》《遍地白花》《春天的仪式》《红围巾》《夜色》《黄花绣》等等,大约能举出十多篇吧。我所列举的这些篇目,都是短篇小说,没有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我自己觉得,在小说的务虚方面,我写短篇小说做得稍好一些。还有,我所举的这些例子都是农村题材,没有煤矿题材和城市题材。这是因为,我离开农村已经多年,已与农村生活拉开了距离。我所写的农村生活的小说,多是出于对农村生活的回望。这种回望里有对田园的怀念,有诗意的想象,也有乡愁的成分。近处的生活总是实的,而远方的生活才容易虚化,才有可能写出让人神思渺远的心灵景观。
我们对小说的虚写有了理性的、清醒的认识,是不是说以后每写一篇小说都能达到虚写的效果呢?我的体会是,不一定。因为现实像地球的引力一样,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和纠缠力,现实像是一再拦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写它吧,写它吧,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被现实牵着鼻子走,并有可能掉进实写的泥潭。反正我并没有完全摆脱现实的诱惑和纠缠,加上抽象能力有限,不能超越现实,有些小说仍然写得比较实。为了给自己留点儿面子,这里就不举具体的例子了。
那么,在《神木》这篇小说里,从实又到虚做得怎么样呢?这个层面体现在哪里呢?是否做到了从实又到虚的转化和升华呢?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从实又到虚的转化和升华中,我还是做出了自觉的、积极的努力,给小说揉进了一些虚的东西,使虚的东西成为推动小说向前发展的动力,并最终主导了这篇小说。在这篇小说当中,虚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理想,是我的理想,也是作为一个作家应有的理想主义。我一直认为,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复兴,包括个人的前途,都离不开理想的引导和推动。理想好比是黑暗中的灯火,黎明前的曙光,一直照耀着人类前行的足迹。作家作为人类精神和灵魂的工作者,工作的本质主要是劝善的,是改善人心的。他有时会揭露一些丑恶的东西,其出发点仍是善意的,是希望能够消除丑恶,弘扬善良。所以作家应始终高举理想主义的旗帜,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史铁生曾经说过:现实注定是残缺的,理想注定是趋向完美。现实是常数,理想是变数。
在现实生活中,那两个拿人命换钱的家伙,直到东窗事发,才停止了罪恶行径。我不能照实写来,那样的话,就显得太黑暗了,太沉闷了,也太让人感到绝望。我必须用理想之光照亮这篇小说,必须给人心一点希望。从全人类目前的现状来看,在工业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头脑高度发达的人类似乎已经无所不能,人类能上天,能入地,能潜海,还能克隆牛,克隆羊,克隆人等。可以说人类在科技层面是大大进步了,甚至每天都有发明创造,每天都有新的进步,仿佛整个地球都容不下人类了。可是人的心灵呢?人的灵魂呢?是不是也在随着进步呢?大量事实表明,人心进步一点非常艰难。科学技术的进步有时不一定能改善人心,反而把人性的恶的潜能激发出来,导致资源争夺不断,局部战争不断,汽车炸弹爆炸不断。这时作家的责任就是坚持美好的理想,提醒人们,不要只满足于肉身的盛宴,还要意识到灵魂的存在,让灵魂得到一定关照,不致使灵魂太堕落。我给小说起名《神木》,除了早期有些地方不知煤为何物,把煤称为神的木头,也是想说明世界上任何物质都有神性的一面,忽略了物质的神性,我们的生命是不健全的,生活就会陷入愚昧状态。有了神性的指引,生命才会走出生物本能的泥潭,逐渐得到升华。
在《神木》这篇小说中,我的理想体现在有限制、有节制地写了其中一个人的良心发现和人性复苏。一个人急于把骗来的孩子打死,另一个人却迟迟下不了手。这个人也有孩子,他的孩子也在读书。由自己的孩子联想到被骗来的这个孩子,他对这个孩子有些同情。他想,他们已经把这个孩子的爹打死了,如果再把这个无辜的孩子打死,这家人不是绝后了嘛,这样做是不是太残忍了。所以他找多种借口,一次又一次把打死孩子的时间推迟。他说,哪怕是枪毙一个犯了死罪的死刑犯,在枪毙之前,还要给犯人喝一顿酒呢,他建议让这个孩子也喝一顿酒。酒喝过了,他又说,这个孩子长这么大,连女人是什么味都不知道,带他去按摩一次,让他尝尝女人的味吧。于是,他们又带孩子去了矿区街边的按摩店做了按摩。至此,这个人可以把孩子打死了吧。按照这次分工,这个人负责把骗来的人打死,另外一个人负责和窑主交涉,要钱。可是,他还是不忍心把这么一个纯真的孩子活活打死。后来,他在井下做了一个假顶,也就是用木头支柱支起一块悬空的大石头,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让石头掉下来,把这个孩子砸死。这样在不知情的人看来,这个孩子是被冒顶砸死的,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死的,他心里会好受一些。在他冒着危险做假顶时,另一个人不但不帮忙,还站在一旁看他的笑话,讽刺他,说他是六个指头挠痒,多这一道。他把假顶做好后,另一个人来到假顶下面,说要试一试假顶做得怎样。他说可不敢试,弄不好,他们两个就会被砸在下面。说着,他用镐头对另一个人甩了一下。这一甩,尖利的镐尖打在了另一个人的耳门上,耳门那里顿时出了血。另一个人以为对方要把他打死,换钱,两个人在假顶下扭打起来。扭打中碰倒了支石头的柱子,石头轰然而下,反而把两个害人的家伙都砸死了。临死前,做假顶的人对孩子喊,让孩子跟窑主要两万块钱,回家好好上学,哪儿都不要去了。结果是,孩子上井后对窑主说了实话,窑主只给孩子很少的一点路费,就把孩子打发了。直到最后,我都让孩子保持着纯洁的心灵,没让孩子的心灵受到污染和荼毒。这也是我的理想所在。
导演李杨在把《神木》拍成《盲井》的过程中,下了不少矿井,付出了不少艰辛,我应该感谢他。但我对电影也有不满意的地方。比如:他让两个家伙嫖娼之后,在歌厅里大唱“掀起社会主义性高潮”,这在小说里是没有的,我认为没有必要。再比如:电影收尾处,他让孩子说了假话,得到了两万元赔偿,这也有悖于我的初衷,我的理想(待续)。
[ 作者系北京作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