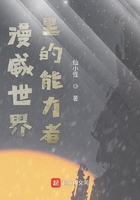“禾子,你真爱说笑。萧泫也就算了,他无依无靠,你照顾着这个弟弟我没话,但我哪用得着你操心呀?现在全家把我当佛似的供着,你还嫌我不够心烦?我巴不得回到以前在C市的生活。虽然平淡但也刺激有趣,”或许是我已经习惯了那样的生活吧,突然告诉我我的幸福又回来了,只会让我措手不及,“对了,你们这次来这就为了看我吗?”
禾子说:“其实不是。陆烁奇他爸重振家业,开了个Party邀商业翘楚聚一聚。其实……霄的爸爸龚伯伯也来了。”
我一惊,瞪圆了眼:“什么?龚伯伯也来?那么说……那么说他也会在Party上出现?”
“他?”禾子萧泫齐道。
“是啊,莫霄啊。”
“什么?”
是的。禾子和萧泫也认为我疯了,精神出了问题,两人皆瞪着圆圆的眼睛看着我,先是很大声地说出了“什么”,之后一冷静便低了音,禾子有些顾虑地问:“那个……万俟琪……你是不是……是不是因为那个……所以……”
萧泫看起来也有些担心。
我笑得很自然:“没有。禾子,萧泫,你们两个必须很认真很信任地听我说,好不好?保证?”
一致地点头。
“其实半个月前,我离家出走了。”我还以为他们听到这里会立即打断我的话,但事实证明,他们没有,似乎他们更感兴趣的不是我是否出走过,而是听与那两个关键字——“莫霄”有关联的事。
他们期盼的眼神告诉我:快点说下去。于是我说:“我去了新加坡。在樟宜机场坐巴士去后港,经过淡滨尼的时候,看见了图书馆内的——莫霄。”
他们依旧以同样的眼神看着我。我只好说:“我已经说完了。”
“啊?没有然后吗?”禾子忽地反应过来,伸手探我的额头,“万俟琪……你……是真的没事吧?”
“琪琪姐……”萧泫更担忧了。
我往被子上猛力一拍,兮兮吓得跳下了床,躲在一边。“喂!你们到底要不要相信我啊!”
“这个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啊。我……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我们得相信科学,”禾子慎重地拍了拍我的肩,“万俟琪,你要振作啊。霄的事我也很难过,但我也不至于会变成……所以……看开了就好。你现在已经失去了容貌,不可以再让精神还——”
“停!”看也不看伸手堵上她的嘴,“既然你们不相信我,我也没办法。你们两个可以出去啦,到A市随处去逛逛,我嘛,要休息了,好累啊……”
说着,躺平了身子,被子一拉给埋进去了。这时,兮兮见“战争”已经平息,又从角落里飞奔过来,一跃上床,钻进了被窝。
禾子萧泫也没法子,虽然嘴里仍在碎碎念些我听不到也听不懂的话,但还是乖乖地出去了。关上门还不忘留两句:万俟琪,你千万要挺住噢;琪琪姐,撑下去。
我真是欲哭无泪。我又不是得了末期癌症,挺什么,撑什么啊!
兮兮,还是你好,总是无声地支持着我。啊?不是无声?对哦,你会叫的。好吧,谢谢兮兮一直这么“有声”地支持我。
本来听着外面乱哄哄的一通,一点睡意都没有,本想就这样躺着直到天亮,看看我这个房间能不能看到日出,但没想到没多久,不知为什么就突然眼一闭找周公去了。
我想,我应该是梦到他了,不大确定。
他坐在一棵长满花的树上,靠着树枝仰望着天,神情淡然。像是他在望天,又像是天在看他。过一会儿,眉心皱成了一块儿。
你在愁什么呢。可以告诉我吗。
如果可以,我想分担一些你的忧愁。仅是一点点也好。
我想过去,慢慢走近他,走进他所在的世界,伸出我的右手为他抚平那丝愁容,然后说:请你以后不要再悲伤了。
三米。
两米。
一米。
半米。
就快到了——站住。被人喊住了。像是被施了法术,动弹不得。之后便眼睁睁地看着眼前那颗花树上的他连同树一起快速地向后方移去,变成了一个黑点。
我的面前出现了一盘棋。棋的一旁是我,另一旁是一位长着胡须的老伯伯。我记不清他穿什么衣服了,只知道好像不是21世纪的人。
我说:“你是谁。”
他摇摇头,指示我坐下。然后又指了指棋盘,应该是在说让我陪他下盘棋。我没有坐下,也没有答应,只是摇摇头说:“我不会下围棋。我只会下五子棋跳棋和飞行棋。”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自己的梦境,所以是由自己的意识控制的关系,我这么说了,他也没反对,说:“那就下五子棋吧。”
可我还是摇摇头:“不了。其实我不会下棋,不管下什么棋都会输。五子棋很费脑,我不喜欢玩,输的只剩下四颗棋子的时候,心里很不舒服。”
“为什么你会认为自己不管下什么棋都会输?你是指你以前从来没赢过吗?可是你又不是预言者,你又怎么会知道这以后,你会一直输呢?没试过你怎么敢如此断然?”老伯伯捋了捋胡子。
啊,这老伯伯怎么那么像电视上那些专门为主角解答问题的人呢?难道——老天托梦给我?想要指示我些什么?
“这……”我对不上了,“这我确实没想过……我很害怕面对。”
“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莫名地害怕啊。”
“所以你才会不断地失去,”他说,“你不去试着做一件事情,所以永远只是失败。但如果你去做了,就算失败,那也是胜利。每个人都是一个美好的织梦者,如果你不去织梦,何来成功可言?空手而得的例子,是少之又少。”
我否认:“不,我做了。我做了非常多的事,然后我知道了我很失败。我永远活在别人的保护膜里,总是给别人带来身体的负荷,成为他们的累赘。如此的我为什么还要去做一个织梦者,肆无忌惮地用别人的生命来完成自己的梦?这样而得的梦又有什么意思可言?”
“或者……你该换另一种想法来想那些问题。”
“什么想法?”我很好奇。
“如果你已经拖累别人,而且是许多,但你仍旧没有完成自己的梦,并且惧怕现实的你一味地选择逃避,抛弃那个未完成的梦。那么,你可以告诉我,那些给你当作过桥石的被你拖累的人们该怎样呢?他们的付出你该怎样回报呢?”
回报……是啊,我该怎样回报……“我……爷爷?爷爷你人呢?爷爷!”到处转圈,却发现老伯伯早已没了踪影。
醒来的方式依旧是恐惧地睁开了眼。为什么是恐惧?
因为后来的时候,萧雨和圣出现了,他们并不知指责我,而是一言不发地盯着我看,令我全身发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