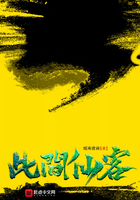悬挂着日本武士道旗的黑色汽车耀武扬威地行驶在上海租界繁华的街道上。
淞沪会战刚刚结束,虽然上海南站和上海市区遭到日军猛烈空袭,大量建筑物化为乌有,无数中国同胞惨死在日军枪炮之下。但日军不敢与西方列强国家发生摩擦,英法租界并没有受到战争波及,保住了暂时的安宁。
穿着日军士兵军服的司机把车开得很快,脑袋探出车窗外,对前面的行人不耐烦地喊:“让开,让开,快点儿让开!”
拉着洋车的车夫,怀抱孩子的妇女,挑着扁担的商贩看到汽车飞速驶来,纷纷惊慌失措地避让,传来阵阵尖叫与孩子的哭声。汽车所过之处,瓜果蔬菜散落一地,一片狼藉。
等汽车远去,人们才开始谩骂:“这帮王八蛋的日本鬼子,不得好死!”
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日本军官来回来张望,手里紧紧地握着手枪。
当他回过头看到坐在汽车后排的日本驻上海特高课副课长波多野三郎正闭目养神,肥头大耳,身上肥肉随着汽车的颠簸上下颤抖,双手自然地搭在军刀的刀柄上。他张了张嘴,欲言又止。
波多野三郎无视车外乱象,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看到军官一脸紧张地样子,皱皱眉头,“高岛君,你太紧张了。现在上海已经没有国民党军队。他们都逃往了南京,而南京政府逃往重庆。剩下的那些小鱼小虾也不足为虑。”
高岛还是有些担忧地说,“课长,现在局势还不稳定……”
话还没有说完,波多野三郎就打断了高岛地话,“你是说会有人刺杀我们?”
高岛点点头,“据可靠情报,国民党军队逃往南京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和中共南方局都派出特工秘密潜入上海,要对帝国高级长官和亲日分子展开暗杀行动……”
“高岛,你是大日本帝国的武士……”
“课长,我不是那个意思,身为日本武士,我不怕危险。如果我们被袭击,那么英法租界地无良报刊肯定会大肆鼓吹帝国的覆灭。而那些报社都受英法领事馆的保护,更让亲日分子对帝国的能力产生怀疑。”
张啸林府邸前面的大街上空无一人,三四十名持枪枪手站在公路两边。如果有人误入街上,便的枪手提枪威胁:“绕回去!再不走把你当奸细抓起来。”
一辆桔红色汽车驶来,被枪手拦住。
司机探出脑袋,大声喊道:“你们凭什么封路……”
又两名枪手走了过来,故意把衣服掀开,每人的腰都别的两把手枪,其中一人冷冷一笑:“今天这路你们过不了,在上海还没有人敢硬闯张先生设的卡!”
司机并不害怕这些枪手,“你们可知道这是谁的车,车上坐的是谁,张啸林也太嚣张跋扈了……”
枪手们一听,同时把枪掏了出来,指着司机,“张先生的名字也是你叫的!”
汽车里坐着人不知道说了什么。司机没现再说话,启动汽车,调头回去了。
枪手们看着驶离的汽车一脸得意洋洋地说:“小瘪三,敢跟我们叫板。”
另外一名枪手盯着汽车,疑惑地说:“这好像是周世海的车……”
桔红色的汽车刚刚消失在枪手的视线里,波多野三郎的坐驾就驶入街道。高岛看见街道上的枪手大吃一惊,马上掏出了手枪。
波多野三郎立刻拦住了高岛,“高岛君,别紧张。这是张啸林欢迎我们的仪式。”
街上的枪手看到日本汽车,立刻跑进张啸林的府邸,对早已经在台阶上等候地一群人喊:“来了来了,波多野课长的车到了。”
穿着暗红色长衫地张啸林与身边的几个人立刻交头接耳,脸上还挂着一丝激动。
汽车停在别墅正门的台阶下。
张啸林等人快步走下台阶。
高岛先下了车,拉开汽车后门,波多野三郎从车上下来,司机把车开进车库。
张啸林远远地便伸出胳膊,紧握住波多野三郎地手,激动地说:“波多野课长,您屈驾来我张公馆,真让我这小地蓬荜生辉呀。”
波多野三郎没说话,只是象征性的握握手便松开了,开始打量张啸林的府邸。
张府的设计非常豪华,有假山有喷泉,有花园有草地。眼前的建筑是传统的中式风格建筑,而后排有欧洲风格。
张啸林有些奇怪,小心地问道:“波多野课长?”
波多野边看着张公馆边说:“张先生,您的家是我见过最豪华的。我在家乡名古屋从来没见过。这次来到支那,才发现自己的见识是多么的少,原来支那也是这么繁华的地方。”
口口声声说着支那,赤裸裸的歧视。
可以张啸林为首的汉奸走狗不以为然,就算心中不悦也不敢表现出来。
张啸林点头哈腰地说:“波多野课长,过奖了。”
波多野三郎这才回过头,“张先生,谢谢您对大日本帝国的信任。”
“我是相信帝国的实力。这位是?”张啸林看向高岛。
“这位是上海宪兵队队长高岛少佐。高岛君是我的朋友,他明明可以胜任更高职务。但为了我们的友谊才来到上海。”
张啸林又与高岛握手,“高岛少佐,您好!波多野课长,高岛少佐,里面请。”
众人纷纷让开路,跟在波多野三郎和高岛的左右进了别墅。
刚刚封街的那几十名枪手任务完成,也就各自忙各自的事情去了。拦车的那两名枪手见人都走了,其中一个人便说:“人都走了,我们也找个地方喝点儿酒。为了小日本儿这几天兄弟我都没睡过好觉。”
另一个人有些害怕地说:“我们半路溜号,让刘管家知道我们可就惨了。”
“怕什么,现在刘管家正忙着招呼小日本儿,哪有时间管我们。我们喝两杯就回来,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
“走!”
偏僻的弄堂(上海把胡同叫弄堂)窄小且狭长,昏暗且潮湿。
不远处,一块黄布做成的招牌随风飘动,上面写着个酒字。
酒馆不大,又地处偏僻,大厅只摆着七八条桌子,柜台后面的酒柜上放满了大大小小的酒坛。
两人坐在小酒馆里要了两壶酒,吃着蚕豆一口一口的喝着。
因为没到正时,酒馆里冷冷清清。店小二坐肩膀上搭着白色毛巾坐在凳子上打盹。老板坐在柜台前“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
“紧喝两口吧,一会儿小日本走的时候,刘管家找不着我们,不但得挨骂,还得扣钱。”
“现在张府也是越来越扣门了,刚来的时候一个月给30块钱,现在降到20块钱。这样下去,恐怕酒钱都不够了,还得养家糊口。”
“你说这府里走私军火,贩卖烟土,开着赌场舞厅的,一天挣的钱够给我们发十年的工钱,至于连我们这点儿钱都扣吗?天天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死了才给100块钱。我们现在的命就这么不值钱?也不知道张先生是怎么混到今天这样,老子是没那机会了。”
“别说了,说多了我都不想在这待了,喝!”
“喝!”
突然,阵阵刺耳的刹车声响了起来,酒馆里的人都纷纷抬起头向外看去,两辆汽车一前一后停在酒馆门口。
从车上下来八个戴着绅士礼帽,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年轻人。
两个人带头冲进酒馆,后面跟着几个人都提着手枪。
酒馆老板和店小二见势不妙,连忙往酒馆的后堂跑。来人并不理会,径直走向那两名封街的枪手。
枪手明白这些明显是冲自己来的,刚站起来。几个人就把这两个人给按在桌子上,“别动!再动老子一枪打死你,打死你跟跟踩死一只蚂蚁没什么不同。”
“你们什么人?”他们开始挣扎,脑袋用力扭到一边,想看清来人的长相,“告诉你们,上海滩还没有人……”
他的话还没说完,站在他们前面的黑西装提起酒瓶就砸在他的脑袋上,接着黑洞洞的地枪口顶在他的脑门上,“闭嘴!”黑西装转过头问身后一个人,“是他们吗?”
“就是他们俩。”
黑西装又问:“你是张啸林府上的阿堂,你是阿毛?”
阿堂面对枪口,虽然不敢动弹,但却恶狠狠地说:“你敢动我们……”
“你是张啸林府上的阿堂,你是阿毛?”黑西装用枪口戳着他的脸。
“张先生的名字也是你们叫的……”
“硬骨头!”
黑西装说完,几个人架起阿堂和阿毛,对着肚子就猛打起来,打着他们二人哇哇大叫,接着阿堂的的肚子上被踹了一脚,砸散了身后的桌子。
阿毛被几个人抬起,扔到了柜台上,又砸到后面的酒柜。
酒柜子上的酒瓶“哗啦哗啦”地掉到地上。
几名黑西装又住起阿堂阿毛,连踢带踹地塞进汽车里。
领头地黑西装走到门口,扶了一下帽子,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银元扔到地上,“老板,还不出来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