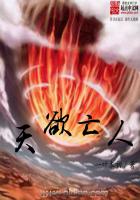都说他们这个借来的婚房不吉利,曾经吊死过一个男人。那是“文革”的时候,那个男人受不了批斗、游街、“坐飞机”的折磨,抛下妻子儿女管自己走了。从那以后,邻居们说这个房间经常闹鬼。麦瑞在夜晚的梦里也能看见一根白晃晃的绸带,然后一个男鬼在屋梁上飘来飘去。有时这个男鬼还会发出一些声音,像“文革”中的口号;有时却是一阵脚步声,重重地从屋顶的每片瓦上压下来。麦瑞并不感到恐惧,她觉得许多时候这个像坟墓一样的家里,倒是因为有了这个男鬼,才让她滋生出许多遐想。说真的,与其面对人,还不如梦见鬼。
麦瑞曾经是处女,现在仍有一颗处女的心。她离婚后,已经像一个处女那样生活很多年了。说来奇怪,在有婚姻的时候她总是在天花板下被人爱、被人占有。可如今要想谈一个恋爱都困难,那些男人见到她不像从前那样信心十足、善于表现,而是变得怯懦、顺从和逃跑。麦瑞觉得自从她父亲算起,她就没法与男人的关系处理好。如果说她依然美丽动人,那么她残破的心灵郁结在心底的创伤,已经像茧一样厚。汤惠琼当然不会知道这些,她并不知道一个女人经历过许多之后,就不会爱也不喜欢爱了。
这会儿麦瑞坐在沙发上。她曾经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坐在这里,日子就艰难地从岁月中挣扎过来了。应该说,一个人的生活常会有一种苍凉悲号的黑暗,那黑暗是她不愿触动的记忆。她有时会想,等到她成了一个衰弱的老女人,逝去的年华留在她心中的将是什么?仇恨抑或是爱情的甜蜜回忆?虽然她爱过,却到后来发现她爱的其实是自己身体内部滋长出来的爱的火花与激情。这种激情似乎与爱情的甜蜜还有遥远的距离。因此她想没有甜蜜的爱情,心里纵然有很多仇恨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仇恨也已经不再是仇恨了,而是成了一种美好的记忆。
麦瑞记忆最深、感觉最好的就是与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菲力浦的网上之恋了。尽管他们从未谋面,可麦瑞还是不知不觉地把情感投入了进去。菲力浦并非洋人而是英籍华人,确切些说是澳门人。麦瑞想起来那是一个晴朗的黄昏,她的窗外花园里红艳欲流的玫瑰上正停留着一大片晚霞,麦瑞喜欢看晚霞,晚霞那一抹绚烂的明亮,仿佛把她孤独黯然的内心照得通彻明亮起来。这时麦瑞心情很好,她为自己的晚餐做了油豆腐、鸡蛋烧猪肉,油爆虾,还有一只青菜腐皮汤。她就坐在窗边,在晚霞的映照下她一边喝着一小杯加州葡萄酒,一边品尝着自己的厨艺。组合音响里轻轻地放着世界三大男高音帕瓦罗蒂、多鸣高、卡里拉斯的歌。餐桌上还有一大叠当天的报纸和一些杂志。麦瑞通常总是饭后坐在餐桌上读报,读完报再收拾洗刷碗筷。
然而那天的晚霞实在是太美丽了,美丽的晚霞是可以做诗做文章的。于是麦瑞来不及洗碗,便先打开了电脑。她在电脑中写道:“晚霞的秉性是最能体现生命本真的实质,把生命演绎得最完善、最彻底、最炉火纯青了。但天底下没有永远不落的太阳,尽管它十二万分地留恋、十二万分地不愿把半边燃得彤红的脸贴在山头;向大地、向人类投来凄楚的一瞥,可它那颗普照苍生的头颅,终究要沉下去的。此刻,我读懂了晚霞为什么要向大地泣下血泪,为什么要向群山唱起哀歌……”
麦瑞写完这段话,仿佛对美丽的晚霞有了交代,心情十分舒畅。她想这时候如果有一个人与她聊聊天该多么好?然而大家都很忙,麦瑞的同事学生和朋友都有家室和恋人。麦瑞从不找他们聊天,他们也很少给麦瑞电话。麦瑞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一个真正牵挂她的人,如果有也都是短暂的利用关系。麦瑞知道网上有聊天室,但她从没有进去过。她觉得在网上与陌生人聊天,搞不明白他们的性别年龄和身份,什么东西都是虚拟和假的。所以麦瑞也没有兴趣和心情,而电子邮件倒是与人交谈的一个好地方。可是麦瑞的邮箱大多是广告邮件,偶尔有信也是她的学生问她功课的事。
然而今天麦瑞忽然发现有一封陌生人的邮件,这个陌生人也许写错了地址。他的信是写给一个叫许子刚的男人,似乎在谈论一些哲学话题。麦瑞不用偷窥就看了别人的信,觉得很快乐。于是这天晚上麦瑞的工作效率很高,她正在翻译一部长篇小说。除了教学,很多时间她都是靠翻译小说来打发的。一般她每天工作到凌晨两点,然后吃夜宵洗澡,躺下睡觉通常是凌晨三点了。好在她一周只去学校三个半天授课,那三个半天又都在下午,所以睡到中午是没问题的。
现在麦瑞从学校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看邮箱。其实她从前并不是每天都看邮箱,只因为心里想着那个陌生人的信,想着信中一些闪烁着智慧的句子。然而邮箱里那封陌生人的信不知什么时候被她删掉了,而且是永久地删掉了。麦瑞觉得有点遗憾,她确实是还想再看看的。
上午她还没有起床的时候,接到汤惠琼从杭州打来的电话。汤惠琼总是打对方付费电话。她知道有这种付费方式后,给麦瑞的电话就多了起来。麦瑞知道她有时候纯粹是无话找话拉关系,日后好把她的儿子送到美国来读书。麦瑞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助人为乐的事她做过不少。人活在世界上,互相帮助也是必须的。只是麦瑞如今已没有什么要别人帮助的事,从前她也知道一切要靠自己。
昨天她的一个同事在办公室门口拦住她,悄悄地与她说:“我看你一个人的生活太孤单了,我的一个学生看上了你,他是西班牙裔的小伙子,就是比你小15岁,小一点没关系吧?”
“当然没关系,只是我不喜欢找洋人。”麦瑞说。
麦瑞曾经婉拒过不少替她做红娘的人,如今依然婉拒着。她觉得恋爱的事最好是自己遇上,自然产生,一切人为的撮合总归会有点牵强。那晚临睡时,麦瑞又打开了邮箱。嗨,那个陌生人的信又来了。麦瑞高兴着,急急地打开网页。陌生人还是写给那个叫许子刚的男人,不过这次他落款:菲力浦。麦瑞从信中知道菲力浦与许子刚都是澳门人,菲力浦在英国剑桥大学做教授,而许子刚在香港大学做教授。麦瑞觉得菲力浦的邮件两次误发到她的信箱,如果不回个信,那么他还可能再发过来,这样看别人的信虽然心情快乐,倒是觉得有点不太好。于是麦瑞给菲力浦写了封信,也在信中谈了她对哲学的喜欢。
麦瑞开始并没有想到给菲力浦发信后,会谈上了网恋。网恋本来是虚幻的东西,可进入了麦瑞的生活就变得真实起来了。麦瑞一天要写七八封信,当然是一来一往的。麦瑞觉得这样很充实,既有了恋爱的感觉和激情,又不用像现实世界中的恋人那样与她形影不离。她依然是独立的、自由的,倒是填补了精神上的一些空虚。于是她的灵魂有了一个着落点,她觉得这就够了。然而,作为男人的菲力浦,仅仅在网上虚拟的世界里来往交流是远远不够的。他要飞到美国来,飞到麦瑞的身边来,把虚拟的世界变成现实。现实是什么呢?是肉欲、是露水夫妻抑或是浪漫的精神恋爱的终结?
麦瑞不愿想得太多,到她这种年龄感性和理性都能拿捏自如。她心里明白不能再陷进去了,陷进去到后来痛苦与受伤害的肯定是她。因为她知道恋爱中的男女,往往是女人用心男人用情,而男人的情很多时候又是不大靠得住的。网上之恋,先多一份怀疑和不信任,应该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法。于是麦瑞思索了两天后回信说:“但愿永远做网上的朋友,不下站。”
麦瑞非常清楚,她想拥有一个与她生活在一起的爱人已经很难了。于是她想生活中没有男人的女人是冷清的、寂寞的、但内心并不一定是孤独的。虽然这样的女人可以说是一种残缺,但残缺也是美丽的。
2004年2月18日
载2006年1月《滇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