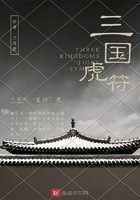“啊!是他发来的。” 杨彩霞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起来。
杨彩霞没想到吕树冬会给她发短信,关心她的病。这短信,让她倏地感到了一种温暖。于是她不顾指关节疼痛,给吕树冬回短信。虽然只十几个字,却让她在手机小小的字盘上,花费了不少时间。这是她有了手机后,发的第二个短信。她没想到短信的“嘟嘟”声,可以是心灵的桥粱。发完短信,她仿佛感觉病好了很多。躺在床上,踏实多了。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短信又来了。这一回杨彩霞一听到短信,就兴奋起来,病也忘了。她拿起手机,急急地看短信,心“扑通扑通”地跳着。“有没有退烧,如果没有退烧,去医院吊点滴。保重!”吕树冬的短信,就这么短短几个字,却让杨彩霞感动极了,就像一座空寂无人的孤岛,突然飞过一道彩虹。杨彩霞的双手哆哆嗦嗦地回短信:“好吧!我这就去医院吊点滴,谢谢!”
杨彩霞起床,头仍然很疼,走路摇摇晃晃,全身发软。但她想一定要去吊点滴,不能再拖了。其实若吕树冬不来短信,她起码要拖到下午才去。现在杨彩霞稍微梳洗后,出门了。为了省钱,她搭公车。从家走到汽车站,本来五分钟的路,她走了十五分钟。她走走停停,走不动了就一屁股坐在行人道边的石凳上。跳上汽车时,由于拥挤他突然感到一阵恶心想吐,眼睛一黑,便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她“阿呀”地叫了一声,一只手紧紧抓住栏杆,另一只手接在了嘴巴口,生怕会吐出一些什么来。
总算到站了,杨彩霞走下汽车就像逃离灾难之地一样。一阵风吹来,她感觉好受一些。一会儿,她来到急诊室发热门诊,先测体温再排队候诊。杨彩霞的体温仍然有39度。医生确诊为感冒发热,给她配三天点滴剂量。杨彩霞的右手吊上点滴,刚坐下,短信又来了。她用左手想打开手机短信,但曾经为了保修手机而受过伤的左手,无法在小小的键盘上按扭,只得作罢。
不能马上看短信,她感到深深遗憾。
三大瓶点滴吊下去,杨彩霞回到家里已是下午两点。她感觉打了点滴后,精神好多了,走路也不再颤颤微微。于是她照常去菜场买菜,买水果,等儿子回家吃晚饭。然后照常晚饭后洗碗,上网看邮箱。本来她还想再看那个作家的长篇手稿,但终因撑不住,躺下了。这时她又测了体温,天哪,还是39度,怎么一分不降?杨彩霞这才有点着急起来。她知道很多大病,都是从高烧不退开始的。此刻,杨彩霞忐忑不安。她想找个人问问,就想起了吕树冬。于是,她发短信道:“热度未退,仍然39度。会不会得大病了?心里恐慌,不知如何是好?”
杨彩霞短信发出,就等着回信。然而吕树冬迟迟没回信,杨彩霞就又发一次。儿子上家教去了,九点一过没回家,杨彩霞就睡不安宁。她生怕儿子路上出车祸,或者又不规矩地与女生纠缠在一起。杨彩霞的心拎在半空中,楼道上每出现脚步声,她都会侧耳静听。有时候没脚步声,她也会神经过敏,仿佛儿子已经“咚咚”地背着书包回来了。
这晚儿子九点半还没回家,杨彩霞就往老师家挂电话。当她得知儿子八点半就离开老师家后,她心里的弦就绷紧了。她想一个生了病的单身母亲,生活的重担,仿佛把她的脊梁也压弯了。她内心在等两个男性。她的脖子伸得长长,那种期盼已经很久了。有时候她把自己想像成一个掌门神,只有这样她才感到有力量。
“嘟嘟”,手机短信的声音响起来了。杨彩霞赶紧抓过手机,这一刻她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手机上。短信打开后,她终于看到了她期盼的信。吕树冬说:“别担心,做个全身检查,好好休息。”这本来很平常的话,但在杨彩霞眼里觉得不同寻常了。她感到有一种异样的温暖,这温暖激起了她冰封已久的“爱情”的涟漪。
高烧,烧得她全身火辣辣地烫。她的心,也开始火辣辣地烫了。她又吃了几颗头苞,一颗黑片,然后再喝一大碗清热宁。等药吃下后,她就在家里焦急地等儿子。她想如果儿子有手机,发个短信给她,至少让她不用这样焦急。她知道,现在中学生有手机的也不少。儿子没提出向她买手机,杨彩霞就觉得儿子在这方面还不错。母亲是很容易满足儿子的好,只要他一点点好,母亲向同事、朋友们夸起儿子的好,总是露出自豪的表情。
“咚咚咚”儿子的脚步声,杨彩霞是听得出来的。她听见脚步声,从床上起来没披外衣就去开门了。“你在干啥?怎么这样晚?”,杨彩霞见到儿子回来,并不想责备他了。她说:“妈妈病着,你乖。”说着就顾自己回房睡觉。儿子:“噢”地一声,也没问问母亲有多少高的热度,要不要帮忙做些什么。在儿子的感觉里,母亲即使病了,也是他强有力的靠山。所以,他从来没想过母亲的身体,也没想过母亲为他是多么操劳与辛苦。他觉得母亲对他的好,是天经地义的,应该的。因此,他每次冲母亲发脾气,就会想你是我妈妈,我不向你发脾气向谁发呢!
杨彩霞的高烧,一连吊了三天点滴,虽然退一点,但仍然徘徊在38度5左右。这些天她每天与吕树冬发短信,有时一天发三四个,短信似乎成了她生活中的一个内容。也许人在病中,格外需要别人的关怀与温暖。杨彩霞只要听到短信响起来,那感觉就是远方灵魂的呼喊。然后,她的心就会荡漾着一种幸福。她没想过那是一种什么幸福,但她确实在最需要人关怀的时候,吕树冬关怀了她。尽管那关怀是精神上的,但杨彩霞确确实实感到了一种心灵的滋润。
大约又过了一个星期,杨彩霞的热度才彻底退了。通过这一次病,杨彩霞忽然觉得自己的身体正在走下坡路。她想一个女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能浪费每一寸光阴了。她要好好学习,勤奋工作。于是,她又继续编那个作家的手稿。读读写写,每晚都会工作到子夜。
儿子的最后一次摹拟考,不理想。杨彩霞有点看急起来,还有3天就中考了,呆在家里复习的儿子,倒一点不着急。他照旧上网玩游戏,还在QQ和MSN上与同学聊天。那天杨彩霞一回家,看见儿子在QQ上与人聊天,聊天的记录尽是喊对方:“老婆。”杨彩霞一下火冒三丈了。她“啪啪”扇了儿子两个头底巴掌,说:“你是不想气死我?你怎么叫别人‘老婆’?你与她什么关系?”
儿子用双手捂着头,说:“那是玩着叫叫的,同学们都这样玩,这是现在的时尚叫法,你不知道而已。”母亲说:“这样的称呼,怎么能随便乱叫。你不许跟他们学着叫,考前不许再上电脑。”母亲说完,气呼呼地坐到电脑前工作。
儿子回到自己的房间,看功课。他实在觉得没什么好复习了,要看的书全看了。不过,他还是遵照母亲的命令,复习功课。这本书看看,那本书看看,然后再做数学习题。做着做着,他就趴在桌上睡着了。母亲不知道,母亲在电脑前工作,还不断接到吕树冬的短信。看信和回信,使她一度忽视了儿子。她的内心,由于接到了吕树冬的短信而变得愉快起来。她想小黄说得没错,有了手机后,果然自己一天也离不开它了。吕树冬的短信,成了她心灵的期待。尽管都是电报似的三言二语,但她感到了一种爱。她想很多时候,因为爱才有力量。
杨彩霞想起周旋唱过的一首老歌:“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好曾在深秋给我春光,心上的人儿有多少宝藏,她能在黑夜给我太阳。我不能够给谁夺走仅有的春光,我不能够让谁吹熄胸中的太阳。心上的人儿你不要悲伤,愿你的笑容永远那样。” 杨彩霞不知道吕树冬会不会成为她心上的人儿,但她还是渴望能有人在黑夜给她太阳。于是,睡觉前杨彩霞又给吕树冬发了短信,道一声:晚安。
儿子中考的两天,杨彩霞没去上班。她一早给儿子做早餐,然后去自行车棚替儿子把自行车拿到大门口。儿子出发时,她又叮嘱儿子路上注意安全,做得仔细一点。然后她坐到电脑前工作。她一边工作,一边心里想,儿子该进考场了吧!过了一会儿她心里又想,这小鬼会不会粗心大意呢? 中午时分,她早早地做好午饭,老是把头探出窗外张望。当看到儿子骑着自行车笑咪咪回来了,她心里便知道儿子的自我感觉不错。
“怎么样,都做出了吧?”母亲说。
“都做出了,但不知道对错。”儿子说。
母亲替儿子盛满了饭,看他吃得狼吞虎咽,母亲心里高兴。饭后母亲让儿子休息一下再复习。母亲小心翼翼地侍候儿子,等儿子下午出发去考场,她才又坐到电脑前工作。晚上母亲悬起的心,总算放下了一半。然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晚饭后,母亲像往常一样在电脑前工作。电话铃响的时候,母亲也像往常那样去接。结果是儿子好同学骏骏来电话,母亲本想婉拒,但骏骏说有急事,母亲就喊儿子接电话了。儿子接完电话火冒三丈。他“咚咚咚”地冲到母亲跟前,拎起一个巴掌,说:“我明天还要考试,你叫我接什么电话?”
母亲被这一意外的巴掌惊呆了。儿子竟然打母亲的巴掌,母亲说:“你疯啦!你有没有礼貌?”儿子说:“你知道我明天还要考试,你干嘛让我接电话?”母亲强忍怒火,她不想让儿子明天考砸锅了。然后母亲说:“好吧!妈不与你计较,你好好复习吧!”
母亲回到电脑前,流下泪来。她想这个孽子啊,真是无法无天了。母亲对儿子的教育有点绝望。她想以后儿子成家立业,一定不能与他一起住。母亲一下想得很远,她越想得远,就越害怕儿子。她想必须对儿子提高警惕,必要时带他看心理医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母亲觉得儿子身上有一种青少年心理障碍病,这种病往往被忽视。
手机短信“嘟嘟”地响起来的时候,母亲的心情就被这“嘟嘟”声撩拨得愉快起来。吕树冬在短信中说:“不用担心,儿孙自有儿孙福。你自己保重。”杨彩霞想,这话不错。一天到晚为儿子操心,回报的竟是请她吃巴掌。母亲的心,寒了。母亲想以后要为自己多着想着想,毕竟到了不惑之年,人生能有几个不惑呢?母亲给吕树冬回短信说:“虽然你距我千里之外,但你住进了我心里。谢谢你的关心。你也保重。”母亲现在发短信,已经熟能生巧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杨彩霞忽然觉得自己爱上吕树冬了。她似乎一天也不能没有他的短信了。如果一天没有接到他的短信,她就惶惶不安。那感觉是杨彩霞离异后,从没有过的。于是那一天杨彩霞回短信时也写上:“我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