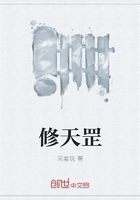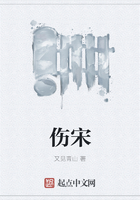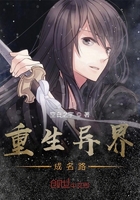道光十六年(1836),张穆曾校定祁韵士的著作。不久,《西域释地》《西陲要略》《万里行记》相继刊行。当时,祁寯藻手里还有一部祁韵士在乾隆年间编纂《外藩回部王公表传》时编辑而成的资料长篇。这十几册资料,因为“未经更事厘定”,祁寯藻便把它称之为“底册”。
张穆在校定《西陲释地》和《西部要略》时,曾见过祁家藏的这一底册。“底册”记载着清代前期蒙古各部以及西北回部的有关事宜。记述着西北地区复杂的山川形势,以及满、回、托忒等族的语言文字。
当时的张穆初出茅庐,要将这内容庞杂的“底册”编辑成书,并非易事。
道光十七年,祁寯藻出任江苏学政,到任后拜访了江南名士李兆洛。二人时相过从。道光十八年夏,张穆南游,经常和祁寯藻相聚。于是,张、祁、李三人的谋面成为现实,在交往中,他们谈起了祁韵士的著作。
道光十八年九月,是李兆洛的七十大寿,祁寯藻以学使的身份到场做寿,张穆随同前往,李兆洛拜见祁公时,又谈起了“鹤皋诸书”,即祁韵士的著作。后来,祁寯藻拿出了先公祁鹤皋所著的《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及其谪戍塞外时写成的《西陲总统事略》《西域释地》《西陲要略》。祁寯藻认为,《西域释地》等三书已有刊本,而《外藩传》,先人精力所萃外间少有知者。他认为,那《外藩传》是他的先父心血和智慧的结晶,但是世人很少有人知道它,想综合各传为编年体,成一家私书,就像司马迁的《史记》一样,藏之名山,传之四海。因此,把这个重任托付给这位江南名儒李兆洛。
李兆洛读过这些著作后,表示愿为效力。于是邀其至友毛岳生编次,门生宗景昌校写,并补《藩部世系表》。(此表后由徐松重新校订),后来形成李兆洛称之为《外藩提要》的编校本。
但大业未竟,李兆洛不幸于三年之后逝世。
于是祁寯藻便托张穆来完成这一书稿——即所谓编校本的最后修订工作。
祁寯藻把这项他认为只有像江南大儒李兆洛才能胜任的工作交给张穆来完成,并没有看错了人。如果说,当年校订“底册”时因初出茅庐,尚未成熟而中途搁置;那么,此时的张穆已经磨炼成了“学界大儒”“舆地高手”。而他那工作时的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精神,恐怕有些“大儒”和“高手”都难以企及。
张穆在校稿时,常用红黑两色毛笔来处理不同的修改之处和增补内容,或在空白处写上眉批或旁批。有时,还在某段文字的下面勾划符号,作出标志,以示强调;有些地方,还将增补的内容写在贴单上,再将贴单贴于原稿。
《校订稿》全书18卷。张穆在复审过程中改动之处达到千余条,增补约600余处,删削60余处。增删的文字少则一字或数字,多则数十字或数百字,最多处达1000余字。
这部手稿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读其手稿,想见其为人,看着这样的书稿,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张穆在校订过程中,对一些书写格式作了调整,并更改了书名,将李兆洛原文中的《外藩蒙古要略》《各藩要略》《外藩提要》等统一改作《藩部要略》,使之与《西陲要略》的体例相一致。读来,一目了然。
一般人以为,校订书稿也不过就是修改订正文字,疏通一下句子。但对张穆而言,这无疑是一次“再创作”。经过他的一番精心的修订,早期粗糙的半成品,已经变成史地之学的精品了。
此书在道光十一年正式刊行。因为祁韵士号筠渌,便以“筠渌山房”的刻本问世。
张穆还校订过元好问的诗文集。
元遗山名好问,是有金一代的大诗人。他的诗作上承唐宋,下启明清,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桥梁。其诗风追随老杜“沉郁顿挫”自成一家。他的创作旨趣也和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中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十分契合。
元好问祖籍平定,于北宋靖康之末迁居句容(今山西忻州市),因此,在他的诗文中常常称平定为故乡。生平踪迹往来,与平定至熟。
张穆的故居阳泉山庄,遗山先生曾到此访友,并写成《宿阳泉栖云道院》以记其胜。其中有句云“一笛悠然此地闻,住山还忆写大君。已看引水浇灵药,更约筑亭宿野云”。悠扬的笛声,潺潺的流水,盛开的芍药,飘动的野云……在如此美好的地方住宿下来,该是何等的惬意!
遗山先生歌咏阳泉的诗作甚多,兹不一一列举。
但最能反映元好问创作成就的,还是那些揭露时弊,关心民生的作品。在他的《雁门道中书所见》一诗中,这样写道:“金城留旬浃,兀兀醉歌舞,出门览民风,惨惨愁肺腑。三年夏秋旱,禾苗穗未吐,一夕营幕来,天明但平土。”
诗中把金城歌舞饮宴的场面和民间惨不忍睹的贫苦生活形成对比,让人想起了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夏秋干旱,禾苗枯死,农民颗粒无收。蒙古大军的铁蹄一到,田园顷刻之间被夷为平地。诗人最后又叹息道:“盘盘雁门道,雪涧深似阻,半岭逢牛车,人牛一何苦”;在险峻的雁门道上,半山腰际诗人碰到了一个车夫赶着牛车行进,下面积雪的山涧深不可测,前面的山路盘旋曲折。诗人叹息道:人像牛一样的辛苦,这是何等的生活!
元好问的诗歌以七律、七古成就为最高。七古兼容李白、韩愈,苏轼的诗风,七律则主要受杜甫的影响。特别是那些以丧乱为题材的诗歌,关注现实,感慨深沉。清代著名学者赵翼评其诗“深沉悲凉,自成声调”,认为“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除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把元好问与杜甫相提并论。这并非对他的过誉,当代评论家都认为:元好问不仅是金国诗人之冠,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
面对这样的一位同乡先贤,张穆自然是仰慕有加,心向往之。他在《元遗山先生集》序中说:“遗山尤夙所仰慕。”原来,张穆的心里早就特别敬仰这位大诗人,决心校订整理他的著作,“以助桑梓雅淡”。于是便开始了他的工作。
张穆在校定《遗山全集》的过程中,搜集考证了各种有关书籍:如《元史》《金史》《元文类》《金石例》《金文雅》《山西通志》等。他参考各种资料,“缺者补之”“误者订之”。如果有些东西无可考较,“概从阙疑。”并没有因为元好问是他敬仰的同乡先贤,而在文集中氽入那些夸大不实之词,体现了一位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元遗山先生集》共四十卷,明储巏所辑。有清康熙四十六年无锡华西闵《剑光阁刻本》。至嘉道年间,方翁纲和叶至冼先后批注题记。最终由张穆校订题跋第六至第四十卷,于道光二十九年重刻并撰序。
张穆谦虚地说,他校订刊行元好问文集的目的只不过是“助桑梓之雅淡”,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给家乡的人们茶余饭后高雅的谈论增添一些内容。其实何尝只是如此?如果没有张穆对遗山文集的整理校订,恐怕后人至今也难以见到这位堪与诗圣杜甫比肩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庐山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