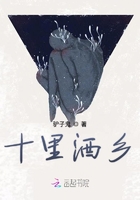道光十一年(1831)的秋天,张穆从家乡来到省城太原参加到京城国子监(国立最高学府)读书的选拔考试。参加这种考试的考生是由州府教官上报,再经学政与总督与巡抚商定认可,又经学政主持考定,然后选择“文行俱优者”保送入京就读,叫做优贡生。
经过考试,张穆取得了优贡生的资格。按照当时的规定:优贡生进入国子监学习,朝考期满之后,可以做官,不过起点很低,一般只能从教官做起;如果由乡试而会试,由会试而殿试即由举人而贡士,由贡士而进士,可以取得更为广阔的进升之路。
现在,摆在张穆面前的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以他的学识才华,乡试中榜,考取个举人,进而入京参加会试、殿试,考取个进士什么的并非难事。但张穆选择了“以优贡生入京”的起点很低的做官之路。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他的内心深处,到京城见见世面,在国子监接受几年熏陶,广交天下文友,博览文化典籍,从而成就一番事业的意识,胜过了做官为宦,光耀门庭的愿望。
在这一年,还有一件事需要提及,早春二月,他曾前往寿阳平舒村拜访祁寯藻。
此公何许人也?
祁寯藻,字叔颖,号淳甫。乾隆年间史地学家祁韵士的第五子。嘉庆十九年进士,官任侍郎、尚书,后为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执掌国家重权。《清史稿》称其为“三朝耆老,辅导冲主,一时清望所归焉”。
中英鸦片战争期间,主张查禁烟贩。曾为抗英名将郑延廷雪诬。
他又是个饱学之士,著有《马首农书》《亭集》。
因为母亲在籍卧病,祁公回家省亲。此时正家居在乡,这给张穆与他的会见提供了契机。
祁寯藻和张穆还有姻亲关系,他的小妹就是张穆的三兄丽暹的妻子,因此,张穆呼祁寯藻为五兄。
因此,张穆的这次造访,既是亲戚往来,又是切磋学问。可以说与祁寯藻的交往,对张穆的人生走向及其学术研究都有重大影响。
张穆在1832年农历的正月入京,国子监朝考期满。按当时的规定,朝考一等者任知县,二等任教职,三等任训导。张穆考试成绩居中,选任正白旗官学教学,当了一名教员。
道光十九年(1839)六月,张穆在北京,准备参加顺天府乡试。
乡试在清代科举考试中是道难关,因为中式名额十分有限。嘉庆年间的山西,每届乡试仅可取士80人左右。张穆曾由京返乡,参加过两届乡试,均未考中,只好留在北京教书。不过因是优贡生的身份,便多了一重选择,可以到顺天府应试。一者顺天府中式名额之多为全国各省之首,二者张穆也希望转换考试场地能给他带来好运。
考试设在北京顺天府贡院,时称“北闱”与南京的“南闱”并称当时中国的两大考场。
其大门正中有贡院匾,内建仪门、龙门,再进去有望楼,人称明远楼,专供巡检人员眺望之用。考生的试房,按《千字文》的顺序排列,约共九千余间。人居一间,大约一米见方。考生入号后即将栅门关闭,等交卷时方可离开。上厕所要领号牌,有专人跟随,出去者曰“出恭”,回来者曰“入敬”。直到现在,我们阳泉乡下的一些老人们还把上厕所称作“出恭”。
考场的场规非常严格,衣食文具皆有特殊的规定。比如参考人员考蓝中所携带的食物、糕饼馒头都需要切开检验,“片纸只字不准携带入场”。
8月8日是这次乡试的头场。重八是个好日子,但给张穆带来的却是一场厄运。
原来,张穆在入场之时,考蓝中带着一瓶酒。提检小吏发现后呵斥:“去掉酒瓶!”张穆听后却拿起来一饮而尽,然后才扔掉酒瓶。这个举动惹恼了那个平常惯于作威作福的小吏。于是小吏和他的同伙开始翻检张穆的考蓝,在翻检过程中毁掉了他的笔、墨、砚台,撕破了他的衣服。这下可激怒了张穆,他拍打着自己的肚子说:“这里是我藏经的书箱,五经四书都在里面,你们能搜检出来吗?”
搜检人员更为恼火,继续进行更为严格的检查,果然从他的笔袋中发现一张有字的纸条,不过与考试无关,是他平时写作时残留的废纸。谁知那搜检人员竟然以此为证,一口咬定张穆有意“挟带”,当即送交刑部处理。
刑部判定:革去优贡生资格,永远不准参加考试。
张穆的入仕之路彻底断绝。
对于这次导致张穆人生转折的巨大事件,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张穆因小失大,过于鲁莽;有的人认为他使性仕气,有失检点;有的人甚至认为,这是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在作怪。
对于这些见解,笔者皆不敢苟同。
让我们看一看张穆在这件事发生前后的一些表现。
前文讲过,张穆放着由乡试而会试而殿试,由举人而进士而状元的坦途不走,而选择了以优贡生的身份去北京当一名“教事”的小径,说明他的内心深处有着长见识,做学问胜过光耀门庭的意识,此其一。
到北京后,他所从事的重考据,重实践,以经国济世为目的的“朴学”研究,也与那考场专用的华而不实、僵化死板的“八股”时文毫不相干,此其二。
事发前,张穆对这次考试作了“精心”准备。考前心态平静,“胸有成竹”,备考之余,照样和友人们品诗论画,饮茗喝茶,此其三。
事发后,“气甚平”“语甚逊”“虑甚周”不像是做了什么“鲁莽事”之后的后悔莫及的心态,而且,其后并没有像他的好友沈垚那样,从此一蹶不振,郁郁而终,此其四。
他平生最为仰慕的人物是顾炎武。人们知道,亭林先生是明朝遗民。清廷慑于他的品德学问,使用了种种手段,想为其所用,皇帝屡屡下诏,召“博学宏辞”。但他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固辞不就”。张穆也是个“不合作者”,此其五。
由此我们想到了不买唐明皇的账,在大庭广众面前敢于戏弄权贵的李太白。
由此我们想到了敢于和封建礼教孤军奋战的鲁迅先生笔下的狂人。
看来,张穆的这次偶然事件,只是偶然中的必然罢了。
至于张穆的幸与不幸,历史早已作出了结论。如果张穆考试得中,中国历史上只不过多了一个为五斗米折腰的小吏,哪里还会有那些彪炳史册的皇皇巨著!
有清一代,即以平定而论,进士及第者数以十计,然能够在其学术领域占一席之地者,仅石舟先生一人而已!
这一年的张穆三十五岁。
从此以后,他长期寓居于北京宣武门外的上斜街闭门著书。书斋定名为“斋”,名字也由张嬴暹更名为张穆。
在这里,我们不妨咬文嚼字地来一点考证,斋名“”,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解释的:“,归也,从反身。”徐锴注曰:“古人之所谓反身修道。”
如果说,在顺天应试之前,张穆还没有认清这个没落王朝的黑暗而“锐身进取”;那么,在经历了这场看似意外其实也在意料之中的事件之后,张穆采取了决绝的态度,迷途知返,去“反身求道”。至于张穆的那个“道”,到底是什么?从他后来的言行中不难看出。
那个穆字,有肃穆、静穆之义,兹不赘说。
从此之后,他便在自己的斋里开创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
还有一件事需要提及。时任编修官,詹事府赞善,进士出身的赵振作,毅然将自己的胞妹嫁给了这个终生已定的连个举人名分也捞不到的白丁张穆。
可见,慧眼识珠之人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