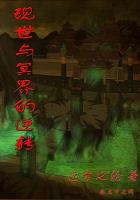那人转眼鄙视的看了我一眼,道:“姑娘外地来的吧?”
“有什么问题吗?”
“怪不得!”那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然后神秘兮兮的道:“姑娘可知道今天监斩的是何人?”
我纳闷道:“不知。”知道我还问你干嘛?
“嘿嘿!是丞相府上的二公子,少上造公良策大人!而且听说今天原本的记录官得了丁忧,回乡守孝去了,三公子公良闫帮他顶了这份差事。公良一家三位公子,那可都是天上有、地上无的人间绝色,今天一下子能够看到两位,怎不叫人兴奋?”
我听的目瞪口呆。
不解道:“可人家明明是男的,你有什么好兴奋的!”
闻言,那人一愣,半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头也不回的掺和进了人群。
我暗叹,真是偶像无国界啊!即是帅哥,到哪里都是吃香的!只是不知道这两人比起我的房莫来,到底是谁胜谁负?
“来了来了!快快快!天啊!二公子真的好俊美!神人啊!三公子呢?”
“在后面呢!”
“真……真是俊美啊!快看,我三年前在长文街的时候,还看过一次,可是这么近距离的,我还真没有过呢!你看……他的皮肤好好哦!”
“是啊!是啊!你看他的手指,简直就像是玉雕的。”
“又高、又俊美、又有文采,家世也是没话说!这才是我们男人的典范啊!做人要做成这样子,真不知道上辈子要积了多少德!”
我无语了,这个大宋的人还真叫人瀑汗。
人群走过,囚禁在木栏内的一个白发老者身穿着囚服,披头散发的萎靡着,就在队伍即将走到我面前的时候,老头突然暴起,用手中的铁链敲打着囚车,睁着血红的双眼控诉着他的不甘,厉吼道:“权臣当道、皇上昏庸无道!老臣无罪!罪的是那些闭塞了圣听、谗言媚上的无耻小人!苍天无眼啊!”
目光掠过,寒意让人心悸。
“啪……”沾着盐水的荆棘鞭打在囚车上,身后传来官兵的怒斥。
人群分散开,我也总算是见到了传说中的俊美的二公子公良策。不!或许,应该叫做路梏。
人生的际遇啊!还真是奇妙。
虽然我确实是有目的的找到了这里,但却没想到竟能这么快就见面!二公子公良策就是路梏,那么,我的房莫呢?
答案很快揭晓。
是三公子。
还是一样的慵懒,眉宇间的淡漠依旧能拒人以千里之外,一袭白衫,微风吹拂,即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他却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存在。
一人一世界,看来,我的男人没变。
当阎王告诉我他转世时的惊慌、成为路梏兄弟时的愤怒、以及阎王爷彻底将他遗忘后的无助……仿佛就在刹那间一切都烟消云散,我松了一口气,心踏实下来。
房莫,你感受到了吗!我,回来了。
薛文公三族上至同袍宗室、下至子侄儿孙,从七八十岁到十几岁不等,囚车一路行来,竟也有六十几个人!其中,再加上妇女妻妾,这些愿不属于三族范围内的丫鬟仆役,围挤在一辆囚车内。哭声、求饶声,呼天抢地的让原本就是在看热闹的人群更加兴奋起来。
麻木了。
反正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些官家的事情天天在发生,谁家兴旺谁家败,与他们这些平头百姓有何关系?
囚车行的很慢,一路上有无数的百姓围堵上来,目的,倒不是想来给薛文公送行,以我的估计,其中倒是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来看公良家两个公子的。我有点好笑,看着我的男人这么受欢迎,我是不是该感到骄傲呢?
所谓的端门其实就是城外十几里地的一块平台,背山靠水,从风水学上来讲,可以压邪避祸,北地的玄武位主土,煞气再凶,也能被皇朝的地龙气所镇压。
猎场外围早已用麻布封了起来,囚车一到,一队士兵齐唰唰将百姓隔离开来。
路梏,呃?不,现在是公良策,身穿墨色绣仙鹤正三品朝服严肃的坐在正主位。公良闫坐在其右手,执袖,慢条斯理的严研磨水。坐定,其余几个朝廷的官员才陆续的就坐。
人群众,我看着公良闫依旧是面无表情,仿佛外界发生什么事情也与他无关的样子,一愣。虽然他执笔的手温良如玉,但却不知为何,我心中隐隐有一种感觉……那手,是一只握剑的手。
“三公子连写字也是这么好看啊?”
“那当然,听说连大家光禄大夫也说三公子乃是文才出众呢!两年前的论演,三公子没有参加,若是参加了,我猜绝不会输给小王爷宫桀的。”
“那不一样!小王爷宫桀可是文武双全,三公子乃柔弱书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怎么好比?”
“你……你竟敢说三公子坏话?”
“我是实事求是。”
我听着身旁两人为了公良闫和那个什么宫桀争吵起来,不由摇头,目光再次掠像公良闫,不由皱眉。
我的男人房莫的后世……这个公良闫当真只是一个柔弱的书生吗?
人群越聚越多,太阳也开始逼近高空正中,插在高台上的一根木签像是死神临近即将敲响的丧钟,周围越是安静,就越是衬托着围场当中萧瑟的凄凉。
按着规矩,在犯人行刑之前的半个时辰内,应该是可以有犯人的家属过来送一顿断头饭的,但薛文公的家属显然已经都在刑场中了,三族之外,避嫌尚来不及,又怎会甘冒着天下之大不韪的危险过来只为了送一顿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