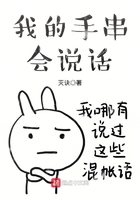正在这个时候,我母亲打电话来。说的还是SARS!她说村里现在已经封路了,村民们自发组织起来日夜值班,从外面回来的人,包括我这种在外面讨生活的和外地来的人,一概不准进村。母亲还让我这段时间尽量不要外出,要在家里吃饭,不要到酒吧那种人多的地方去。我说好,好,好。跟母亲说电话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酒精又在大脑里开始发作了,我有一种要呕吐的感觉。母亲问我欧阳雪还好吧。我说,她很好,刚刚才从打过电话来,我想她吃了那么多牛排应该像一头牛那么强壮了吧。
接下来的一天里,即4月22日,我看了整整十几个小时电视,看得眼睛都痛。
23日,还是看电视。从早上晨运回来后一直看到傍晚。饿了就在冰箱里找点东西,热一热将就一下。中午睡了一会,好像是个把小时吧。从下午开始,我一边看电视一边一边喝酒。这次喝的是青稞酒,一种产自西藏的外表看上去像红酒一样但比红酒口感好的酒。我一个人喝完了一瓶还意犹未尽,继续喝红酒。我像个破罐子破摔的人一样把自己当成一个酒囊了。要命的是,自从我开始跑步,即开始过健康生活后,身体越来越好,酒量也变成了一个无底洞,怎么喝也喝不醉。我多么想大醉一场啊,一醉解中愁。可是我就是无法让自己喝醉。我想,再这样喝下去,就算是中产阶级也会被喝成一个贫穷的人的。
最后我看凤凰卫视的“宣战SARS”这个专题报道。英俊的胡一虎正在说一些让人为之动容的话,他先说了香港一个护士因公殉职这个小故事,然后说医护人员每天都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坚守岗位,很多医护人员都自动请缨去护理SARS病人。再然后,胡一虎同志念了一封来自医院的观众来信:“今天一上班,院长召集了我们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院长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胡一虎的语调还算平静、朴素,我却鼻子发酸,泪水紧接着不争气地流了下来。好一句“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我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令我的泪水如此充盈。
这个可恨的胡一虎了,好像在我心底下最软弱的一角扔下一把绣花针一样。
身上的酒精味道又开始折磨我了,连呵出来的气体都臭得令自己无法忍受。越是情绪不稳的时候我就越无法容忍自己身上的异味。红酒好喝不假,但我的身体受不了红酒,牙好像又开始隐隐作痛了。青稞酒更甚,好像是一种补酒。我感觉到全身上下都是热烘烘的。
这样的时候,我多么希望身边能有一个人。哪怕这个人是不会说话的,哪怕这个人是个失聪的,甚至这是一个植物人……只要是跟我一样是个有生命感觉的人在我的身边,就已经足够了。孤独是如此可怕。我的承受似乎已经到达了极限,我只想有个什么人能为我减轻那怕是万分之一的孤独的感觉。
洗澡。还是洗澡。我无法不洗澡。我开着淋浴让微热的水从头顶缓缓而下,手中的牙刷使劲地在嘴里来回拖动。我不能再让自己哭泣了,我他妈的堂堂七尺男儿怎么可以轻易掉泪呢。
换上柔软的裕袍,感觉好多了,我闻到衣服上薰衣草那种古怪的香味以及洗发水浓郁的甜香。
就在这种诱人的香味里,我开始回忆我的生活。没错,我恨我的生活,我恨我的朋友,我甚至恨我自己。欧阳雪一声不响跑到英国去,实在是太自私了,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实在可恨;江维永远也不会对我说他内心的痛苦,他永远都是以上帝的嘴脸出现在我的最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令我永远亏欠着他;万纤我把她当成红纷知己她却抄袭我的小说,我还在她面前暴露了男人真不忍让人了解的欠缺,而我前天还收到她问候我的邮件;马达这个混蛋,有两个老婆还不知足居然还做出这种令朋友脸上无光的事情……我像个愤青一样怒发冲冠,内心像有头小兽正用它的獠牙使劲撕咬着……到了这个时候我再次知道我并不需要这种生活,这并不是我真正的理想,我的理想只是过一种快乐比痛苦更多的健康生活,我只想像我大多数朋友一样过一种庸俗的井市生活……我选择了文学的同时等于选择了逃避,我一直都在逃避,我逃避自己的内心,我是个无能的人,而欧阳雪却心甘情愿地为我的逃避为我的无能提供物质基础。我他妈的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我以往的平静只是我最无耻的伪装。
我使劲揪自己的头发。可是头发太短,我甚至连自己的头发也捉不牢。我从客厅走到房间,再从房间走回到客厅。当我在床上倒立的时候,浴袍的下摆倒垂下来,覆盖下来,我的脸于是便被埋没在一片黑暗中。我们可以想像一下,我腰部以下的肢体裸露在暧昧而微凉的春风中,像个圆规一样并列着直接天空。王小波写过一首诗:
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
而阴茎倒挂下来
这首诗的题目是《三十而立》
不知道是因为腰部以上的部分覆盖着两层厚厚的棉布,还是因为身体的血液向下倒流而感到暖烘烘的。我全身的肌肉绷得紧紧的。总而言之,我身体上下两个部分体会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下面暖,上面凉。或者说,下面凉,上面暖。是的,这件加厚的裕袍实在是太厚了,季节已换,而我的浴袍却还是这么厚。我不知道倒立支持了多久,总之在我昏厥过去之前,当我的血液就要从大脑里喷涌而出的时候我倒在床上。我解开浴袍的腰带,我躺在床上,仰着身子,让自己从浴袍里脱颖而出。我的手划过光滑的肌肤,尖锐的指甲划过的时候我感受不到痛楚反而有一种自虐的快感。无法抑止,我需要来一次必要的自慰,要不然我不敢保证自己不会从这19楼上跳下去。可是我无法勃起。每天早上坚硬如铁的物件在这个我最需要它表现的时候它却不听使唤。
在这个微寒的春天,我赤裸着,来到客厅看A片。我就是不相信,我他妈的连自慰也无法如愿!
当高潮即将来临的时候,我的脚和头成为一个平面的三个支撑点而身体则如满弦的弓一样紧绷着向上凸起,左手的力量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而右手,原本是托举着同样充血的屁股……后来,我再次站在淋浴下面,看着左手和右手的血迹被温水稀释后顺着手臂往下流。腿上也有血液往下流淌。我的右手的五个手指把屁股挖出五个洞来,手指甲上还有掐下来的皮肉,而左手也把那个部位磨擦伤了。痛,火辣辣的痛。非常痛,前后都痛。我觉得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我宁愿意马上死去也不愿意再承受这样的痛楚,同时感觉到疼痛的还有思想的深处。
我以伤害自己的身体的方式使自己到达了一个另类的高潮,一个空前强大的高潮。
疲倦,非常疲倦,我有一种即将就要虚脱的感觉。
突然就有了一种迷失记忆的感觉,坚硬的头撞向同样坚硬的墙壁。那个响声,令我吓了一大跳。是的,我有一种作贱自己的欲望。在我的头撞向墙壁之前,我常常为自己头脑里储存着的智慧而骄傲,而在那一撞之后我认为我大脑里所储存的都是他妈的臭狗屎。
身体的前后都受伤了。
今晚,我将以何种睡姿入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