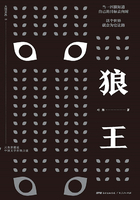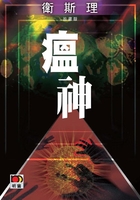万纤说,好吧,其实,这么多年的感情,最清晰的印象还是初恋,也就是高中时代那个男生,现在想起,坐在他自行车后面的感受,还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但是我始终弄不明白,才几个月不见面,他怎么能这么快就找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呢?
江维说,我觉得那个男生,未必就把你当成了恋人,或者他把你当成自己的妹妹也说不定。
在大家的笑声中,万纤说,有这个可能,不过,我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解释,太失败了呀我。
我说,万纤,不介意的话我问你个比较深刻的问题。
在大家的哄笑声中,万纤似乎略微犹豫了一下,眼里闪过一丝苦涩,但手一挥就说,问吧,反正今天我是豁出去了。
我说,经历了这么沉重的打击后,你是否会有一个以前根本就不可能想象的转变?
具体指的是什么样的转变?万纤说。
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你的人生观、做人的态度之类的大话,从小的方面就是具体指你在爱情方面的态度,即经历这些后,你是否还有能力去跟别的人相爱?
今天晚上,我觉得你更适合做这个主持人。万纤笑着说。很难讲,因为那是以后的事情。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从此以后,心慈手软这个词以后肯定跟我无缘了,因为我已经活得太明白了,一个人如果活得太明白,就不会感情用事,不感情用事,就不会再犯不必要的错误!
那你还老是说要跟四方一起去自杀!马达说。
万纤看着马达笑,那只是随随便便的一句笑话,你别当真。说到这里,我就说句题外话吧,在我们这些朋友中间,我觉得,四方是个实心人所以他的痛苦最多,快乐最少……
万纤这话说得相当准确。我打断了她的话说,万纤你真是太理解我了。没事,如果真要自杀,我一定拉上你一起去的。
……
关于这个情人节的谈话,我已经写得太多了,我罗里罗嗦写了这么多,其实只是想引出万纤的情感经历,因为万纤在感情上的屡屡受挫,在感情方面苦苦追求,苦苦挣扎仍然一无所获,最后甚至导致她性格大变,并且因此而使到她后来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一切。
这天晚上的内容已经结束,如果江维不提前退场的话。以往,我们有什么活动,送万纤回家非他莫属,因为他有一辆汽车而我们的是摩托车。江维的父亲突然发病,谈话快结束时他老婆打来电话,他便飞一样离开了。是我用我的破摩托车送万纤回家的。
快到文艺大院时,万纤突然说她暂时不想回家。我问她想干什么。她说想找个地方坐坐,喝杯酒。我把车停在一个大排档前面,表示我可以陪她在这里坐坐。万纤说还是去酒吧好,这种地方的东西怕不卫生。我知道万纤怕的不是食物的不卫生,是这里进进出出的人,档次太低了。我说,就你事多,哪里坐不是坐。话虽这话说,我到底还是陪她去了丽心钢琴吧。
我们到达时,正是酒吧最旺的时候,满屋子都有是人。快过年了,大家都忙,晚上心态比平时更浮躁,到酒吧的人也比平时多些。这么冷的天,这里还能有这么多人,真是不容易。不过,到这里来的客人跟别的酒吧有些不同,到这里来的,大都是些自我感觉不错的所谓的白领,不怎么喝冰凉的啤酒,大多数人喝的是中国特色的鸡尾酒和国产红酒。所以马达经常取笑我和万纤,到这种地方来冒充领导时尚朝流的小资阶级。
我的原意是喝杯果汁就算了,我的牙还隐隐作痛,今天实在是不适宜喝酒。但是万纤不同意,说到这里来怎么能不喝酒呢。她自作主张帮我要了杯草蜢仔,一种薄荷味很重的鸡尾酒。
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是有些晚了,客人太多,熟悉的服务员就把我们安排在大厅以外的另一个小厅中。这样,我们可以听到钢琴和小提琴的声音,而看不到弄出这两种声音的夫妻俩。小厅内还有几对小情侣。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略感不安。万纤可能感觉到了气氛有些不妥和我的不自在,但她没说什么,只是看着我笑。
万纤似乎还未能从刚才的谈话里跳出来。她说,四方你觉不觉得我今天说得有些太直了。
你说得很好,很到位。
我的感觉是,整个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在说真心话,你们都在敷衍我。
怎么会呢。我说,你真是太敏感了。
下次我再做这个栏目的时候可不敢再请你们这些大龄青年了,得请些二十出头的人。年轻人在谈论的时候才会无所顾忌,尤其是在谈到感情问题时。你们这些人呀,在社会里混得太久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好笑。我也曾经二十几岁,也有过口出狂言的张扬。说实话,要现在的我在谈到感情问题时像十年前一样畅所欲言,简直是天方夜谭。
四方你不会觉得我特别傻吧?
我说,你什么意思?
就是我今天几乎把自己所有的心事都说出来了,我知道,作为一个主持人,把话说到这个程度是不合适的,但是当时我有些控制不住自己,我有一种一吐为快的冲动。
我说你今天的表现很出色,不愧是一个有经验的编辑。不过,我觉得你今天晚上还是有所保留的,比如你说的真正爱过的那个不能在一起的人……
万纤说,没有的事,真的,说着玩的,你别当真。
我说,可是我觉得那是真的哦。
万纤说你少取笑我,你李四方是什么样的人,你是怎么想的我未必还不知道?四方,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没有女朋友,你会不会接受像我这种有这么复杂经历的人?
我的意识一时无法转过弯来,万纤这个话题的转换太快。我沉吟片刻才小心地说,你怎么突然想到这个的?
随便问问。可能是因为我现在对自己失去信心才会问出了这么傻的问题吧。
我一口把杯中的酒干掉,说,妈的,这酒真不经喝。这么说吧万纤,你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思考,而是时间,你需要时间去休息,你实在是太累了,等你休息够了,你就能真正面对自己的一切,当你能真正地面对自己后,你根本就不会觉得自己傻或者聪明了。其实人不管是聪明还是不聪明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能感受到生活中的幸福。
万纤说,我有些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我说,其实,你心里明白的。不是有许多人失恋后奋发图强化悲痛为力量,把自己变成一个大文学家吗?
万纤哈哈大笑。说,你真厉害呀,怎么跟我想到一块去了。我正是有这个打算的。不过,我有好多年没动笔写小说了,在报社里做得久了,现在我除了娱乐新闻好像啥都不会写了,真是白念了这么多年的中文。
万纤让服务员送一支红酒过来。我想要阻止都来不及。
小提琴的声音,经过扬声器的扩大后听起来有些霸道,而钢琴则是原汁原味的。这音乐实在是不协调。我把我的发现告诉了万纤。她说,你现在才知道这个呀。我说是呀。她说,她第一次来就知道这个了。我说,那你还经常来这里。她说,佛山这个破地方,你说我们还能去哪里?我想了一想,也是,佛山这个小城市,到处都是假模假样的场所,到处都是假模假样的人。
窗外,一辆洒水车经过后留下一条湿了一半另一半仍然是干的马路。路灯透过树叶从高处洒下微黄的光明。夜深了,经过的车辆不多。隔着厚厚的玻璃,汾江南路虚假的宁静与酒吧里激越的声音噪音达成了一种和平共处的默契。
这天的红酒喝起来味道有些古怪,似乎比平日更苦涩。我有些喝不下去,就往自己的杯子里加了好多冰。回到家里后,我才知道,是我的身体有问题才觉得红酒的味道不对。当天晚上,我的牙又开始痛。这一次的牙痛来势凶凶,一直闹了一个多星期,直到欧阳雪离开我了我还在痛。
半醉了,没喝多少,我们都半醉了。我的感觉不好,非常不好。不单单胃难受,心里也不好受。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之,跟万纤在酒吧里面对面的坐着,莫名其妙就觉得难受,心里出现一种难以压抑的烦躁。
这天晚上,我跟万纤都没再怎么说话。其间,有几次,我们的手在无意中碰到了对方后很快又躲开。这种躲开是刻意的。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后,稍稍吃了一惊。我认识万纤这么多年了,怎么今天会有这么微妙的感觉呢?我相信,万纤也有相似的感觉。是我影响了她还是别的原因呢?难道是万纤的遭遇对我造成了影响吗?
时候已经不早了,我想,我们还是早些回家。我对万纤说,今天到此为止,不能再喝了。万纤看着我,好一会也没有说话。然后她笑笑,说,那就回吧。
万纤的这一声那就回吧,意味深长,似是无意,又似无奈。
结帐,走人。已经是很晚了。
是的,我感觉到,万纤像个虚弱的病人一样,贴着我的后背,厚厚的衣服,无法阻隔体温的扩散。我不是个胆怯的人,但我有些害怕了。
突然,万纤使劲拍了拍我的肩膀,嘴了发出一个含糊的声音。我知道她要吐了,刚把摩托车慢了下来,还没有停好,就有东西从万纤嘴里喷射而出。
心情不好的时候,喝酒是很容易出事的。我这样,万纤也这样。
我把车停在路旁,扶住万纤,拿出纸巾,帮浑身发软的万纤擦干净她美丽的脸。她和我衣服上的脏东西已经是无法擦干净的了。万纤的脸上,始终保持着一个心满意足的微笑。妈的,这娘们,没准故意这样骗取我的服务呢。就在我扶万纤上车的时候,她突然睁开眼睛,抱住我,亲了我一口,然后嘿嘿地傻笑几声。
之后,万纤像一条蛇一样继续贴在我的后背,让我送她回家。我的头有些痛,还好不算太严重,还可以坚持。当时我有一个很坏的想法,就是不把万纤送回家,而是送去附近的酒店,开个房间,我们在那里住一个晚上。她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而我还有四分清醒。这四分清醒,足以完成好事。
我把摩托车开得很慢,表面上是照顾万纤,不让她吹风吹得太过,其实是像以前的小说写的那样,我正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是,很快,我就否决了自己的想法。这是哪跟哪呀,首先,万纤的酒量,我清楚,喝这一点酒,根本就不是问题,她可能在装醉——吐并不代表醉酒;其二,我若那样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跟她发生肉体关系——跟万纤与跟欧阳雪发生这种关系好像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没多久,文化大院到了。在正门口,万纤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以为她又要吐,马上急刹车,她的胸部狠狠地撞击了一下我的后背。万纤说声谢谢,把头盔还给我,又说晚安,就自己往前走了。连头也没有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