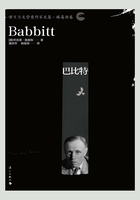约瑟夫定定地望着棺材,想起了蚕。蜜黄色的棺材就像一只蚕茧,安静地躺在他面前,让他在某个瞬间觉得自己仿佛置身另外一个时空。他拼命想把恍惚看到的画面记在脑子里,可是四周的噪音潮水般涌来——低沉的交头接耳声、清嗓子的咳嗽声、鞋尖不小心踢到硬木跪垫的脆响,时刻提醒他身在何处,随后他又一次在病态的懊悔与失落之间痛苦摇摆。“都是我的错。”约瑟夫想。这几个字像刀子一样刺在他的心上。
圣犹大教堂里,管风琴的呼啸声蔓延到他身后的空旷处,乐曲裹挟着悲伤,在半空中盘旋鼓荡。此前他也参加过几场葬礼,但这是头一回坐在前排,感觉跟以往截然不同。过去的葬礼上,他不过是一群吵吵嚷嚷的小学男生中的一员,在路边站成一排,与日后他连长相都难以记起的人告别。现在的他却处于整个仪式的中心,仿佛被一个讨厌又强硬的拥抱紧紧箍住。
他垂下眼帘,母亲的手轻柔地搭在他的膝头。约瑟夫把手放在她的手上,挤出一个虚弱的微笑,然后再次望向棺材,合起眼皮,让黑暗包围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他能回到某个确定的起点,从那时起留意每一个瞬间,现在是否就不会如此迷茫,是否就能理解事情发生的缘由和意义?可这一切又该从何说起?人们往往很难察觉一件事是如何开始的。与开头相比,结局反倒更加清晰可辨。如果一件事结束了,总有各种显而易见的迹象,比如事物终结,比如生离死别;事情的开头则更像阴影和雾气,悄无声息地融入四周,模糊一切。
约瑟夫竭力回想事情的起点,不知不觉又想到了蚕。最近他老是想起它们,不由自主,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起这种简单的生物,不明白它们与这件事有什么联系。但这一次他恍然大悟:试图解开过去那些纠结的线索,就像从蚕茧中抽出丝线一样。
抽丝时,首先要在蚕茧上找到松脱在外的丝,拿拇指和食指小心翼翼地捏着向外拉扯,让互相粘连的丝线与坚硬的蚕茧缓慢分离,这时轻轻晃动就能震断蚕丝,剩下最后一根丝线。只要微微抖动悬在丝线上的蚕茧,它就会在旋转中摆脱纠缠,剥离坠落。
这正是约瑟夫在做的事:寻找一条引导他前进的线索,无论这条线索多么纤细脆弱。一旦集中起精神,散乱的记忆图像便渐渐呈现出清晰而独特的画面:三个男人的面孔赫然在目,虽然他们彼此素未谋面,但每一位的人生都与约瑟夫不可思议地交织在一起。
他看到父亲的脸,上一次见它时,上面写满困惑、忧伤和愤怒。他还看到汤姆·莱顿的脸,像石头一样沉默,隐藏在房间的暗影深处。最后,他看到奔跑怪人的脸,那人眼中燃烧着绝望的火焰。奔跑怪人总是如影随形,像个躲在远处的幽灵,拖着不安的步伐越靠越近。
约瑟夫再次凝视棺材,松散的记忆丝线终于渐次解开,最后只剩一幅画面。那是他每天晚上透过卧室窗户看到的画面,是他邻居的旧木屋——汤姆·莱顿一家的房子,高踞在黑色的木桩地基上,活像一只蹲伏在阴影中的长腿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