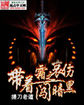“巴尔克,我想你应该知道,现在再添进来一个成员的话,我们就要把原先所有的人员计划再次打乱了!”
“是的是的,话是这么说,但是我们的人员就应该越多越好,不然怎么能看到那激烈的争斗呢?”
“好吧。那个家伙现在状况怎么样了?”
“该做的我都已经给他做完了,听说这次人群里有他的仇人,现在他就等着和班恩一起行动呢!”
……
“木先生,我们到了。”派来接我的人说道。
“就这样吗?”我问,“就在这海边开始吗?”
“哦,不,”那个人笑道,“我们还要坐计程车呢。”
“嗯?原来你是台湾的同胞啊,居然没有一点口音。”
之后,我们一路谈论着关于这次大疫情的事情,他的话虽少,但是可以看出,他还是很有主见的一个人。
聊得久了,我就在车座上小憩了一会儿。再醒来时,已经到了火车站。火车站讲的是法文和英文,而我恰恰外文极差,尤其是听力。这个时候,我稍感到有些不对劲了,那份敌意感觉又回来了。
但是那人没给我考虑的机会,将我拉进了火车站,并和另外两个人把我送进了火车,并给了我一张行程图,之后竟迅速消失了。
“相必……这火车上应该有和我同行的人吧?”我心想,“如果没有,那我就立刻报警!”
“十三号包厢……奇怪,欧洲人不是很忌惮这个数字的吗?。”我暗说。
走到十三号包厢,这是一个很偏僻的角落。推开门看了看,是个上下铺,还没有人。左脚刚踏进去,右脚自己竟忙不迭地就跟了进来。突然,我的头痛的毛病又发作了。于是放下包袱,在属于我的下铺躺了一会儿。
……
“Hello?”
“嗯……?”我用手揉着右边的太阳穴,从床上坐了起来。看看四周:没有人啊;又探头看看上铺:也没有人。
“唉!最近这神经真是太脆弱了!”我说完,起身接了一盆热水,洗了一把脸。
“您活得可真精致!”
又是这个声音?可是包厢里并没有人啊!真是咄咄怪事!
“朋友,我想我们应该是可以面对面交流的吧!”我说道。
“唉!真是无趣啊!”伴随着话音,镜子里冒出一个和我一般身高的人,规正的头发,白色的衣服,戴着眼镜,像一个科研员,总感觉在哪里见过他。
“原以为你还有兴趣和躲一躲猫猫呢!”那个人说。
“你好,库特·弗兰克,你的室友!”
“你好,木弥,幸会。”
“你是泰国人吗?还是日本人?”
“不,中国人。”嗯?等等!他不正是在用中文和我交流吗!
“哦,还好还好,亚洲的语言我只会中文和土耳其语。我看你不像土耳其人,就讲了中文,果然没有讲错!”
“所以……你也是来参加那个游戏的吗?”我问。
“嗯,是的!不过啊,我听带我过来的人说咱们这些参加游戏的人都是讲中文的,好像是因为主办方就是中国人。”他爬上上铺,和我聊着。
“这样啊……”我从背包里拿出手机,看了一下闹钟,忽然大惊失色。
“怎么了?”库特问。
“今年是哪一年?”我赶忙问他。
“额……1894年啊。”
(粗口)!好嘛,我终于想起来为什么他这么眼熟了……
……
“所以……到底怎么了吗?”他又问。
“哦,没什么!”我说,“哦对了,话说……你是做什么的?”
“我嘛……是一个探险家。曾经驾驶帆船跨越英吉利海峡、乘坐热气球飞越原始森林,完成各种看似不可能的旅程……”
“哦!真是不可思议!”我恭维他道。
实际上我在心想,只可惜现在潘德明还没有出生,不然我也不至于在他面前这么没话儿。
“那么,你是做什么的呢?还在留学吗?要知道,你可是我第一个见过的没有辫子的中国人!”
“我……”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总不能告诉他我是博物馆的导游吧!
“哦,我知道了!你一定是这里的华侨吧!那些华侨总是在外国人面前支支吾吾的。你放心,我不是那种爱欺负人的人!”
“感谢你,库特,你也是我见过的第一平等的人。”
“谢谢,你也是我见过的少有的没有那种眼神的人。”
“那种眼神。”
“对,那种眼神。”
尽管我们才相见不到十分钟,但我们都已经大概知道对方是什么人了。
……
“咚咚咚!咚咚咚!”
“你约的人?”库特问我。
“不,我一个人来的。”我说。
我们两个人一起看向那扇门,门还在“咚咚咚”。
“请问,里面有人吗?没人的话,我就进来了。”这是个女孩子的声音。
“有人!”库特喊了一声,但捂住我的嘴,把食指放在嘴前,寓意我不要说话。随后跳下床,突然变小,用手让我去开门。
我明白他的意思,把他捧在手上,躲在门后,为她开了门。
“您好,我想我……”
“这个人在和谁说话?”库特贴耳问我,而我摇头表示不知。
“请问,这位先生,这里应该就是13号房吧?我的手册上是这样告诉我的。但是我觉得您可能是看错了您的票吧,因为男女混铺真的在欧洲实在是太不常见了……”这个孩子居然在对着窗户说话,还说得有声有色,好像那里真有人一样。
库特点着他的太阳穴,我则左右摸着我的眼睛,最后库特同意了我的看法。
“咚!”
“先生,请不要再躲在门后看我笑话了好吗?”这个女孩儿竟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忙把弗兰克放进口袋,慌忙应付着。
“啊?啊……哈哈,我――只是有些奇怪,为什么男性的房间里会有女性要来,所以就静观其变了……”
“那么,您确定您的房间是十三号包厢吗?”
“当然,你看,这是我的票。”
“可是……”她拿出她的票,“你看,我的票也是这个房间,而且我们都没有上错火车。”
我对比了一下,两张票上的文字一模一样。
“难道说……”小女孩儿惶恐地看着我和两张床铺,“主办方竟然要让我们两个人共处一室吗?”
“只怕更糟呢……”我将手伸向口袋,“我们现在是三个人共处一室呢!”
“喂!我才不要掺合这破事呢!我要找我的律师投诉主办方!”弗兰克在我的手掌上大呼小叫加乱蹦。
“哇!你是来自小人国的居民吗?”那个女孩儿问。
“额……”
“那么,您就是来自日本喽?”
“很遗憾,小姐,我来自中国。”
“别开玩笑啦!就算你不是日本人,想必也是朝鲜或者东南亚的居民吧?你的发型……”
“咳咳!小姐,我想我们现在还不应该讨论这个。”弗兰克打断了她。
“哦,是哦……”小女孩儿挠挠头,“那么,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呢?”
“你们看!”库特指向一扇小门。
“奇怪,如果这里有门,拿它通往的不应该就是外面了吗?可它明显是一个房间与房间之间的便携门啊……”
“哪里有人?请扶我一下好吗?我的视力实在不佳……”
这个时候我才仔细地打量她:戴着一个针毡帽,身穿一套学员的衣服,戴着眼镜,双眼无神,拿着一根盲杖。
“原来是海伦娜呀。”我心想。
“这不是写着呢嘛,‘13(2)号包厢’,应该就是这位小姐的包厢。先打开看看吧。”弗兰克说。
门一推开,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小房间,而且是小到不能再小了,就像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房间一样,躺在床上,腿可以伸到沙发上;跪在沙发上,就可以开门了。
“我的房间……还好吗?”海伦娜问。
“嗯……在这个极其寒冷的冬天里面,你应该会感到很温暖。”我半开玩笑地说。
“那……请你们把我抚进去好吗?”
库特看了看我和海伦娜,我看了看海伦娜和他,海伦娜则在中间,茫然地看着我俩。
……
“咔噔,呼――”
“我想……问题可以解决了。”库特说。
但是我则更倾向于,这个包间将要成为求生的包厢。
“这位先生,这似乎不是你们的包厢吧?”
一个大概如今高中年纪的女孩儿背着一个很大的背包走了进来,那个背包足以装下一个和她差不多大的人。
怕不是要有两个修机位吧?
“请原谅,恐怕你们来错了包间吧?哦……”
她看向我和海伦娜紧紧握住的双手,似乎误会了,还有些不好意思,脸都红了。
“真行!”冒险家从我的肩上滑下来,变回了原先的体型。
“弗兰克,我想我们应该挪挪地方了。”
“你确定那么小的地方足够我们两个人住的?”
“我足够了!你不是能变小吗?”
“哼,我就知道……”
“所以……我们是那个……你们怎么说?哦!我们四个是室友吗?”
“啊不,你和海伦娜是室友,我和库特在里面,只是起夜时可能会打扰了。”
“诶?你是怎么……”
“她的视力不太好,希望你可以好好照顾她,拜托了。”说着,我把海伦娜推了过去。
……
“小姐们,木先生,也许你们之前就认识。但是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再熟悉一下彼此?”一头雾水的库特说。
“特蕾西·雷兹尼克,机械师。”现在听起来,她的声音还是挺甜的。
“库特·弗兰克,冒险家,偶尔搞搞发明,写点报道。”
“海伦娜·亚当斯,学员,正在筹备学费,多多指教!”
“木弥,来自中国,历史研究爱好者,幸会!”
等等,特蕾西、库特和海伦娜都是修机位,那么,会不会也就意味着,我也是个修机位呢?
天呐,我可不想拥有在游戏里修机位遛鬼的体验呀!